
活动简介

2022年4月29日晚,第十七期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5号楼201室举行,主题为“疾病污名与母职重构:患病孩子母亲养育历程的经验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戴嘉雯、陈一宁主讲,丁冠兰主持,宋丹丹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爱玉、副教授田耕、助理教授凌鹏出席并参与讨论。
内容回顾
研究介绍
戴嘉雯、陈一宁:
我们研究关注的对象是患特殊疾病孩子的母亲们,她们处于双重意义上的“密集养育”中:比普通母亲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面对复杂的照料,却无法满足社会的养育期待,更难以获得任何现实意义上的回报。
更多的牺牲是指,母亲们全方面地投入照料孩子的生活,从孩子出生到自己离去难以抽身。为了照料患病孩子,母亲们做出不同程度的让步。在双亲家庭中,更多的母亲选择辞职陪读;单亲家庭中,母亲们则在工作获取经济支持的同时照顾孩子,形容自己一个人当三个人用。这类安排与婚姻状况、家庭条件密切相关。但与普通母亲不同的是,患病孩子母亲的“让步”通常不是孩子成长阶段的一个选择,不会随着孩子的长大成人而停止,而是伴其一生。同时,特殊疾病也放大普通养育历程的诸多艰难,如因孩子的智力障碍体验更多教育上的挫败,因其社会性障碍感受亲子情感的断裂。患特殊疾病的孩子很难真正“长大”,他们对情感、生活、外在世界的认知保持着简单又黑白分明的状态,也许终其一生都无法理解母亲付出真正的含义。绝望的预期则是指,母亲们难以通过养育回应社会期待的养育目标。疾病剥夺了孩子进入社会与“成才”的可能,当普通的母亲还在以“望子成龙”的梦想去期待孩子的未来,患病孩子终身因社交能力和生活能力的缺陷不能独自进入社会、在成年后为母亲尽养老之责。即便是作为普通母亲完成人生历程的养育体验,也时刻笼罩在自己离开后无法照料孩子的担忧下。
由此,我们展开了对这种极端的母职情境的审视,并进一步追问:对于患病孩子的母亲们,她们是如何以极大的自我剥削和自我牺牲,投入就其目标而言极度绝望的母职实践?在患病孩子母亲养育的历程中,我们发现,她们虽看似是被家庭与观念推选而出、在特定的性别分工与母职期待下成为了孩子生活中最重要的养育者,但实际上,她们即便并未受到外在环境的肯定,也展现出了充足的内在动力,以“为孩子好”为目标践行母职。做称职的母亲并非仅仅为了满足某种社会处境下的角色要求,而受到无法安定的内在认同驱使。
通过追溯她们的养育历程,我们发现,养育期待的转变是实现母职重构关键的方式。早期康复时,母亲们经历密集康复的尝试,直到逐渐接受,特殊疾病不可治愈,且需要一生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矫正与共存。青春期教育阶段,学校的环境则使母亲们对孩子的期待不断被“正常化”的权威挑战,在社会污名下将养育期待向更加个体化的方向调试。患病孩子的母亲们所实践母职,或许在社会意义上是注定失败和无望的,但也促使我们反思“做母亲”的方式:贯彻所谓社会期待并不是养育的必然。患病孩子母亲们所参照的养育标准从社会化,变为医学化和群体化的,最后变得个体化,经历了漫长甚至持续一生的努力。在理性养育中所做出的那些“非理性”的决策,揭示出密集养育之下母亲们底层的情感,也正是当下“密集母职”研究中未获足够重视的面向。
在有关自我与孩子的边界、期待与现实的选择中,母亲们展现出外在建构的观念底层更寻常的情感动力。“做母亲”意义的建构,来自于与患病孩子共处的经验。困境时刻交织在疾病之中,而感受到的爱与作为本能的爱则成为了超出制度性母职约束性的话语,构成了母亲们主观且独特的经验,促使母亲们在自己的生活理解和实践养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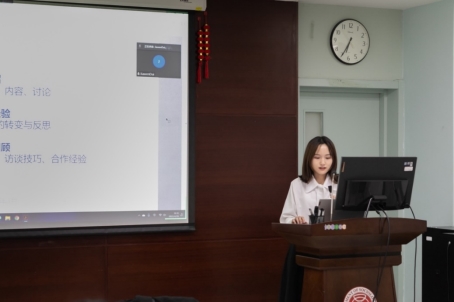
研究历程
在2020年9月-2021年8月期间,我们进行了三次集中的田野调查并对文章进行修改。
初入田野时,我们的研究兴趣在患病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家庭的照料模式,希望探究在相对有限的福利水平下,家庭成员如何协作完成患病孩子的照料,以维持家庭的有序运转。从诸多新闻报道中窥见这类家庭冰山一角的故事,并怀着最初的好奇和模糊的研究问题进入田野。然而,随着田野调查的展开,我们提出的研究问题遇到了阻碍:我们的受访者大多拒绝或回避了关注其他家庭成员的问题,而主要与我们分享自己在照料患病孩子过程中的体验,使我们难以在互动的视角下展开对疾病照料的深入描述。但与此同时,初步的田野也使我们走出文献与资料,对患病群体有了更全面、真实的了解。我们的受访者以照料患病孩子的父母为主,他们对于患病群体现状的介绍、私人照料经验的分享给我们许多的启发,使我们得以在孩子生命历程的视角下理解父母的照料投入,并逐渐确认了两个作为线索的研究关注:一是疾病污名,即作为孩子照料主体的父母所感知的污名体验,以及与之相伴的、父母在社会互动中面临的压力和阻力,如他人的误解、家庭的排斥、社会的拒绝。二是父母角色,即随着孩子幼年确诊、年龄增长、患病状况的变化,父母在照料过程中对“理想父母”看法的转变。

戴嘉雯:
第一阶段以污名和父母角色为主体的研究告一段落后,我们继续以患病孩子家庭为对象进行挑战杯的写作。初入田野、面对纷繁田野收获的无措直接体现在了第一阶段的写作中,我们完成的文章缺乏聚焦,多为经验描述,理论分析不足。基于对第一阶段研究的反思,我们开始了第二阶段的田野和文献阅读。在过去的访谈中我们发现,相比于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更多的母亲全身心地投入到患病孩子的照料中,因孩子终身无法治愈的疾病改变自己的职业安排和人生选择。因此,我们进一步聚焦于母亲养育患病孩子、安排家庭运作的策略。第二阶段,我们主要关注到中产母亲群体养育实践的特殊之处:面对患病孩子庞大的照料需求,母亲们往往不得不调整职业安排,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应对。但一部分中产母亲面对这样的母职两难,采取加入、组织乃至建立家长共同体的方式,既通过共同体纾解照料压力、获取康复知识,又通过共同体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第二阶段的写作,我们以母亲与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诠释患病孩子养育策略的支点,描述共同体如何作为母亲们连接私人养育与公共生活、养育孩子与自我实现的途径,以对话国内中产母职与特殊母职经验的相关研究。
第一、二阶段的研究后,我们对已有的田野和研究进行反思:共同体作为中产阶级母亲对抗母职两难的策略,并不足以在更大的母亲群体中推广。更重要的是,照料患病孩子的母亲们为我们提供了探讨特殊母职的视角,但我们既有的文章尚未凸显出疾病在养育经验中的特殊表现,而更多地将其视为加剧养育负担的原因。疾病全方位地改变了亲子关系和照料经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所研究疾病的特殊性,并未使亲子关系转变为单纯的疾病照料模式,而是与普通的养育具有高度的可对话性。基于此,我们尝试在第三阶段的田野调查中更多聚焦于母亲与孩子在日常相处、照料过程中的经验,并拓展来自不同阶层、教育背景、家庭环境的母亲受访者,从中寻找共性;同时,回顾有关母职和密集母职的相关研究,最终以患病孩子母亲的养育历程为视角展开文章主要内容的讨论。
陈一宁:
最后,我们希望分享田野中的困境与反思。面对许多受访者长时间养育经验的叙述,故事写作、生命历程梳理等梳理、剖析、重组田野材料的方法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对于患病孩子照料经验的询问涉及诸多敏感和隐私,提出的问题经常无法得到想要的回答,而是回避和沉默。我们认为,保持道德的警觉和对受访者的尊重最为重要,但同时也需要保持好奇、接受等待和理解沉默。通过一年断断续续的田野与修改,我们也深感学术研究的不易,并更多地理解,“具体的事实才是理论的出发点,述说者应该有勇气表现出自己思考中的艰难、矛盾”。
博士评议

宋丹丹(博士):
嘉雯和一宁的田野做了很长时间,从田野小班教学课、挑战杯到实习报告,面对疫情以及患病儿童家庭这个群体,她们在联系田野对象、进入田野、获取信任、恪守伦理上遇到更多困难,她们的真诚和努力让我很钦佩。
这个研究讨论的是患病儿童的妈妈们,但似乎讲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母亲和孩子的稳固连结和不可割舍的情感。为了回应这一观点,首先需要回顾她们根据三次田野写成的三篇文章的结论和推进。第一个阶段的报告重点放在失范的概念上:母亲养育孩子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抵御外界的污名,对养育细节和层次挖掘不够。第二个阶段则强调共同体的概念:妈妈们会自发组织康复小组和团体,从共同体中寻找到规范。外在的力量不可忽视,但不能完全视为动机、伦理和行为的来源。第三个阶段是重构母亲的规范,即妈妈如何找回生活的信心。细致地贴近和理解在养育孩子时因为被孩子们触动,而抛弃了外部的期待、更贴近孩子的生活。
她们的结论提示我们反思如今思考母职的方式。密集母职的概念在近年的研究中非常热门,需要回到概念本身,看它被提出的历史和立场。
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hood)由Hays于1965年在其专著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中正式提出,意指一种“以孩子为中心、专家指导、情感投入、劳动密集、经济昂贵的母亲的养育方式”。这本来是由个案堆叠起来的概念,描述的对象可能有局限性,但被作者视为非常广泛的现象,国内学者引进这个概念时忽视了它的诸多定语,使之像“内卷”一样被泛化了。要重新思考作者希望解答的问题:高度现代化、市场化、个人利益驱动化的美国社会,为什么还存在这种无私的、不理性的爱?她主张密集母职是一种被逐渐建构出来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它所表露出的情感是不自然、不合理的,所以她提出密集母职是为了反思密集母职。
她们能够反思现有研究对情感关注不够,把母亲情感转变的瞬间和体验拉回来,是很宝贵的。患病儿童的母亲甚至可以为正常家庭亲职提供一种反思,因为她们无限贴近孩子的现实,而不是把期待强加于孩子。
文献综述中提到吴小英总结的学界对“做母亲”对于女性而言的悖论:要么是对母亲的剥削,要么是母亲的赋权,都过于强调作为母亲本身得到或失去了什么,没有回到被研究者的立场关心生活细节。她们的论文挑战的不是密集母职本身,而是母职的意识形态。上述回应不是为母亲极大的牺牲正当化,而是要回到研究者的生活、抛却先入的立场。
对于密集母职的特殊性,还需要关于阶层的讨论。文中没有直接讨论低阶层患病儿童家庭的养育,论点落在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联结使得母亲会根据孩子建立个体化的养育模式和养育期待,这种倾向应当是共通的。但低阶层患病儿童家庭的一些细节需要被发现,或许她们体现的是与中产阶层母亲不同的密集样态。我个人觉得密集不是一种能力而是内在倾向。
另外需要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异,借助西方患病孩子养育方式(较健全的社会托管体系)进行对比,才能突出中国的特点:无限制的家庭照料责任。至于是否有共享的观念和文化,需要重新回到概念。
提问与回答

提问:本研究中父亲的一方很缺失,是因为问不到还是不愿意回答?
回答:我们整体接触机构的负责人和患儿家庭中大多数是母亲在负责照顾,父亲相对缺失。我们尝试从母亲的口中描摹养育中的家庭分工,但她们很难直接回应,基本上在讲自己,不愿意把整个家庭展现出来。
提问:患病孩子的母亲在养育中缺乏正向反馈,因此亲子关系不简单是投入—回报。这些母亲真的不在求什么吗,还是在以其他人无法体会的方式获得正向反馈?她们如何一步步鼓起继续培养的勇气?
回答:她们的内在激励在于在细微的日常中慢慢看到孩子微小的进步,这种激励是很难被外人理解的。另外,母亲发现自己在的时候孩子会更安静、有安全感,这种细微的差异让她们会认识到自己是特别的、为孩子所需要的。
提问:这些母亲如何理解疾病,是否会用宗教或者“命”的方式来解释?
回答:国外很多研究会提到宗教对于疾病认同的作用。我们接触的家长会有“这就是命”的说法,但没有宗教,可能是中西文化的差异。
提问:进入共同体和孤军奋战的母亲在养育方式上是否有明显差别?如果说情感连结是普遍的,那么共同体对于养育过程而言有多重要?
回答:我们接触到一位低收入阶层的母亲,其生活被养育孩子所占据以至没有时间参加,另外学历较低、缺乏知识进入群体,也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这表现出阶层文化的差异、养育安排带来的局限性。中产母亲介入共同体的方式不能描摹整个群体,所以侧重共同体之外养育历程的共通性。共同体起到知识指导的作用,但与孩子相处过程中的情感是共同体无法干预的。
提问:从情感连结反对男权社会构建母职的政治正确,情感连结是否有被建构的面向?父母双方谁来全职,母亲选择全职照顾意味着孩子与母亲的相处时间增加,可能本身会导致情感连结就会更进一步。我们不能仅停留在情感连结来反对之前的政治正确。
回答(宋丹丹):在目前文化中,母亲往往承担照顾的角色,这会增加感情连结,这个反思是很对的。我的讲法是不能只按照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讨论情感连结。当然,养育中为什么是母亲更能感到种种触动?当然这个田野中父亲展现较少,可能父亲会显示出更复杂的面向。
老师评议

刘爱玉老师:
这篇文章来自田野调查小班教学课程。现在她们讲得非常有逻辑、有学者范,当时我们最早听到的是几个故事,都困惑能做出什么样的研究。中期时要将社会学理论与田野现实对接,从理想母亲想到密集母职的概念,照亮了研究,田老师和凌老师也做了补充。她们执行力特别强,阅读了相关文献,把这些理论概念跟经验事实结合起来。一年多看她们的成长特别开心。
密集母职问题还有美国梦、阶层再生产的背景,与美国早年社会分工相关:父亲工具性、母亲情感性。在密集母职预设的中产阶级中,男人养家、女人持家,有中产阶级地位的焦虑、地位再生产的冲动,最重要的是孩子可以通过努力培养出来。本研究面临的情境和密集母职非常不一样。密集母职的定义太多就是没说清楚,是否可以称为绩优主义的密集母职?要通过家庭的分工和努力让孩子在绩优体系中胜出。
中国社会中家庭性别分工有一套伦理规则:贤妻良母、严父慈母,但这是针对正常孩子来讲的。对于患病儿童,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为“道德化的母职”。通常讲的母职是情感性、表达性,或者科学主义的(也是绩优的)。评价中国母亲的价值标准在于能不能生正常的、能传宗接代的儿子,不正常的孩子会导致母亲受到社群中其他人的道德判断。拯救母亲的价值,就是把残疾孩子养成正常孩子,道德化的母职获得了自我的价值回报。分享知识看似专业主义,实际上背后有道德伦理。最后,这个研究要回到反思密集母职的概念上,要放到父亲缺场、伦理建构的面上。

田耕老师:
我很欣赏这个研究,因为它本身是很密集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以母亲照顾者的密集情感表达作为研究对象。最初的版本像规范的社会学研究,带有很多对家庭结构的分析,后果是把母职天然地放到了以家庭为中心的结构中。
当时我产生的直觉性问题:这些特别的孩子本应受到比较均衡的家庭照顾,但为了照顾必须分工和分离,这些孩子恰恰会把生活和情感放在母亲身上。这种“密集”有无奈的社会分工,会加剧本来中国家庭教养的困难(丧偶式教育),但这是为更大的责任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必须首先理解这种艰难的母职的形成过程。她们需要平衡不正常状态,并在感情中消化,消化的过程体现在孩子康复和成长的过程中的亲子关系中。母亲对不正常的母职本身的认知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密集母职是过度滥用的概念,与中国的现实有关,但也缺失她们这样的视角。密集母职不是因为对权力的要求,这些母亲某种意义上是牺牲者,但并非不公平社会制度的牺牲者,应注意到母亲情感中的复杂面向。相比于丧偶式教育中的受害者心态,这里的密集母职是非常不同的。启发在于:密集是什么意思,从何而来?这对当事人的影响很大,需要区分。因此,我们能够比较理解嘉雯她们的选择。这个研究不仅过程上是本科生研究的楷模,思考上也有很有潜力。

凌鹏老师:
这项研究为什么一方面困难,一方面又很重要?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最困难的往往是最不那么社会的地方。在社会层面上交流没那么困难,但她们的研究是在社会下面讨论。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但人不仅是由社会组成的,人还有本身,心理、感情等无法言说的东西。如果人与人之间无法进行表层的社会交流,它们究竟是什么?这篇文章之所以如此深入,是因为能够剥掉社会表层的东西,直接进入深层。
本研究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关注失范和污名化(社会性的问题),第二阶段关注共同体的支持(交流的问题),第三阶段则是母亲作为人/主体如何理解自己——这些母亲是多重身份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母亲与孩子的关系确立自我。福柯正是从最不社会的地方(精神病院)讨论社会最根本的问题。要努力尝试不是单纯从社会表层做社会学研究,个人不仅仅是社会角色,而且在底层有很深的东西,甚至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但能达到这一层次就是非常好的研究,因为能接触到支撑社会的根本。
从社会污名、共同体进入情感性关联是逐步深入的过程,之后恰恰要返回去:如何处理家庭问题(父亲的不在场)?母亲的情感作为核心已经探到底,如何从核心出发把上面看到的问题重新包容进去?母职这个概念对于当代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密集母职的概念虽然在学术界受到批判,但已经成为家长教育小孩的常识,母亲们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但一定会受到这种影响,比如如何做母亲、处理家庭关系。要从这个核心问题重新容纳社会层面的东西。比如父亲的位置不显现,恰恰证明他非常重要或者有影响。
面对访谈对象的沉默肯定不能逼问,但这个问题可能是非常关键的,比如父亲的角色,他与孩子的关系可能非常重要,但母亲不愿意说。如何把这些敏感问题和沉默解释出来,是扩展和丰富问题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