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基层治理的数智转型》
基层治理的数智转型
邱泽奇 等著
ISBN:978-7-5228-5517-2
2025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数智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创新性应用,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分四编探讨了基层治理从传统的属地治理到前沿的数智治理的转变。
具体而言,本书以分析典型的“枫桥经验”开篇,探讨数智治理工具在各地实践中的适配性创新应用,并进一步探索数智治理综合服务平台在基层治理中的本地化实践,最后聚焦省级层面数智治理综合系统部署和治理的数智转型实践,探寻基层治理数智转型的理论路径与实践策略。之所以称“数智转型”而不是“数智化转型”,是因为这一过程还有很多变数。
尽管如此,对基层治理数智转型的讨论,不只是对实践的记录,更有助于把握基层治理的发展方向,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作者简介
邱泽奇,湖北沔阳(今仙桃)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社会发展与治理、组织变迁、社会研究方法、城乡社会学等;代表性成果有《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中国人的习惯》、《朋友在先——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案例研究》和《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等著作,以及《技术与组织:多学科研究格局与社会学关注》、《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合著,一作)、《回到连通性——社会网络研究的历史转向》(合著,一作)、《技术与组织的互构——以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为例》等论文。
目录
第一编 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与数智转型尝试
第一章 “枫桥经验”的传承与创新
一 从“枫桥经验”到“新枫桥经验”的发展背景
二 “枫桥经验”的历史沿革
三 呼之欲出的“新枫桥经验”:在传统与创新的转折点上
四 “新枫桥经验”的特征:多主体参与+多渠道交互
五 对“新枫桥经验”的总结与思考
第二章 “村民说事”制度的机制与局限
一 缘起:回应危机管理的需求
二 组织化进程:面向日常的制度建设
三 方家岙村的旅游致富路:谁在说事?
四 旭拱岙村的风气整顿经:为谁说事?
五 从危机管理到日常事务治理:“村民说事”制度有效性的限度
第三章 村民参与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一 研究背景
二 上海市嘉定区北管村的乡村治理创新实践
三 重庆市合川区香龙镇“智慧乡村、自治小院”建设
四 总结与思考
第二编 数智治理工具应用的地方性探索
第四章 数智治理融合的泰达街道
一 泰达街道网格化管理实践
二 街道网格化管理社区典范:华纳社区的治理实践
三 网格化模式下智慧治理服务
四 总结与思考
第五章 “沈阳新社区”与宝山“社区通”
一 线上治理工具应用于基层治理的时代背景
二 “互联网+社区”的“沈阳新社区”政务微信服务平台
三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社区通”智能化乡村治理实践
四 总结与思考
第六章 传统城郊社区治理的数智转型
一 城市社区基层治理智能化发展的宏观背景
二 周家渡街道社会治理基础
三 周家渡街道基层治理的信息化体系建设
四 周家渡街道基层治理智能化特色项目建设方案
第三编 数智治理综合服务平台的基层治理实践
第七章 为乡村振兴搭建数字平台
一 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愿景与“痛点”
二 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尝试与局限
三 “为村”作为打通基层治理痛点的工具:超越与想象
四 “为村”典型实践案例:共性与差异
五 短评:数字乡村,未来已来
第八章 茶市村从贫困村到“为村明星”的数智化转型
一 “为村”的湘西实践:扶贫难题下的“扶智”探索
二 茶市“为村”的发展:贫困农业村的“为村”“逆袭”
三 茶市的“为村”经验:多主体参与+多领域应用
四 变革及其原动力:技术驱动下的“人气”汇聚
五 总结:自上而下的技术渗透与自下而上的潜能释放
第九章 邛崃市的基层共治
一 邛崃“为村”的应用场景:增强“连通性”
二 “全域为村”的组织机制
三 “为村”平台与乡村治理实践
四 “为村”平台与乡村产业发展
五 总结:“全域为村”的平台优势
第十章 阳江市基层治理的数智转型尝试
一 “党建为村”的宏观背景
二 村庄治理的“痛点”和“为村”的介入——以丰垌村为例
三 基层政府工作的“痛点”与“为村”的可能
四 技术提供方的“痛点”和“为村”的错位
五 总结与政策建议
第十一章 上海青村镇的“为村”实践
一 大都市郊区的“为村”应用场景
二 青村镇的“为村”项目定位
三 不同村庄差异化的“为村”实践
四 用户特征与产品逻辑的张力
五 总结:发达地区乡村治理中的“为村”应用特征
第十二章 电商扶贫的孟河村探索
一 孟河村的脱贫之路
二 数字经济:城乡联动、电商扶贫
三 数字治理:干部引路、群众跟进
四 总结:以数字技术凝聚全村
第四编 乡村数智治理的地区案例
第十三章 “川善治”:基层治理的省域实践
一 引言
二 “川善治”平台在四川省的推广运用情况
三 典型市(州)运用“川善治”平台的治理实践
四 “川善治”平台在四川的应用成效
五 问题与建议
第十四章 “川善治”平台的达州市实践
一 区域概况
二 “川善治”平台的应用背景与定位
三 达州市推广运用“川善治”平台的目标、政策与成效
四 “川善治”平台落地乡村的具体应用实践
五 总结与讨论
第十五章 “好德行”平台的德阳市实践
一 “好德行”平台应用背景
二 城乡治理中的问题与数字赋能入口
三 推广“好德行”平台的做法与成效
四 社区治理中的数字化实践
五 数字赋能德阳市城乡治理的综合路径
第十六章 “川善治”平台的自贡市实践
一 自贡市“川善治”平台应用的目标与地区效果
二 自贡市地区概况
三 自贡市“川善治”平台的基层治理实践
四 对自贡市应用“川善治”平台的思考与反思
第十七章 “川善治”平台的泸州市实践
一 泸州市乡村基层治理中的痛点、难点、堵点
二 数字技术引入泸州市乡村治理的过程
三 数字技术赋能泸州市乡村基层治理的效果
四 数字技术工具作用于基层治理的机制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序言
中国乡村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却在2010年前后悄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也由此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数智治理是应对这一挑战诸多尝试中的一种。在国家政策主导下,各地多样化的努力汇聚了社会广泛参与的智慧,这是中国乡村变迁值得铭记的。
几千年来,乡村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体。第一,乡村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高。1952年,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7%;1980年的占比还有82%(国家统计局,1983:104)。第二,第一产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高。在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比超过50%;到1980年,这一占比超过了30%(国家统计局,1998:56)。尽管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在下降,但其重要性却丝毫未减。国家粮食安全、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收入和社会保障等,都依赖第一产业。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始终都在强调农业、农村、农民的重要性。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提出“国家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并明确规定了保障农民权益的原则;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并明确指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地位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动摇;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首次将“三农”问题明确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重中之重”表述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取消农业税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并将新农村建设目标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其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同时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三步走”目标,即到2020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千万工程”)为核心方法论,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在国家发展战略中,从农业的基础地位,到“三农”的重中之重,再到“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三农”的重要性从来没有改变过。
在“三农”中,乡村治理是关键组成部分,“治理有效”也是乡村振兴总要求五个维度中的一维。乡村治理,听起来只是乡村的事儿,事实上却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历史地观察,乡村先于国家而存在。换句话说,对中国而言,乡村是国家建构的基层。郡县制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国家体制的建成,对此,钱穆先生有充分的论述。可是,在国家建成之前,乡村早在存在。据杜佑《通典·食货三》记载:“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同,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陵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于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夫始分之于井则地著,计之于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这段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早在周王朝建立之前,乡村已经是一个组织化社会实体,乡土社会、乡村治理已经存在,有规制、有目标、有功能、有管理;而国家,则历经夏、商、周,迟至秦始皇一统江山后采用郡县制才实现了组织化。也就是说,乡村不是被带入国家的;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已经存在的乡村构成的,早在秦始皇选择以郡县制建国时,乡村就已经是建构国家可以选择的依据和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乡村的基石性并不意味着乡村的独立性、自治性。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历史上,皇权不下县,乡村是完全自治的乡村。我想这是一种误解,至少是某种程度的误解。其误解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皇权的界定。假如我们把皇权界定为政府官员,那么的确,皇帝不曾任命过县级以下的官员。可是,国家权力不只有官员一种表达形态。税赋、徭役、司法,算不算国家权力?当然算。如此,皇权不仅下县,而且下到了每一个人。《史记·商君列传》有“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说的就是国家权力对家庭经营方式的规定。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2002年出土的秦简清楚地记载了秦灭楚后设立迁陵县,县辖三乡(张新超,2024)。县政府的职责之一是编户齐民。秦始皇选择的郡县制,其实是秦统一中国之前一些国家比如楚国早已开展的社会实践。
独立的乡村一旦被纳入国家组织体系,其治理便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在秦始皇之后,每一个历史时期虽然都对郡县制进行微调,如从汉唐到明清都有限度地保留了分封制,可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从家户到国家的系统化、组织化构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构成了国家的基层。
把基层治理置于国家治理中考量,可以站在国家立场观察基层治理的特征。从实行郡县制开始,历史上的基层治理虽有变迁,但基本构架不曾改变,起点即如中国历史文献里不断重复的,是以井田制为形制的组织化的社会互助体系。在没有国家之前,基层治理原本是社会治理。在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后,基层治理大致经历了两次历史性变革。
第一次是基层治理的封国化。在组织化基层的基础上,周王朝的基层治理是在封国基层基础上的国家化治理。如果我们认可历史文献的记载,便可以说,没有基层社会就没有封国,没有封国自然也就没有周王朝,国家便是空的。基层是与封国互为参照的基层,而不是与周王朝互为参照的基层。准确地说,周王朝没有基层,自然没有基层治理。我们可以将基层治理的这一变化理解为井田制之后的第一次历史性变革。
第二次是基层治理的国家化。秦一统天下,废分封,置郡县;废井田,开阡陌,意味着把周的封国体制改为系统化组织起来的郡县体制。以郡县制为形制的组织架构彻底删除了国家与基层之间的中间主体,把国家直接建立在基层之上,形成由家户到国家的系统化组织。换句话说,秦始皇建立的国家是高度系统化、组织化的国家,是把每一个人、每一块土地都纳入组织体系的国家。组织化国家不仅刻画了国家的组织形态,即系统性,也刻画了国家的权力属性,即中央/国家与基层的确存在权力分配,不过,这是总体主体与从属主体的权力分配,而不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平行主体的权力分配。如此,国家治理不再是平行权力甚至不是协商性权力之间的治理,基层治理自然成为国家治理的基层。
正是中央/国家与基层的系统性和组织性构成了中国基层与非中国基层的本质差异,即中国基层是中央/国家的基础,基层失,则中央/国家去;基层稳,则中央/国家固;基层兴,则中央/国家荣。运用这个逻辑,可以解释在秦之后的中国,虽有改朝换代,却再也没有突破由秦开创、由汉唐微调的国家体制及中央/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基层治理始终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层治理没有发展变迁。历史地观察,基层治理的确发生过一些调整,不过不是在形制层次,而是在形制稳定前提下的技术层次。例如,在基层治理中,国家与家庭的分工。在基层封国化之前,基层互助即自治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秦汉乡亭制中便产生了自治与法治的分工,如国家负责法治,基层负责乡情、乡亲及生产互助、丧葬嫁娶、守望相助、贫穷相济等。抽象地说,国家更多地负责公共事务,如规则治理、道德建设等,其他非公共事务依然由基层负责。宋朝的新变化是把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治理变革为组织化治理,且在治理内容上有了更加清晰的分工,如国家的基层治理更加关注安全、税收、教育、社会保障等国家和民生两类事务,其他的依然由基层自治。
不过,上述讨论有一个更大的前提,即存在乡土社会。国家是乡土的,社会亦是乡土的,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对乡土性的不同维度进行了刻画和分析,为读者呈现了一副清晰的乡土图景。乡土性的根本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国家经济的根本在农业。
问题是:这一根本在2010年前后发生了历史性改变。一如前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以户籍人口计算的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82.1%;2000年虽然将统计口径改为常住人口,但乡村人口占比还有63.8%;到2005年,依然有57.0%;直到2010年城乡人口占比才几乎相等。2015年乡村人口占比进一步下降为43.7%,2020年再次下降为36.1%,2024年又下降为36.1%。直白地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尤其是21世纪的头十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结构的乡土性。在人口数量意义上,中国从乡土中国变成了城市中国。
同样是在过去40多年间,中国经济的乡土性也消失了。一如前述,尽管农业的基础地位没有改变,但农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却在不断下降。以国家统计局(1991:24~25)数据为依据,1990年一二三产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分别为28.4%、44.3%、27.2%。在工农业总值中,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重分别为24.3%、37.4%、38.3%。在农业总产值中,农、林、牧、副、渔业的比重分别为58.8%、4.3%、25.6%、6.2%、5.4%。1997年乡镇企业改制,乡村工业向两端分化,也没有改变农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比下降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的数据,2010年,在三次产业结构演化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降到了个位数;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3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2.8∶1。
综合多个权威来源的数据,从农户收入视角观察,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31%;2013年增加至943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户收入第一大来源;到2023年工资性收入达21691元,占比达42%,在东部地区如常州占比则高达61%。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户收入中的占比,2000年为63%,2023年下降为34%。转移性收入占比从2000年的约8%上升至2023年的21%;财产性收入变化不大,从200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23年的2.5%。
归纳而言,2010年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城乡关系属性的分水岭。一方面,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改变了人口规模结构的城乡格局;另一方面,非农经济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计来源,即使是生活在乡村的人口,其生计的主要支撑也不再来自农业。由此带来的一个本质性变化是:乡村,在事实上,留给了那些留守在乡村的人口。那么,他们是什么人呢?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人们戏称“386199部队”。
综合多来源数据,2000年留守妇女约4000万人,留守儿童约2699万人,留守老人约3500万人;2010年留守妇女约4700万人,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2013年留守老人约5000万人;2023年留守妇女约2500万人,留守儿童约4177万人,留守老人约5500万人。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在规模上呈现妇女、儿童和老人三个群体数量大体均衡的格局,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留守人口开始向老幼两端汇聚,呈现极老、极幼化趋势,从中部到西部趋势逐渐清晰。
乡村人口和经济变革的这种格局带来的是乡村治理从未遇到过的场景:一方面,乡村依然是国家治理基石,可是构成基石的人口却离开了乡村;另一方面,乡村依然是乡村人口的乡村,可留在乡村的人口不再是农户的当家人。在乡村社会有决策能力的人不在乡村工作和生活,留在乡村的人却缺乏决策能力,甚至在家庭中缺少决策权力。不仅如此,农业虽是乡村人口生计的底线保障,却不再是主要收入来源。
本书的意图不在于提出高深的理论、阐述复杂的道理,而在于试图记录中国由乡土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进程带给乡村治理的挑战,生活在乡村的干部和群众的创新与实践,以及有责任感的企业面对乡村治理难题时的技术赋能。
本书的内容组织隐含了以下考量。第一,继承与创新。乡村治理是中国治理智慧的载体。实践中的一些智慧总可以在历史中寻到踪迹,寻到社会合法性,比如,“枫桥经验”沿袭了自治传统,却又从来不是照搬照抄,食古不化,人们总是会在现实中找到创新机会并进行创新;又如,“村民说事”回应了村民对参与村庄事务的诉求。第二,创新与实践。乡村治理也是中国治理创新的实验地。实践中的一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不得已的创新。比如,村里的事务需要村民参与决策,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在家里的人又做不了主,怎么办?村“两委”不得不运用微信群。面对数不过来的诸多微信群,企业想:能不能把村里的事务梳理一下,建一个服务平台?这便有了数字技术的引入。第三,实践与发展。乡村治理还是中国治理实践的发展地。随着实践的深入,观念在更新,技术在迭代,效能在提升,组织在完善。比如,运用数字技术进行乡村治理,提升效能的路径是体系化,“好德行”“川善治”便一步步地提升了治理层级,把基层治理发展为以省为统筹单位的体系化治理,这是基层治理在秦之后的一次革命性发展。
为了呈现这些考量,本书在编排上遵循了基层治理实践循序渐进和迭代发展的线索,收录了从2017年我们接触到乡村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之后调研的各类案例,分四编探讨基层治理从传统的属地治理到前沿的数智治理的发展。之所以称“数智转型”而不是“数智化转型”,是因为笔者预判这一过程还有很多变数。第一编分析从传统“枫桥经验”到“村民说事”的转变;第二编探讨数智治理工具在各地实践中分散的适配性应用,城乡都有案例;第三编引入治理平台的应用,不同层次亦有案例;第四编聚焦省级层次的系统部署和数智转型实践。本书希望通过从传统到数智的基层治理实践变革与发展,各地城乡因地制宜的适配性调整,以及在省级层次的系统化部署,探讨基层治理的数智转型。
这是一本案例刻画与探索的书。在调研中,我们得到了案例地区的政府、村“两委”、村民、企业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在案例访谈、人员访问和实地走访中,我们得到了相关机构和人员的理解,请恕我们无法一一列出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名字。这本书是团队合作的产物,依据时间顺序,参与调查的人员有:马宇民、张樹沁、黄诗曼、高正予、乔天宇、黑若琳、杨乾宇、任碧萱、周彦、李佳、张燕、于健宁、李澄一、徐婉婷、马力、李由君、杨玉鑫、李佳锦、覃雨蓉、张茂元、谢子龙、许庆红、王旭辉、彭斯琦、冀星、李铮、徐燕婷、李思妍、庞雨倩、张蕴洁、宋远航、毕文芬等。如果有遗漏,还请原谅。参与案例写作的主要人员有:张燕、于健宁、李佳、黄诗曼、李澄一、徐燕婷、周彦、张茂元、张蕴洁、李铮、李佳锦、宋远航等。在编辑过程中,需要把不同时间成稿的案例汇集在一起,核对事实时还需回头与案例地点或案例调查者和对象进行沟通交流,为此,李铮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此,笔者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当然,文责自负。书中出现的任何问题,皆由笔者一人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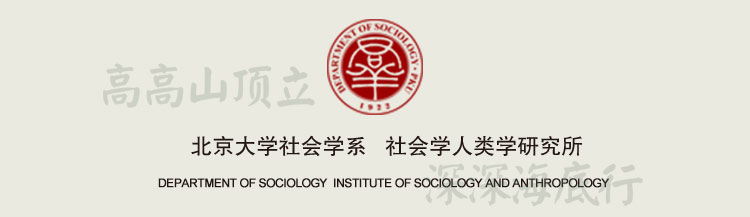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