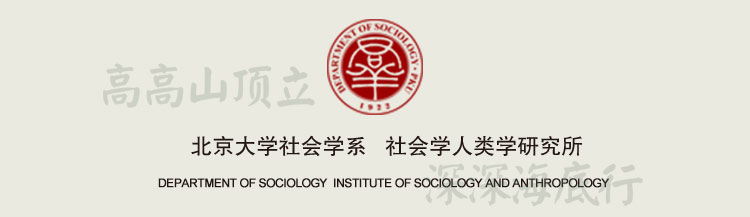黄华节 中国古代社会的休假制度
编者按
黄石,1901年生,广东人,黄华节是他的笔名。据学者考证,他约于1923年进入广州白鹤洞协和神科大学读书,在校期间跟随校长龚约翰(Dr. John S. Kunkle)研究宗教史,受许地山先生的影响开始研究神话学和礼俗史,他还在燕京大学研究院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宗教和民俗研究,后又“南归”,具体情形不详。黄石始终是一名活跃的民俗学研究者。例如1932年,黄石曾与许地山、江绍原、吴文藻、李安宅一起,共同为编纂《野蛮生活史》系列在报纸上“征求同工”,这说明他与具有燕京大学背景的宗教学、人类学学者群体保持着稳定的学术联系。
黄华节于此文中详梳中国古代官家之休假制度与庶民之休假习俗之流变,以显示中华文化中对勤劳与逸乐调和的一种尝试,更以休假之不彻底、不多得、不普及显示对“闲暇”重视不足的传统,从而主张将勤劳与逸乐同作人生要素、文化动能看待,追求对悠闲暇豫的保护。
中国古代社会的休假制度
黄华节
人类须要工作,也需要休息;须要勤劳,也需要逸乐。作工与休息,勤劳与逸乐,是一种生活的两方面,不但没有冲突,并且相互完成,休息是恢复疲劳的必要条件,逸乐是增长劳动效能的主要方法,两者同是人生的要素,同是文化的动能。
悠闲暇豫给予人生,给予文化的好处,可得而言者,约有数端。第一,它让人有反省的机会。今天我作这件事,应不应该,对不对?假如不该,不对,下次可别再错了。假如做得很对,就记在心上,以后再遇到同样的情景,照样处理就得了,必如此然后有经验,有改进,有进步。第二,它予人以从容预拟将来的计划。假如一个人终日忙着从手到口的工作,当然不会有深长的远见,伟大的抱负,和精密的计划,结果是把一部血肉的机器用到残破之日,就扔入墟墓里,如是而已。第三,它予人以发展精神生活的便利,使人生超越不完全的现实,而向美满的前途迈步。宗教,音乐,诗歌,绘画,雕刻,伦理,哲学思想,乃至于科学的发现与发明,都是“有闲阶级”创造出来的。
由个人生活,扩大到民族生活,以上几条律例,仍是一样的有效。现代人大都崇拜西洋的文化,大家又都知道西洋文化导源于希腊,但为什么希腊人能够在几千年前,就创造出那般精深博大的哲学与科学,那般瑰丽完美的艺术与文学?原因是一部人,有“剩余的精力”,有“安闲的时间”,并且还有“享乐的态度”去做那些“饥不可为食,寒不可为衣”的玩艺儿。只这一个显例,就可以证明我在篇首提出的论断了。现让我总结一句,“有闲”是创造文化,提高生活的基要条件。
现在说到我们中华民族,原来是一个文明的古国,然而一到近代,和异样的文化接触,便着着遭逢失败,处处露出破绽。在清之季世,人们早觉的物质文化不如人,可是仍用精神文明胜于彼以自慰,及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再次觉悟,连精神文明,也赶不上人家了!此何以故?原因虽多,而中国历来的统制生活态度,和上古时代的生存状况,实为一个有力的主因。
不错,我中华民族确是得天独厚,获得一块沃衍的平原,做生存活动的根据地,然而我们在上古所占的地盘——黄河流域,和埃及巴比伦,希腊诸国一经比较,便瞠乎其后了。我们最初所占的领土,地位处在寒带,虽然不是苞封冰雪,但一年总有四分一乃至三分一的寒冷季节;虽然,有黄河的灌溉,但水利不很调剂得当,要竭力设法调节水量,故古之治者,以水利作为政的要务,是以“治”字“法”字俱从水旁;我们的地盘,距海很远,而山岭纵错,有了这几个,以及旁的地理和物质的原因,华族在古代生活都是刻苦劬劳的。况且在初开草莱的时候,筚路蓝缕,谋图生存,更非易事。
此种生活的状态,无形中便形成一种刻苦劬劳,注重实用的民族精神。春秋时代的三大学派,除道家一派,因发生于异样的一境——江汉流域——而主张乐生外,儒墨二家的思想,俱极力发挥这种精神。墨家“以自若为极”,以九年在外三过家门不入的夏禹为理想的人格;儒家以兢兢业业为美德,以晏安逸乐为大戒,致有“宴安鸩毒”的成训。其理想的人格,如尧舜等,俱是“朝乾夕惕”的勤劬人物。
一方面有物质的原因为发动;他方面又有圣贤的教训为推进,故中国自有史以来,几于上下一致以劳动为美德,以逸乐为大戒,以安舒暇豫为败德之原。所以历代的上下人等,俱不重视休息。既不重视休息,像西洋那种七日一休假的制度,便要等到很晚才发生,并且发生之后,也并非普及与全体,只是少数人所享的特权。
“休假”或“假期”二语,在中国典籍书史上,最先发现于《史记》史迁记李园事春申君事云:“李园事春申君事,谒归故失期则假告”。“假告”即今人之所谓“告假”或“请假”,是为“假”字在中国文书上的第一次发见。宋明的考证家,据此断言战国之时,已有休假,是为休息之始。如作事物纪原的高承,引史记文句之后,接住边说:“……则告假,已见于战国”。(见原书卷一)又明人王三聘,考证休假的起源,其主张与论据,均同于高承,谓告假始于战国。
今按,古之所谓“假告”,即几之所谓“告假”,而告假与休假,性质虽同,意义却不一样。休假是指公务本来照常,但从公者得主管机构或职司的许可,得暂离职守若干时之谓。李圆的“告假”,属于第二义而不属于第一义,故不得据以断言战国时已有休假之例。并且李圆事春申君,为家臣,为门客,偶因故失期而回,始告于春申君以求原谅,严格说来,也不得谓之“请假”,充其量只可谓补“请假”而已。然而“假”之一字,此为第一次发见,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认为开后世给假于士大夫的先例,这纵然不能作为“休假制度”的缘起,至少可以算作一个滥觞。
.png)
高承《事物纪原》。图片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
我国真正的休假制度,当始于汉。在这个时代,不但百官有休假的事实,抑且法律上亦有给假的明文。高承《事物纪原》指出汉律的规制,及士大夫“休假”的实例道:“汉律,吏得五日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休沐”二字,是我国历代沿用表示休止工作,暂时燕息的成语,直至西洋俗习规制输入华土,士大夫亦援用固有的成语,以表示西洋的七曜一周的例假,称日曜日为“休沐日”。“言休息以洗浴也”,这个“休沐”的定义,确与近代休假的观念很相近,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断言汉代的“五日一休沐”制,是中国休假的正式起源。我说“正式”,指其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成为国家颁布的法制也。
.png)
《大清顺治二年七政经纬躔度时宪历》,顺治元年七月初二清廷采用汤若望以西洋新法所修之历法,并由多尔衮建议,易名为“时宪”,以符合朝廷“宪天乂民”的至意。清朝定制,每年十月初一日颁行次年历书。七政即水、金、日、月、火、土、木七个在一定轨道上运行的星体。躔度即是用以标志日月星辰在天空运行的度数。古人把周天分为60度,划分若干区域,以辨别日月星辰的方位。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曰“吏得五日一休沐”,则显然休沐不是公卿大夫专享的特权,举凡为政从公者——即前时所谓“吃衙门饭”,而今时所谓“机关办事”——都有享受五日一休沐的法权利了。这是很有趣的,现代苏俄五日一周制的,不图在数千年前,早已施行于我国了。
高王二子,俱异口同声说,“然则休沐始于汉。”(并见同上)惟有明之杂考家罗欣,则把休假制度的起源,推早一点,说始自嬴秦,并且其动机也不是体恤群臣的劳苦,反倒是苛待属僚的恶例。他在所著的《物原》上说:“古考,卿大夫退朝则归家,无日夜待命台寺者。秦始制抑臣之体制,公卿非五日一休沐,则不敢归社。”按秦一天下,政治上起一大改革,废旧制新。与宗周以前的封建制度,迥然大异,当统一初成,新的政治制度尚未完全确立之时,政务纷繁,万机丛脞,卿大夫“日夜待命台寺”,自是应时势而不得不然的要求,始皇此举,正所以显其励行改革的努力,不得谓之“抑臣之礼制”。但待命台寺的公卿大夫,得五日一休沐而归舍,则图治之中,仍寓体恤之意。
从我们现代的立场看来,这种制度,似乎比古者夙夜在公,全无休沐,犹较胜一筹。因为古之卿大夫虽然“退朝则归家”,无须“待命台寺”,但归家之后,仍得日夕奉公,不容懈怠,并且国君一旦宣召,虽非入朝时间,也得匆遽奉命。“君命召,不俟驾而行”,虽然是一个勇于负责的孔老夫子个人的话,却可以代表古代乡大夫的劳碌终日。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也许是假想的传说,但公卿冢宰的朝夕劳瘁确然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么,秦制乡大夫“日夜待命台寺”,表面上是苦差,然而五日之中,有一日得归家从容休沐,松了肩膊上的责任,岂非此胜于彼?
诚如罗欣所说,则五日一休沐之制,创制于秦,则不自汉始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秦制只限于在朝内值班待命的卿大夫,并非一般从公者都沐此特殊恩典,这是秦制于汉律的大不同处,我们说秦制式促成休沐制度的确立的近因则可,说是休沐制的正式起源则不可。质言之,秦的办法只是休假制的肇端罢了。汉的政制法律,几全部承袭秦之遗制,但不是完全因袭,其间却有所更改。休沐制亦然,汉仿秦例,而制成定律,许在公者每五,日休沐一天。这是法制;不是恩惠;这是一切“吏”得共同福利,不是卿大夫的特权。所以我们虽不否定秦时五日休沐的事实,却也不能因此动摇休假制度成立于汉朝的论断。
五日一休假,照现代的科学眼光看来,本来是最适当的办法,但这个古制,到了唐朝,便大加变革,把奉公的时日延长,把休沐的次数缩减,由五日一休沐,变为十日一休假了。这就是说,一月六日的例假,骤减了一半,改为一月三日的公假。因此就把一个月画分为三旬。近世称三旬为“三澣”,俗作“三浣”, 澣有上中下的区别,就是唐代“休沐”的遗迹。据杂考家的考据,这个制度创于高宗永徽三年,(西纪后六五三)其原本的记载,见于唐会要,今将诸书的征引,以补参证。
唐会要:永徽三年二月十日,以天下无虞,百司务简,每至旬假,许不亲事,以宽百寮休沐。然则休沐始于汉,其以休旬则始于唐也。
.png)
明代陈洪绶《晞发图》 。图片来源:中国三峡博物馆。
此高承之说也,证据确凿,当极可靠。观此,知休假制度到了唐代,不但有了定制,并且还有专名,称为“旬假”。再据“许不视事,以宽百寮休浴”两句看来,则到旬假这一天,简直是庶政暂停,光景与现时没有多大分别了。这种制度,似比汉制更进一步:汉律仅言“吏得五日一休沐”,据高承的注解,也仅说,“言休息以洗休沐”,却未明言百官可不视事,所以唐代休假次数虽比汉代为少,但实质上却比汉律切实得多了。
唐代的“旬假”制度,明之大儒杨慎(升菴)考证更详,并援文学为做证。他在所著谭苑醒醐卷四上面说: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为上旬中旬下旬,盖本唐制十日一休假。故韦应物诗云:“九日驰驱一日闲”。白乐天诗:“公假月三旬。”然此乃唐制,而今犹袭用之,则无谓矣。
韦白之诗句,不但为唐代“旬休”制的一个有力佐证,并且更从而表现出唐代的特征。“九日驰驱一日闲”,可见“旬休”是整天休息不办公事的。“公假月三旬”,则唐人已有更“休沐日”的旧名,而称为“公假”或“公假日”,与今之所谓“公众例假”,词义都相近了。升菴最末一句说,不单匡正俗谬,并且还有一个重要暗示,即唐代的公假制,明代已废止了,故曰“则无谓矣”。
清人吕种玉亦尝略考“三澣”的名源,但犯了一点错误。他在所著《言鲭》下卷说:
今人纪月,上旬中旬下旬,称上澣中澣下澣,此起于汉唐侍从官,每十日假一日,休沐浣衣,三旬之中三浣,故以此名。澣同浣。
吕氏之说,除提示“澣”与“浣”通义之外,于考证上没有什么贡献。最大的错误,在说“汉唐侍从官,每十日假一日”。汉制五日一休沐,已见高承所引的汉律,唐律“百寮”公同休假,亦载在唐会要,并不限于“侍从官”。吕氏之言,殊失之于考。
唐代的休假制,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最进步、最实际,并且与现代最类同。除了上述的一月三次的公众例假外,唐代还有一种喜庆式的假期,与今日国庆纪念日同性质,尤其与节日相似,这样的假期,见于历书上者,一年之中,均有三天,即正月晦日,上巳,重九三个节期是也。这三个假日,不单为例假,并上带有娱乐性质,唐书云:
贞元(德宗年号)四年九月二日敕:“今方隅无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胜地追赏为乐。仍各赐钱,以充宴会。”
此正史记载明文,当可新人,又据别的记载,则除上述三个喜庆游乐的假日之外,还有三月十五老君诞这一天,亦为唐人的假期。
唐以正月晦,三月三,九月九为假日,任百官游赏,又三月十五老君诞,亦定为假日。
宋人李上交虽然没有给我们开示唐人休假的日期,但他有几句话,说明唐代假日——包括旬假,节假——一般的特征和规例,也很重要,足以使我们更了解唐制的特色。彼于其所选的《近事会元》卷三上面说:
唐明皇开元二十五年诏:旬节休假,并不须入曹司,任追胜赏乐。
以上所提的四个节假,三月三,九月九二者,大家都容易明白。三月三是上巳节,自先秦以降,代代踵行,至今犹有遗俗;尤以唐时一代,最为重视,作者已另有《上巳修楔考》一文,论述颇详,兹不复赘。读者如果检阅唐时诗杜甫的《丽人行》,就可以得到一幅四民行乐图的逼真活跃景象。九月九是重阳佳节,也是大家知道的。
惟有正月晦这个节假,因现代已废,大家许不大清楚朝廷所以给假的原因。按隋杜宝《玉烛宝典》有云:“元日至晦月三十日,士女湔裳于水正,以为度厄。”(见卷一)观此正月晦为节日,性质与上巳同,自隋已然,唐朝特承前代的遗制而已。再往上推,则隋以前,南北朝间,亦早已有之。例如北齐书有这么的一句说:“君臣于正月三十日祓降,放舟游宴。”然则唐人以此日为公众节假,“任百官游赏”,有由来了。
考正月晦之所以演变为节假,实由于一段神话,及俗人于次日送穷度厄的迷信风俗。《四时宝镜》云:“高阳氏子好衣食麋,正月晦日死。世作麋,弃破衣,三十日祀于苍,曰除贫。”这固然是一个神话的解释,荒诞不可据。但由此推考,正月晦为一年的第一次月晦,古人对于太阳的四变象,朔望弦晦,甚为重视,这种迷信观念,从初民遗存下来,且为世界“七曜一周制”所从的共同根源,因初民视月出四变象,对于人间有不可思议的威力,故于此日停止工作,而视为“禁日”,此即所谓“安息日”的起源,我国上古时代有没有这种迷信风俗,不易确考。
.png)
宋《缂丝上元婴戏图轴》局部。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但一年中的第一次月圆,与第一次月晦,自来均视为重大的乾象,因以此两日为节假,休止工作,前者谓之“上元节”或“元宵节”,后者尚没有专名,但泛称为“正月晦”而已,这两个节日,初时本为停息诸工的“禁日”。观《玉烛宝典》所记“士女湔裳度厄”一语,即可知其本质;其后失原义,乃转变为追亲游赏的节假。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故唐朝典章,亦不能不沿古之遗风,承绝此日为休假的节日,任百官不视事,而追赏为乐。
末了,说到老君诞日,唐人之所以定为节假的原因,按道教自汉代成立以后,中国两晋人士之趋尚,在社会上已成一大势力,同时对于道教思想的教祖——太上老君李耳,亦产生大批莫可诘究的神话传说。唐承六朝之后,更兼以老君姓李,与帝王同宗,因推崇专奉,过于他人。故此连政府也承认老君传说的诞辰——三月十五为节假,与正晦——上巳,重九同为追赏行乐的假期。
我国古代官家的例假、节假,光景大略如右。然而以上所指出的休假制度,都是为士大夫阶级而设的,一般老百姓小百姓不与焉。这一般劳力食人者,终岁劳动,迄无休止!漫说五日一休沐,即十日一假,亦不可得。那么,难道他们真的一年做足三百六十日的工作吗?是又不然。
平民阶级的休假,没有一定,大抵一年不过几天。凡年终重要的节假,就是民众共享的假日。劳苦民众,应该有几天休息的期间,让他们痛痛快快的乐一乐,这条原则,虽主张勤俭力作的儒家祖师,也不吝予以明白的承认。《礼记》载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很可以表明儒家对于民众的主见。《杂记下》说: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蜡, 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儒家对于调节人生的劳逸的主见,“一张一弛”四字就是工作与休假的大原理。张是紧张,义即劳动;弛是弛缓,义即逸乐。据这一段话看来,孔子就是事实上承认逸乐是人生所必需的,虽“朝乾夕惕”的文武圣王,犹弗能“张而不弛”,劳而不休。故王者于民众农劳之假,以休息之,举行“八蜡”之礼,使民饮酒忻乐,尽一日之欢。按“蜡”是一种祭礼,于十二月农功已毕之时举行,与腊祭大同小异,或曰“蜡”即“腊”也。三代时谓之“八腊”。苏东坡把“蜡”祭的意义与性质即功用,说得很清楚,他说:
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义,亦曰不徒戏而已矣。……子贡观蜡而不悦,孔子譬之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盖为是也。”
姑勿论“蜡”与“腊”的意义与异同到底是怎样,但从礼记的描写,可以确知这是古人一个“狂欢”的节期,与杨恽在报“孙会宗书”所描写“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傲:酒后耳热,仰天扶缶而呼呜呜”的情景很相类似。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中国士大夫阶级,从秦汉以降,就有法定的“例假”,以资休息;唯独庶民阶级,则大都是终岁作苦,只年中有三几个节期,是让他们喘息的恩日,这和士大夫阶级比起来,就差得太远了。中国文化从来握在士大夫阶级手里,这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文稿整理:林上
推送编辑:苟钟月、陈立采
审核:凌鹏
节选文字整理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资料室所藏《社会研究》。为方便阅读,在尊重历史文献原貌的基础上,对部分文章段落进行了重新划分,对部分标点使用进行了调整;所有的修改不损害原意、不改变原文风格、不破坏时代通行表达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