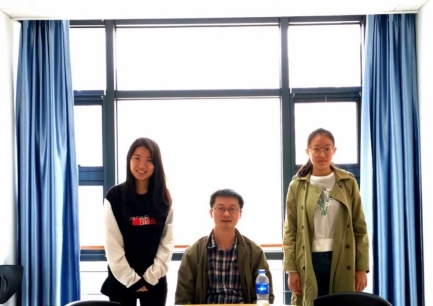郭金华:让学术重返生活
郭金华:让学术重返生活
供稿:系团委学术实践部、《五音》编辑部
关于教学
郭老师以前做过研究生的班主任,但现在是第一次做本科班的班主任,您对这个新角色有什么感受吗?

同学们经常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从中学时代明确的单一目标,到现在选择和机会爆炸性地增多,这个过程有时候反而是非常让人难受的,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我觉得从没得选择到有选择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同学们在中学阶段可能目标相对明确,实际上这也可以理解成没有目标,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分数高一点,能考个好的大学。但是到大学之后,虽然分数也很重要,但是可能已经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可能朝自己那方面发展。但是很多时候,同学们在中学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对自己兴趣特长的关注和认识,可能大多数同学还没有想过这些。然后进入大学之后,突然在你没有这种明确自我意识的前提下,让你再做这些选择,这就是大家感到比较困惑和迷茫的地方,这是我的理解。
目前您开设的本科生课程包括《民族志研究方法》、《社会人类学(与高丙中教授合上)》以及研究生课程《医学人类学专题》、《中外人类学史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原著选读(与朱晓阳教授合上)》,请您大致介绍一下这些课的侧重点,以及您对这些课有没有建议选修的顺序?
在为本科生开设的两门课程中,《民族志研究方法》是我工作以来较早开设的针对本科生的一门选修课。跟高老师合开的《社会人类学》实际上是最近几年才接手的,属于人类学的必修课。按照本系的安排,《社会人类学》是放在《民族志研究方法》之前的,是对人类学的一个概念性的基础介绍课程。
另外一个就是《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这个题目听起来像一个人类学专业的课程,但是我在讲法上会比较注意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普适性,尽量使之适应社会学专业同学的运用。我在课程内容安排上比较偏重社会学专业或者是其他的社会科学专业都可能会运用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里面的一部分。目前系里安排是在三年级开设研究方法,我觉得这个安排还是比较妥当,正好在同学们做研究论文之前设置这门课程。但是很多时候也感觉好像是不是稍微有点晚。我在讲授这门课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感受:一方面大家对一个具体的研究来讲好像还是缺乏问题意识,然后就是研究方案的设计考虑得不够周全,导致大家在不太完善的方案基础上进行资料收集,最后的分析就必然暴露出很多局限。我在这个课上主要是希望给大家一种意识:研究还是需要首先有一个明确的研究问题,然后在这个研究问题的基础上,能够制定一个相对来说周详一点的方案,再去执行这个研究。我觉得给大家灌输这样一个意识其实是挺重要的。很多时候我参加论文答辩时都感觉到很多研究确实是存在一些缺陷,如果在最开始的研究设计中注意一下的话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硕士生的课程基本上都是采取偏重大家一起读书、汇报讨论的这种形式。在为硕士生开设的课程中,《中外人类学史研究》是必修,《医学人类学专题》是限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原著选读》是跟朱老师合开的。《中外人类学史研究》基本上是按照人类学的几大传统来介绍,《医学人类学专题》算是一个分支人类学的介绍,也是我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
目前基本上是这些,但是今年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因为从下半年开始我们要招收人类学的本科生了,所以一些本科生的课程和硕士生的课程都可能要做一个相应的调整。
关于治学
您在哈佛大学就读人类学博士期间,有没有什么让您现在依然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那时候记忆深刻的事也是挺多的。我到哈佛是9月12日,之前一天是9·11。我倒完时差以后去见导师,在跟导师的第一次聊天以及后面的学习中,慢慢感受到西方的人类学,尤其从英法的传统来讲,总是建立在一个自我和他者之间对立的基础上,我们借由理解他者来实现对自我的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建构出一种他者,也就是我们会强调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不同。我们不断地去描写各种不同,不同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刻板印象,但实际上是不是真得有那么不同呢?其实虽然我们和他们可能是有些区别,但还是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后来我在上学过程中也慢慢体会到这一点。那时候,去留学之前我们这边信息很闭塞,我们有很多关于美国社会的想象,比如他们的青年人很独立,上学费用都自己打工挣钱得来的。但是去了之后和他们慢慢熟悉起来,就觉得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刚开学的时候,美国的父母也是从全国各地开着车送小孩到校报到。我也看见父母陪着小孩买生活用品,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互动方式也是互相讨价还价,小孩要买,父母说这个不能买,和我们的代际关系好像也差不太多。这些日常生活的体会跟学术研究都有些关系。去美国之前,我们就想象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但是去了之后就发现确实有不同,但是在这些不同之外,还是有很多有共性的地方。我们有时候强调文化差异有多大,其实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普遍性要多一点。这种意识在我们面对现在这种社会、这个时代可能尤为重要。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越来越频繁,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冲突,但还是需要一个大家能够共处在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要去寻找文化之间的共性、相似性,而不是去不停地强调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多么不同。
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跟精神病艾滋病相关的污名,您当时是怎样想到这个题目,又是怎样寻找田野地点的呢?
在哈佛读书的头两年是上专业课程,之后会有一个资格考试,这个考试通过的话,你就可以开始写你的研究计划了。那时候应该是2003、2004年左右,当时正是国内讨论艾滋病最热的时候,我感觉回去做相关主题的研究应该会比较方便一点。
关于寻找田野地点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我虽然对这个题目有兴趣,但是之前确实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群体以及整个医疗体系,所以一开始研究方案设计纯粹是纸上谈兵,就想按照一般的套路,比如说可以找城市、农村不同的地方,或是从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来选研究地点,从而确保研究的代表性。但是后来回国做田野之后就发现一个问题,一个是这个研究主题相对敏感,而且这些群体本身也很敏感,比较反感外面的人来接触他们,后来有朋友提供建议说,或许可以从志愿者、从医疗机构入手。然后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和路径,通过他们介绍,先通过志愿组织医疗机构,然后接触到这些患者。这个经历其实也告诉我:研究方案可以设计,但是事实上等到实践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它是不可行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意味着研究方案就不重要了呢?倒也不能这么理解。研究方案可能是提供了一种框架,或者说是从逻辑上来让你思考整个研究的完整性、充分性,但是有时候还是要考虑到现实的问题,有过多次的研究经历之后,你会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在后面的研究中,就知道这个方案怎么能够既保证逻辑上的合理性,又保证现实中的可行性。如果换了一个研究群体,可能之前那种方法就未必能用了,还需要重新调整。也就是说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从而保持了开放性。
在做田野的过程中,有哪些让您印象很深刻的人和事呢?
在我做田野的过程中,有两个研究对象去世了。这两个人都是艾滋病患者,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云南。我在北京的田野地点是在一个医院。当时我就跟上班一样,每天早上准时上班,下午到点下班。时间长了以后我跟医生还有这些患者都比较熟悉了。因为跟一些比较核心的患者的接触,我才能够进入到整个患者群体。在北京做研究大概有半年之后,得到一个机会去了云南大理的一个医院继续做研究。我在云南待了大概有六七个月然后回到北京,在回学校写论文之前北京就有一个患者去世了。那时候还是挺意外的。
我对于艾滋病的印象和理解实际上也经过了一个变化。在研究之前我也是挺害怕的,跟一般人的认识是差不太多的,因为之前没有什么接触,也觉得挺可怕的,觉得艾滋病就跟死亡有关;后来跟艾滋病人接触之后,我慢慢地知道艾滋病实际上只要服药的话,病人是可以长期生存的,但是他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艾滋病病毒攻击免疫系统,然后病人的身体免疫力下降,就会容易得病,当时我在田野里面已经习得认为这个病不会那么容易死。当我听到其他的病人跟我说有一个人死了,就觉得还是挺震惊的。在云南期间也有一个患者死掉,这个患者是吸毒后感染,其实在感染艾滋病之前,他基本上是被家里给抛弃了。大家都很痛恨那些吸毒的人,去云南之前,北京的患者就跟我讲,说你去云南一定要小心,那些患者跟北京的患者不一样,他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你都不能相信。这可以反映整个社会对于吸毒者的一种印象和看法。这个患者年纪也不小了,40多岁的时候就从家里被赶出来。我当时在云南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做两个事情,一个是做艾滋病研究,另外一个是在帮波士顿大学做一个研究项目,这个研究项目本身就要求我每个月做一些调查访问。患者每个月会来取药,然后我们就顺便做一个访问调查。这个患者发病住院十多天,因为他家里不管他,医生打电话去他家里让家里交一下住院费,家里都拒绝说这个人已经跟他们没有关系了。所以他的住院费都是科室在垫付,等他稍微好转一些就不得不请他出院回家休养。在他回家之前,我记得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跟他有一个访谈,也算是聊天,聊聊他家里的事还有自己的生活经验,这个访谈给我的印象很深刻。过了周末到星期一早上,等我到医院去的时候,护士就告诉我说这个人死掉了,因为这个人有癫痫,他回家以后只有自己一个人,他晚上发病,没有人在旁边帮忙,就这样死掉了。
这是田野期间我印象最深刻或者说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两个人。艾滋病人死亡的原因在我的理解里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不了解疾病之前,死亡跟疾病是有直接关系的;后来发现死亡实际上跟艾滋病没有太大关系,而跟疾病的社会内涵有更大的关系。吸毒感染艾滋病的人被家人赶出来,等到发生状况的时候,没有家人在旁边,就容易出问题。
您在整个田野的过程里面遇到过怎样的困难呢?
其实第一个困难应该是无法开始。我在北京首次接触这些病人的时候,是经过一个大学的老师介绍进入的。她介绍我去了之后,医生觉得我可以在那里待着,但是患者都躲得我远远的,觉得说医生同意你来,但是我们没有同意你来。于是他们就不理我,就不跟我说话。这个过程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里面管它叫进入,进入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你得到现场,第二个是说你得让别人接纳你。
当时我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他们不跟我说话,我也不跟他们说话,但是我会帮他们做事情,但是我当时并不是有意识地在想怎么来做,这跟我自己的性格可能有关系,就是我需要等一等看一看,然后才会行动。实际上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患者其实以前也见过很多志愿者、研究者,他们大多数来看看患者长什么样就走了。但是我在那确实帮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我整个大半年的时间都帮他们做事情,什么邮寄药物啊、修电脑啊、写项目申请书啊。这是我能够被患者群体接纳的重要原因。当时因为艾滋病抗病毒的药物是国家免费发放的,但是免费发放的前提是每个患者要在地方的疾控中心登记,有很多患者害怕一登记就暴露了,于是他不愿意去登记,宁愿去自己掏钱买,他们把钱汇到北京的医院,然后买了药我们就要给他寄,当时我就常常跑医院去旁边的邮局给患者邮寄这些药物。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到半个月的时间,这些患者觉得我来了也不瞎问。患者其实很反感别人问问题,因为有很多人上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感染的?这是他们最不喜欢的问题。但是我从来不问,只是帮他们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过了半个月之后,他们慢慢地开始接受我,一起吃饭一起玩啊都很正常。这是一个跟研究对象建立一种相互信任关系的过程。
第二个在云南的案例是说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带来的后果可能不完全是正面的。去云南的时候我是以一种在当地医院的项目管理人的身份去的,所以科室的医生对我是很有一些戒备的,他们觉得我是北京派来监督他们的。当我和其中一些医生相处的比较融洽,关系比较熟络之后,其实会在医生群体内部会造成一种紧张关系。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一书堪称几乎是任何集体记忆研究的必引书,这本书的中译本是您和毕然老师合译的,您当时为什么注意到了集体记忆的问题?
在硕士阶段,我参与了孙立平老师等主持的一个口述史项目。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发现,不同的人来回忆同一段历史经历,他们的讲法都有一些出入,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景下对于同一段经历的叙述也存在相互冲突。我们就试图理解不同的叙述究竟是如何共存的。翻译这本书实际上是整个口述史研究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您在《与疾病相关的污名——以中国的精神疾病和艾滋污名为例》一文中从污名化主体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污名现象,在文章中也提出过“是否可以摆脱从特定个体或人群出发理解污名的桎梏,而是从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出发来理解污名”的问题,污名好像随处可见,有时似乎是我们借以界定自身的方式,分类诚然是简化认知的方式,但分类是否可以绕过污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关于污名的研究有一个倾向就是把污名还原为特定群体的某种特质。这种研究路径会把污名附着在这群人上,认为污名是由这群人自身的问题造成的。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污名的时候,自然就会问到是什么人会去歧视这些人呢?有很多解释都顺延着这个脉络,比较流行的解释是无知的人会产生歧视,后来又有研究认为是社会变迁、道德水平下降产生很多缺乏社会同情心的人,这些人会产生歧视,还有的解释是说某种特定的文化会产生歧视。后来我就觉得这么来分析污名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把前面的逻辑又重新用了一遍:认为歧视别人的那些人自身也是有问题的,他们歧视别人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或者缺乏道德,或者是因为某种文化特质。其实这么想是在重复使用污名化的逻辑,总是觉得是某一些人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污名化其实具有普遍性。
这种感受当然也跟我自己的研究经历有关系。我也是在研究过程中才意识到污名这个问题可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跟特定的疾病没有必然关系,疾病可能只是某种社会关系的载体。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被歧视、被污名化的群体太多了,这背后实际上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和面对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而我们如何看待和面对这些人实际上是以某种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不管是性别歧视,还是几十年前的身份歧视,到现在因为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也可能会产生歧视。实际上这是一种普遍的感受和体验,我们总是把这个归咎于某些特定的他者,觉得这是他们的问题,跟我没关系。简单地说,我们之所以污名化某个群体,其实是觉得他们违背了我们认同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和原则,所以就会将他们打入另册,排斥他们。我觉得我们需要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污名这个问题,总之它是建立在人们对于差异的感知和评价基础上的,而且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您在《中国老龄化的全球定位和中国老龄化研究的问题与出路》一文中说道“中国老龄化研究缺乏针对个体老化过程和社会老龄化过程特征的研究。中国目前的老年医学研究仍然主要关注与老年相关的疾病,而老年社会学则侧重于老年人生活质量、养老模式研究”。在上一篇文章中其实也可以看到您对于不可拆解的“个体”本身的关注,是否隐含了您并不认为个体是特征的集合,您怎么看待特征与个体本身的关系呢?
污名化就是特征吞噬了作为整体的人的过程,就是说人们用对某个特征的印象替代了对整个人的认知。我觉得在现代医学里这个趋势是非常突出的。医学人类学的观点认为现代医学存在一个问题,疾病和人的分离,也就是作为特征的疾病和作为患者的人的分离。医疗越来越聚焦处理疾病,而相对忽略了患病的人。现代医学总是想把病和人区隔开来处理,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特征和个体的关系我觉得其实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不可避免会经由某些特征去认识人,也就是说我们是经由某种特征来理解一个人。但是这种认知模式也是存在问题的,污名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您最近在做怎样的研究,读哪些书呢?
我读书比较乱七八糟一点,有我的专业领域医学人类学这边的,然后最近几年因为教人类学史的课,也逼迫自己读各种人类学史的材料。我所受的人类学训练也是很局限的,一方面我的训练是属于美国人类学传统的,另一方面我的研究是偏重于医疗这一领域。从我个人感觉来说,阅读人类学史可以帮助我对于人类学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这对我来说还是帮助很大的,比如说各种理论和方法当时是在什么样背景下出现的,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不同的研究者如何尝试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除了种种知识点之外,研究人类学史还可以给我们提供思维方式上的学习和训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跟同学们聊天的时候,常跟同学们说上课如果只是把课程当做了解知识点来看待的话,可能效果不会那么大。听一门课,听完之后,你总觉得在这个课上学到了以前没听说过的东西,但这个东西你很容易会感到无聊,因为这些知识点虽然你经历了从不知道到知道的过程,但是可能你未必对它感兴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无聊。我老跟他们说,其实你更多需要去考虑的是这些知识点背后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去试图理解某人提出某些概念,提出某些理论的过程,或者说反思这些学者是什么样的人,他当时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他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后果又是怎样的?这也是思维的一种训练,通过去理解其他研究者他们是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这个思考是大有助益的。不管你以后是不是做研究,这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很重要,而且这么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和路径,有可能会提出完全不同的理解,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在不同的思维方式上做这种比较。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才可能找到适合你的或者说你擅长的那样一种思维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在大学学习中至关重要的。
现场同学提问
您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会和研究对象建立起关系,慢慢熟悉之后可能会有情感上的联系,这个会不会影响最后研究的客观性?您会不会感觉长时间的田野会跟生活割裂开来呢?
你要说完全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对人类学来说,客观主观可能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人类学当然最初是按照自然科学研究来打造自身,以自然科学为模板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研究人的科学。但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人跟自然科学的对象还是不一样的,这个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自然科学的那一套来做。
但是人类学的研究仍然还是要追求科学性、有效性、客观性。大家在阅读、评价特定研究的过程中,还是会去讨论这些问题。当然我觉得客观和主观可能并没有一个截然的界限,我要跟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的话,我当然可以做到不投入情感,这也许是客观的,但也可能是很主观的,因为我有可能把自己的想象投射到我的研究对象上去理解他。就是说这种投入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研究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跟人打交道,时间长了,必然会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有一种情感的投入在里面。但是很多时候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需要暂时忘掉自己研究者的身份,跟研究对象混成一片,但是等到研究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实际上是需要提醒自己研究者的身份的,这并不是说我不跟这些人做朋友,或者说我要跟他保持距离,而是说你要有这种意识,所以研究者的这种自我意识可能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开始的时候不要老想着自己是一个研究者,那样的话你就很难进入到这个群体。但是到最后你如果把自己变成研究对象的一员的话,不是不可以,但是你的研究就可能废掉了,如果你还想继续完成这个研究,实际上是需要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提醒自己你的研究者身份。
在研究里面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跟你在日常生活中一样,你会交一些很好的朋友,也会获得一些敌人。人类学讲田野方法的时候总是去强调我们跟研究对象建立这种亲密的熟悉的关系,但其实这都是教科书上讲的一个方面,根本就不讲有敌人怎么办?有人就是不能跟你成为朋友,你怎么办?其实这都是发生过的事情,每个研究过程中都发生,只是很多人不把它写出来罢了,都去写那些成功的那些好的东西,田野里面有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变成亲密的朋友呢?
想请问老师,我今年寒假的时候去做调研,到了之后发现实地去访谈的时候,农民的语言反馈又是很不成体系的,我们的研究周期又很短,最后结果就不知道怎样成一个体系化的思路。
本科生这个阶段去做调查,可能主要还是找找研究的感觉,要去体验一下做研究怎么回事,跟人访谈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你们都很着急,但其实不用着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多参加多参与,研究的感觉是要靠一些经历来积累。另外一个也不要把日常生活跟研究分得太开了,你在日常生活里也跟人聊天,不能把研究看得太脱离日常生活。你刚才说农民说的全是一些比较片段的内容,这就是日常生活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你俩日常聊天,在我听来也可能是很破碎的,但是你们不会觉得破碎。为什么?因为你们俩谈话的背景我是不知道的。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话是不用说的,因为双方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另一个要注意的是,你要明白自己跟你的研究对象之间是有一些分别的,你们经过长期训练,知道什么叫逻辑,什么叫条理,如何准确表达。这都是学术训练教给你们的。但这套语言跟日常生活的语言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