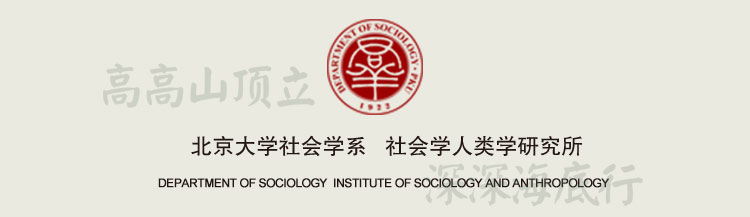童世駿:約翰·羅爾斯的“規則”概念及其與當代中國語境的相關性
童世駿(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
摘要:羅爾斯最早引起學術界重视的論文是〈兩個規則概念〉,在其中他不同意把规則當作過去行動的“概括”,而主張把它看作是對某種社會實踐方式或社會建制的定義。羅爾斯後來的學術工作主要就是研究作為一個規則體系的社會建制:一方面研究社會基本結構的構成性规則,另一方面研究社會成员對由這些規則所定義的社會建制的態度。從羅爾斯早期那篇論文的“規則”概念和文章最後提出的兩個問題出發,我們可以對羅爾斯後來發展的正義論做出很有意思的解讀。這種解讀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諸如羅爾斯理論中義務論成分與功利論成分之間關係那樣的理論問題,並且有助於理解羅爾斯政治哲學與當代中國語境的相關性——它不僅僅與在中國主張和捍衞某個“主義”有關,而且與解釋和解決當代中國面臨的一些“問题”有關。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中説“正義是社會建制的首要德性”,而社會建制則是“一個公開的規則體系,它規定職務和地位,連同它們的權利、義務、權力和豁免等。”不難看出,在羅爾斯的正義論與規則論之間存在着内在聯繫。羅爾斯的規則論即使不是他的正義論之建構的主要基礎,也可以説是他的正義論之得到更好理解的其中一個角度。
本文擬對羅爾斯哲學中的“規則”概念作大致梳理,其目的不僅是爲了更好地理解羅爾斯的規則論思想本身,而且是爲了從此出發,一方面更好地理解羅爾斯正義論的一些重要特點,另一方面更好地理解中國當前社會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現象——近年來,“規則”一詞在我國各種場合出現頻率之高,可以説已經成了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關鍵字之一了。
.png)
“規則”概念在羅爾斯的博士論文中就已經提到,但從該博士論文的公開發表的那部分(题爲“一個倫理學抉擇程式綱要”[1951])來看,羅爾斯並没有對這個概念作詳細討論,而只是説:“我們可以把規則——它與原則相反——理解爲這樣一些準則(maxims),它們表達的是把原則運用於一些被公認的和經常出現的場合。規則的遵守、日常生活中對規則的訴諸,對這些進行辯護,就是要表明規則是這樣一種準則。”
羅爾斯最早引起學術界重視的是一篇题爲〈兩個規則概念〉(1955)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羅爾斯分析了兩種規則觀,也就是兩個他所謂的“規則概念”。其中一個規則概念似乎也就是他在上述論文中自己的觀點——規則是原則(在那文章中主要是功利原則)對特殊情形之運用的結果:
它以如下方式來看待規則:我們假定每個人都通過運用功利原則來決定他在特定情形下將做甚麼;我們還假定不同人們將以同樣方式來決定同樣的特殊情形,並且與那些先前決定過的情形相類似的情形會重複出現。這樣,就會出現這樣情況:在同樣種類的情形中,同樣的決定或者是由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刻做出的,或者是由不同的人在相同時刻做出的。如果一種情形出現的頻率足夠高,我們就提出制訂一個規則來覆蓋那種情形。
羅爾斯把這種規則觀稱爲“概括的規則觀”(the summary view of rules),因爲這個觀點把規則看作是由直接運用功利原則於特殊事例而達到的過去種種決定的概括。羅爾斯認爲,規則作這樣的理解,就是“把它們詮釋爲一些準則(maxims),詮釋爲一些單憑經驗的方法(rules of thumb)。”

圖1: John Rawls 圖片來源:The Harvard Gazette。
但是,羅爾斯這篇文章的主题恰恰是對這種規則觀的批判。羅爾斯的理由主要有兩個。
第一,這種規則觀無法解釋社會中人們對彼此行動的確定預期和在此基礎之上的相互合作是如何可能的。把規則理解基於過去經驗的實踐準則,意味着每個人原則上始終有資格對一條規則的正確性進行重新考慮,並對在一特定事例中遵行規則是否恰當提出質問。規則的必要性似乎僅僅在於:要不然的話,對功利原則的運用可能效率不高;在一個合理功利主義者的社會中,規則是不必要的,因爲在那樣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有足夠的能力直接把功利原則運用於具體事例中。但問題是,如果每個人原則上都可以就事論事地確定基於功利原則做甚麼,常常會導致混亂,而設法通過預測别人會怎麼行動?協調行爲的努力,就很可能因此而失敗。
第二,這種“概括的規則觀”也不符合人們通常對像“懲罰”和“許諾”這樣的社會實踐方式的理解。根據這種把規則當作過去經驗之概括的觀點,一個人在特定情形下要不要遵守諾言,歸根結底取決於他把功利原則運用於這個情形所得出的結論,也就是説他是否認爲在這種情形下遵守諾言將實現總體上的最大的善。但是,羅爾斯認爲,這種觀點顯然是與人們遵守諾言的義務的理解相矛盾的。因爲,一個不被遵守的諾言,根本就不是一個諾言——“遵守諾言”這條規則是内在於“許諾”這種實踐方式的;許下一個諾言意味着不管怎麼樣它都是要被遵守的,除非在許諾時已經直接或隱含地承認了一些例外的情況。
與這種“概括的規則觀”相反,羅爾斯提出他所謂“實踐方式的規則概念”(the practice conception of rules)。羅爾斯寫道:
根據這種觀點,規則被理解爲對一種實踐方式(apractice)的定義……一種實踐方式的特徵就在於:教人如何從事這種實踐方式意味着教人掌握定義它的那些規則,並且訴諸這些規則來糾正從事該實踐方式的人們的行爲。從事一種實踐方式的人們承認那些規則是對這種實踐方式做出定義的。那些規則不能被簡單地當作對從事該實踐方式的人們事實上如何行爲的描述:並不能簡單地説他們之行動的方式就好像他們在遵守那些規則一樣。
因此,對於實踐方式的概念具有根本意義的是,規則是被公開地知道和理解是具有定義性質的;同樣具有根本意義的是,一種實踐方式的規則是可以被教會的,是可以作爲行動的依據而形成一種融貫的實踐方式的。根據這種觀念,規則並不是對將功利原則直接地、獨立地運用於重複發生的具體情形的單個人們之選擇的概括。相反,規則定義了一種實踐方式,並且其自身是功利原則的主题。
根據羅爾斯這種“實踐方式的規則觀”,在哲學家們常常談論的幾種規則中,只有所謂“構成性規則”(constitutive rules)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規則,而所謂“範導性規則”(regulative rules),以及“技術規則”(technical rules)、“實用準則” (pragmatic maxims)和“道德原則”(moral principles),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規則。
這個規則概念與“概括的规則概念”有幾個根本區别。
第一,與概括的規則概念所認爲的相反,實踐方式的規則在邏輯上是先於特殊事例的。也就是説,如果没有相應的實踐方式的規則的話,一種特定的行動根本就不會被描述稱爲那種行動。以棒球比賽爲例:許多類似於棒球比賽中的動作可以在别的地方進行,但只有在棒球比賽中這些行動才被描述爲棒球動作。
第二,對每個人有甚麼權威在特定事例中判斷遵守規則的恰當性,“實踐方式的規則概念”提供了一種新的看法。如果某人想進行某一實踐方式所規定的活動,他要做的只能是遵守這種實踐方式的規則,而不能問這個實踐方式的規則是否適用於他的情況。他只能對這個實踐方式本身提出疑問,而不能對這個實踐方式之下的特定的行動提出疑問。
還是以棒球爲例:如果有擊球手問:“我可以擊四球嗎?”人們會認爲他是問規則是甚麼。如果人們告訴他規則是甚麼,他還是説在這種情況下他覺得總的來説最好是擊四球而不是擊三球。人們很可能善意地認爲他在開玩笑。你也可以説,如果允許擊四球而不是三球的話,棒球運動會更好一些。但你不能把規則當作是過去事例中甚麼是總體上最好的事情的向導,進而問它們對於特殊事例作爲特殊事例的適用性問题。
第三,根據這種新的規則觀,實踐方式的規則不是幫助人們按照某個更好的倫理原則認爲是正確的方式來判定特殊事例的向導。無論是準統計性的一般性概念,還是一個特定例外的概念,都不適用於實踐方式的規則。一個特殊事例並不是一個實踐方式的規則的一個例外。相反,例外是對於規則的限定或進一步説明。
在羅爾斯那裏,強調兩個規則概念之間的上述區别,是爲了表明倫理學中對我們行動的辯護有兩種基本形式。這兩種形式可以看作是對於兩種不同問題的回答。
比方説,如果一個孩子問父親爲甚麼要把某某人關進監獄,父親的回答可能是因爲他在某處搶了銀行……但如果孩子進一步問父親爲甚麼要造監獄把有些人關進去,父親的回答則可能是因爲要保護好人,不讓壞人欺負。這裹的問題是不一樣的:前一個問題使用了專有名詞、提到了具體個人,後一個問題則不包括專有名詞、不提及具體個人,而僅僅涉及一種實踐的類型或形式,或者説僅僅涉及一種建制。前一個問題是一個個别行動的辯護問題,這個問題是通過訴諸這個行動所屬的那種實踐方式的規則來回答的。後一個問題是一種實踐方式的辯護問題,回答這個問題不能訴諸定義這種實踐方式的規則,而必須訴諸某個原則——在“兩個規則概念”中,這個原則是功利原則。换句話説,功利原則不能直接用來對個别行動進行辯護,而只能對個别行動所從屬的那類實踐或實踐方式進行辯護。
.png)
羅爾斯的上述觀點很像倫理學中區别於行爲功利主義中的規則功利主義。但是,要判定羅爾斯在〈兩個規則概念〉中的觀點是不是規則功利主義,取決於對規則功利主義是怎麼理解的。
還是以許諾爲例。根據行爲功利主義,我在一個特定情形下是否要遵守諾言,取決於我遵守諾言所帶來的功利的總量是否大於我不遵守諾言所帶來的功利的總量。對這種觀點,人們可以這樣來反駁:即使在一個特定情形下不遵守諾言會帶來比遵守諾言帶來的更大的功利,我也還是應該遵守諾言,因爲我知道如果大家都不遵守諾言,許諾這種社會建制就不復存在,而由此帶來的功利損失要遠遠大於我這一次不遵守諾言所帶來的功利增加。如果我們把後面這種觀點稱作規則功利主義的話,那麼羅爾斯在〈兩個規則概念〉中的觀點就不是規則功利主義的。
在那篇文章中,羅爾斯根據其對羅斯(W.D.Ross)的觀點的闡述和詮釋提出以下幾個觀點,從中可以看出他的觀點與功利主義的關係究竟是甚麼。
第一,羅斯認爲,不管遵守諾言這種實踐方式的價值有多麼大,根據功利主義的理由,必定可以設想有某個價值是更大的,而人們可以想像這個價值是可以通過破壞諾言而達到的。羅爾斯認爲羅斯的這個觀點的價值在於指出,人們是不可以通過一般地訴諸效果來爲破壞諾言進行辯護的:“因爲許諾者並不擁有一個普遍的功利主義的辯護理由:它並不是許諾這個實踐方式所允許的諸種辯護理由之一。”
第二,羅爾斯赞同羅斯的這樣一個觀點:上述意義上的規則功利主義觀點過高地估計了不信守諾言對許諾這種建制所造成的破壞。一個人不信守諾言當然會損害他自己的名譽,但一次不信守諾言對許諾這種實踐方式造成的損害是否大到足以說明信守諾言這種義務的嚴格性,這一點並不是一目了然的。
第三,羅爾斯認爲更重要的是對一個與羅斯提出過的例子相似的例子的分析:一個兒子向臨死的父親單獨做出有關遺産處理的許諾。在這種情形下,不信守這個諾言會對許諾這種實踐方式産生甚麼樣的損害,是與這個兒子考慮是不是要信守他對父親許下的諾言不相干的。
從這幾點可以看出,羅爾斯非但不贊同直接用功利原則作爲辯護一個具體行動的依據,而且不贊同間接地用一種實踐方式之維護所具有的功利價值來爲實施這種實踐方式之下的一個具體行動進行辯護。羅爾斯確實強調要把用功利原則對實踐方式的辯護與用功利原則對個別行動的辯護區别開來;他也確實主張,在像懲罰和許諾這樣的事例中,只有前一種辯護是合理的。
但是,並不能因此就簡單地説羅爾斯在這裏的觀點是功利主義的觀點。從他對羅斯的上述觀點的贊同來看,羅爾斯在〈兩個規則概念〉中的立場可以説是介於功利主義和義務論之間的。或者説,他在那時——而不僅僅在後來的《正義論》中——就設法把功利主義和義務論結合起來了。
功利主義的作用是引起羅爾斯對作爲實踐方式和規則體系的社會建制的重視,把倫理學研究的重點從人的行動轉變到人們在其中行動的社會建制。當羅爾斯説功利原則只能被用來對規則所定義的實踐方式進行辯護,而不能爲實踐方式之下的具體行動提供辯護的時候,他的興趣不僅在於功利主義,而且在於他認爲古典功利主義者實際上最感興趣的問题——實踐方式、社會建制或規則體系的問題。在該文的一個注釋中,羅爾斯寫道:
重要的是不要忘記,那些我稱之爲古典功利主義者的人們基本上都對社會建制感興趣。他們位列當時主要的經濟學家和政治理論家之中,他們常常是對實踐事務感興趣的改革家。從歷史上來説,功利主義常常與一種融貫的社會觀相伴随,而不僅僅是一種倫理學理論,更不是一種從事現代意義上的哲學分析的努力。功利原則相當自然地被認爲、被用作一種判斷社會建制(實踐方式)的標準,當作推進改革的基礎。
但是,羅爾斯同時強調,一旦用功利主義對一種實踐方式進行辯護之後,功利主義的辯護作用對於這個實踐方式之下的具體行動來説,就不復存在了。中國哲學家金岳霖在論證效用論或實用主義在知識論中的作用時,採用過類似的思路:效用論的作用是作爲對知識論“出發方式”之選擇的依據,而一旦根據效用論選擇了知識論的出發方式——金岳霖認爲這種出發方式只能是實在論的——之後,就必須放棄效用論,決不能像實用主義那樣繼續把效用當作評價特定命題之真假的標準。
同樣,羅爾斯的思路是:一旦我們用功利原則對某個實踐方式進行了辯護之後,這個實踐方式之下的具體行動的辯護問題的回答,就只能訴諸對這個實踐方式進行定義的規則——也就是這種實踐方式的“構成性規則”(constitutive rules)——了。羅爾斯寫道:
實際上,實踐方式的要點就是使人們放棄依據功利主義考慮或各種明智考慮而行動的資格,以便把未來拴定下來,以便協調好各種計劃。具有一個這樣的實踐方式——它使得許諾者不可能一般地訴諸用來對該實踐方式本身進行辯護的功利原則——是具有明顯的功利上的好處的。在以下説法中並没有甚麼是自相矛盾的或令人吃驚的:當人們在論證象棋運動、棒球運動的現狀令人滿意的時候,或者論證這種競賽應當在各個方面加以修改的時候,人們提出功利主義的(或美學的)理由可能是恰當的,但是,一種運動的選手在爲自己做這個動作而不是那個動作提出理由的時候,如果也訴諸這些考慮,就不恰當了。
換句話説,對於一個從事許諾這種實踐方式的人來説,他之所以有必要信守諾言,並不是因爲信守諾言會帶來任何功利效果,而僅僅是因爲他正在從事許諾實踐。信守諾言是許諾這種實踐方式的題中應有之義。這裏的義務論色彩是很明顯的。
這種觀點很自然地會引起這樣的指責,説它意味着這樣一種保守主義的看法:對每個人來説,他所處的社會的社會實踐方式提供了他的行動的唯一的辯護標準。對這種指責羅爾斯斷然否定,説他的上述觀點並不是一種道德觀點或社會觀點,而僅僅是一種邏輯觀點。當一種行動是由一種實踐方式提供規定時,除了訴諸這種實踐方式之外,一個特定的人的特定的行動是不可能有别的辯護的。但從中並不能推論出我們是應該還是不應該接受我們所處社會的那些實踐方式。“人們盡可以隨其心願地採取激進立場,但是在那些由實踐方式來規定行動的地方,人們的激進主義的物件必須是社會實踐方式,以及人們對這些實踐方式的接受。”
在幾年以後發表的〈作爲公平的正義〉一文和將近二十年以後發表的《正義論》一書中,羅爾斯的立場相對來説確實要激進得多,而這種相當激進的立場的對象,也恰恰是“社會實踐方式”以及“人們對這些實踐方式的接受”。

圖2:A Theory of Justice 圖片來源:Wikipedia。
.png)
先來看看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對“社會實踐方式”所作的思考。
《正義論》的整個工作可以被看作是羅爾斯在新的意義上把義務論和效果論結合起來。功利主義作爲一種社會理論,關注的是作爲規則體系的建制問題,而義務論作爲一種倫理理論,關注的是個人權利和義務的問題。兩者都區别於德性論——功利主義區别於德性論之處之一在於它重視社會建制問題而不僅僅是個人倫理問題,義務論區别於德性論之處之一在於它重視規則而不是德性。
在羅爾斯看來,義務論必須從個人層面上昇到社會層面,使它從一種有關個人行動的道德理論成爲一個有關社會建制的正義理論;而功利主義則必須用義務論加以補充,從而作爲社會建制以及人們對社會建制的接受的主要辯護理由的不僅僅是功利原則,而是把功利原則作爲内在環節的公平原則。這兩方面都可以看出羅爾斯的規則論與其後期的正義論之間存在着密切聯繫。
在《正義論》第二章第一節中,羅爾斯對規則的問題作了相當系統的闡述。他的觀點可以歸結爲以下幾點。
第一,社會建制是一個公共規則體系,這些規則“確定職務和地位,連同它們的權利和責任、權力和豁免等。這些規則規定某些形式的行動是可允許的,其他形式的行動是被禁止的;在違反規則的情況發生時,它們還規定一些懲罰和辯護等。作爲建制——或更廣一些地説,社會實踐方式——的例子,我們可以想到遊戲和儀式、審判和議會、市場和財産制度。”
第二,説某時某地存在着一個建制,是説由這個建制所規定的那些行動被作爲一個常規而執行,並且在這種執行的同時,人人都知道定義該建制的那個規則體系是要被遵守的。
第三,説這個規則體系是公共的,是説如果只要這些規則和人們對這些規則所規定的活動的參與都是一種同意的結果,那麼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知道他在這種情況下應該知道的東西。正是這一點構成了進行合作的人們之間的相互期待的確定性。
第四,有必要區别一個建制的兩種規則,一種是所謂“構成性規則”,它們對一種建制加以定義,確定這種建制的權利和義務;另一種則是策略或準則,它們涉及的是個人和團體根據其利益、信念和有關彼此行動計劃的猜測而將選擇甚麼樣的可允許的行動。
第五,還要對一個單一的規則(或一組規則)、一個建制(或其中的一個主要部分)以及整個社會系統的基本結構做出區分,因爲單一規則、由規則構成的建制、由建制構成的整個社會制度,它們的正義還是不正義並不是對應的。
對規則概念作上述説明,是爲了説明社會建制的概念;而在所有社會建制中,羅爾斯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的基本結構,也就是社會的主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
在説明這種意義上的社會建制的“構成性規則”的時候,羅爾斯在形式方面列出了像“一般性”(generality)(可以這樣理解:其涉及的對象是一個類中的全部個體)、“普遍性”(universality)(也就是説,它們是所涉及的人們都可以理解、都應當遵守的)和公開性(它們應該向所涉及的人廣而告之)之類的特徵,在内容方面把這種構成性規則看作是對某個原則之運用的結果。
這些與羅爾斯早期的觀點没有甚麼不同。但在以下兩點上羅爾斯後來的觀點與其早期的觀點完全不同:作爲規則之基礎的不再是功利原則,而是程式公平原則;程式公平原則的作用不是僅僅作爲一個範圍更廣的普遍命題被運用於這種範圍之中的一個特例,或者僅僅作爲一個普遍原則而爲特定範圍内的規則提供辯護理由,而是作爲社會基本結構的構成性規則——正義原則——的選擇程式的形式特徵,用這種程式的公平性來確保正義原則的正當性。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羅爾斯思想中功利論成分和義務論成分在兩個層次上的結合。
第一個層面是選擇正義原則的程式。在羅爾斯那裏,選擇正義原則的原初狀態之爲公平的,主要是因爲其中的各方在道德上是平等的。就此而言,就羅爾斯把道德平等當作最基本的價值這一點來説,羅爾斯的觀點可列入義務論的範疇。但是,羅爾斯認爲,原初狀態中的各方通常傾向於選擇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基本社會善,他們要考慮的是將如何決定哪個正義觀是對他們最有利的。從這點來説,功利主義原則又可以説是包括在平等原則之中了。
第二個層面是選擇出來的那兩個正義原則。在這兩個正義原則中,第一條原則要求確保每個人具有與别人同樣的自由相容的平等的自由,第二條原則要求社會經濟方面的不平等以機會平等、最差境遇的人的狀況在這一格局中比在其他可選擇格局中爲好作爲前提。羅爾斯強調第一原則優先於第二原則,意思是對第一條原則所保護的基本平等自由的損害,是無法用更大的社會和經濟利益來辯護或補償的。就此而言,羅爾斯的觀點屬於義務論的範疇。但是羅爾斯畢竟没有只講正義,不講效率;用他在196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話來説,最普遍的原則所要求的是“建立最有效率的正義建制”。”羅爾斯明確指出,功利原則是包含在這個原則之中的。
羅爾斯的兩條正義原則,作爲社會建制的構成性規則,可以看作是“建立最有效率的正義建制”這條原則之運用的結果。這條原則與正義原則的關係,不同於作爲原初狀態之象徵的程式公平原則或平等原則與正義原則的關係。前者的關係可以説是語義上的——原則可以説是規則的預設而藴含在規之中的;而後者的關係則可以説是語用上的——要讓原初狀態中的各方選擇那兩條正義原則,還需要對人性的特徵、正義的環境等等做出許多假定。
儘管後期羅爾斯對作爲規則之基礎的原則的看法與早期不同,但在這一點上,兩者卻仍然是完全一致的:對實踐方式社會建制的辯護,與對屬於這種實踐方式或社會建制之下的體行動的辯護,是兩個不同範疇的問題。

圖3:Thomas W. Pogge, Realizing Rawls 圖片來源:Amazon。
前面説過,在他“建立最有效率的正義建制”的原則中,正義是主要的,效率是次要的。這只是後期羅爾斯思想中的義務論成分的一個表現。這種義務論成分還表現在另外一點上:對他來説,一旦從這個原則出發引出那兩條正義原則之後,社會行動者就不再能夠用這個原則——尤其是包含在其中的功利原則——作爲自己對由兩條正義原則所定義的社會基本結構提出異議的依據了。除了正義之外,合作、效率和穩定這些價值在選擇社會基本結構的過程中都起作用,但一旦選擇了兩條正義原則之後,成爲政治活動之依據的就只能是這兩條正義原則,而不能撇開正義原則直接訴諸這些價值。用托馬斯·博格(Thomas Pogge)的話來説,“作爲羅爾斯正義標準之基礎的那些價值,已經被充分容納了,已經被‘窮盡’了,因而(從邏輯上)無法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滿足,因此不能夠爲違反這種建制——它也是用那些價值來辯護的——的任何行爲加以辯護。”
.png)
這裏所説的建制是社會的基本結構,而不是指這個基本結構——也就是憲法框架——之中所制定的特定的法律。在羅爾斯的理論中,對於正義原則,人們具有遵守它們的自然義務(natural duty),而對於根據正義原則而建立的憲法框架之内制定的法律,人們則具有服從它們的職責(obligation)。這裏涉及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有關“人們對這些實踐方式的接受”的問題。羅爾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與他的規則論的聯繫更加密切。
羅爾斯認爲,原初狀態中的人们不僅要選擇有關社會建制的原则,而且要在有關社會建制的原则選定之後進一步選擇有關個人如何處理與社會建制的關係的原则。前者的結果是兩條正義原则,後者的結果是他所謂“公平原则”(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或“公平游戲原則”(the principle of fair play)。公平原則是所謂“職責”的來源。“職責”不同於“自然義務”,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與社會建制或社會實踐方式有聯繫,後者則與特定的社會建制或實踐方式沒有必然聯繫;前者只有當我們自願地加入一個建制的時候才有約束力,後者不管我們自願與否都有約束力;前者則只能歸之於具有特定角色的個人,而後者之適用於人們之間,是不論他們之間的建制性聯繫的。根據公平原則,如果一個建制是正義的或公平的,也就是説滿足兩個正義原則的,那麽只要儅一個人自願地接受了一個建制的格局或利用了它所提供的機會去追求他的利益,這個人就有職責去承擔這個建制的規則所規定要做的那份工作。羅爾斯用這個原則對適用於普通公民的政治職責和信守諾言的職責作了説明。
前面提到,羅爾斯在〈兩個規則概念〉中提出要把對於許諾這種實踐方式的辯護與許諾這種實踐方式之下的具體行動的辯護區分開來。在《正義論》中,羅爾斯又提出一個新的區分:要把作爲一種實踐方式之許諾的規則的約束力與作爲公平原則對許諾這種實踐方式的運用之結果的誠信原則(the principle of fidelity)區分開來。這個區分在羅爾斯的規則論乃至正義論中具有重要意義。關於許諾,羅爾斯寫道:
許諾是一種由一個公共的規則體系所規定的行動。這些規則——就像所有建制一樣——是一套構成性的約定。就像遊戲規則那樣,它們規定某些活動、定義某些行動。在許諾這個例子中,最基本的規則是支配“我許諾做X”這句話之使用的規則。它的意思大致如下:如果某人在恰當場合說了“我許諾要做X”,他就該要去做X,除非存在着一些使他開脱的條件。這條規則我們可以理解爲許諾的規則: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對整個實踐方式的表述。它本身並不是一條道德原則,而是一條構成性約定。在這方面,它與法律規則和法令以及遊戲規則具有同等地位;就像這些規則一樣,它之存在於一個社會之中,是當它多多少少被作爲行動依據的時候。
要確定公平規則能否運用於許諾實踐而引出誠信這種職責,一要看這種實踐方式是否正義,二要看許諾的人是否自願地做出許諾。
關於前一個問題,羅爾斯說儘管通常理解的許諾實踐所規定的恰當場合和開脱條件是符合原初狀態下人們會做的選擇的,他還是不願意把許諾實踐說成是顧名思義就正義的事情,因爲這樣會混淆許諾規則和從公平原則中推導出來的誠信職責之間的界限:“存在着多個許諾的變種,就像存在着多個契約法的變種一樣。一個人、一群人所理解的某個特定的實踐方式是否正義,仍然有待於借助於正義原則來確定。”
關於後一個問題,羅爾斯說,做一個許諾,就是訴諸一個社會實踐方式並接受它使之成爲可能的那些利益,那就是建立和穩定小規模的合作格局。正因爲這種利益,人們才自願地進入許諾這種實踐方式。一個人並没有做出許諾這種職責;但如果做出了許諾,而許諾這種實踐方式又是正義的,或者說一個人進許諾活動的條件是符合正義的許諾實踐的標準的,那麼,根導出職責的公平原則,這個人就因此而承擔了誠信職責,而是與許諾的規則不同的:
將許諾的規則與誠信的原則(作爲産生於公平原則的一個特例)混爲一談的趨勢尤其強烈。初看起來它們好像是同一回事;但是,前者是由現存的構成性約定所定義的,而後者則是由原初狀態中可能被選擇的一些原則所解釋的。用這種方式我們因此可以區别兩種規範。“義務”和“職責”這些術語在這兩種語境當中都被使用;但是從這種用法中産生的含糊性,應該是很容易消除的。
這兩種規範或規則,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自然義務,構成了個人行動所要遵守的三類社會規則(作爲規則,它們都區别於準則和建議等等)。根據羅爾斯的觀點,我們可以對這三種規則或規範做以下概括:自然義務具有道德意義,但不與社會建制發生必然聯繫。建制性要求與社會建制具有必然聯繫,但不具有道德意義。職責可以說是介於自然義務和建制性要求之間的:它們一方面與社會建制具有内在聯繫,另一方面又具有道德意義。羅爾斯尤其強調不能把建制性要求與職責混淆起來:
建制性要求,以及那些從一般來説全部社會實踐方式引出來的建制性要求,可以從既成的規則及其詮釋當中加以確定。比如,作爲公民,我們的法律義務和職責——就其能確定的而言——是由法律的内容所確定的。適用於作爲遊戲選手的人們的那些規範,取決於該遊戲的規則。這些要求是否與道德義務和職責相聯繫,是另外一個問題。即使法官和其他人用來對法律進行詮釋和運用的標準與正當原則和正義原則相像或相同,也仍然是這樣。比方說,在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裏,法庭用來詮釋憲法中那些調節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確保對法律的平等保護的部分的,很可能是那兩個正義原則。儘管在這裏,如果法律滿足其自身的標準的話,我們顯然在道德上必須——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服從法律的,但是,法律要求甚麼的問題,仍然是與正義要求甚麼的問題是區别開來的。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有關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和良心拒絶的討論,是對這裏所說的區别——法律的要求和正義的要求之間的區别——的詳細發揮。但這裏的情況比許諾的情況要複雜。羅爾斯没有討論一個特定諾言是否正義的問題。可以設想這種情況:
甲對乙説:“你如果付給我兩百元,我就去把你的那個仇人揍一頓。”但等甲拿到乙的錢之後,他覺得打人不好,反悔了,不按照諾言去打人了。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根據許諾實踐的構成性規則,還是根據誠信原則,甲都是不對的。他的行動要得到辯護,只能訴諸“不能打人”這個自然義務。
就法律而言,羅爾斯不僅考慮它是不是根據體現正義原則的憲法程式制定出來的,而且認爲它即使是根據體現正義原則的憲法程式制定出來的,也有一個是否正義的問題。關鍵在於,在羅爾斯看來,即使在一個近似正義的“秩序良好社會”中,憲法也仍然是一個雖然正義卻不完善的程式。“說它是不完善的,是因爲不存在任何可行的政治過程能確保根據它而制定出來的法律一定是正義的。”公民的利益和看法各不相同,從程式的角度來說只有多數裁決原則才是正義的,但多數決定的結果從内容上說卻並不總是正義的。
我們必須擁護一部正義的憲法,所以我們必須贊同它的一個基本原則,即關於多數裁決原則。因此,在一種接近正義的狀態下,根據具有的擁護正義憲法的義務,我們通常也就具有遵守不正義法律的職責。
但這種職責是有限度的。第一,從法律本身之不正義的程度來說,不正義的負擔在長時段内應該是在社會不同群體中間多多少少平均地分佈的,不正義政策的困苦不應該在任何特定情況中具有太重的分量。對於那些長年遭受不正義對待的永久性少數群體來說,上述限度更容易突破一些,因而對他們來説,服從法律的職責就更容易成爲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公民就有權利不服從、不遵守不正義的法律,而進行所謂“公民不服從”,它是“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出於良心但政治性質的反對法律的行動,其目的通常是爲了造成法律和政府政策中的變化。”第二,從公民的態度來說,即使當公民有職責在行動上服從不正義的法律的時候,他們也没有職責要在思想上認爲這些法律是正義的。
羅爾斯從他對建制性規則與建制性職責之間關係的討論中引出的結論,可以概括爲這樣幾點。
第一,建制性職責與建制性規則之間的聯繫,要求我們在一個建制是正義的,我們因爲從這個建制獲利而自願地加入這個建制的前提下,服從它的構成性規則。
第二,但建制性職責畢竟是與建制性規則相區别的,爲建制性職責提供根據的公平原則同時也要求當我們在某個建制明顯不符合正義原則的情況下,不服從這種建制、不遵守它的構成性規則。
第三,由於這種建制——特定的法律——並不是社會的基本結構,而羅爾斯的正義論的前提是一個其基本結構是正義的或接近正義的“秩序良好的社會”,所以,公平原則又要求在反對根據立憲程式制定出來的某個特定法律的同時,履行遵守這種立憲程式的建制職責和服從正義原則的自然義務。爲此,羅爾斯又強調,公民不服從必須是非暴力的、公開的,進行公民不服從活動的人必須承擔由此帶來的法律後果等等。
.png)
上面所分析的羅爾斯的規則觀念,與當代中國語境有着多方面聯繫。
第一,隨着“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成爲國家的正式綱領,憲法(共和國的構成性規則)的作用得到空前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前面提到的羅爾斯關注的兩個主要問題——社會實踐方式的問題和人們對社會實踐方式的接受的問題——可以說也已經成爲我國政治生活的兩個最基本問題。相對於社會基本結構的理想設計問題來說,目前實際上存在的各個層次建制之間的關係和如何對待這些建制,是對普通公民關係更爲直接的兩個問題。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利益調整、經濟形勢的動蕩不定等等,使得公民在對憲法的忠誠與對憲法框架内(有的是在此之外)制定的法律、政策的服從之間,常常産生程度不同的矛盾。羅爾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語境中討論的問題和提出的觀點,對於我們理解和解決這些矛盾,至少是具有啓發意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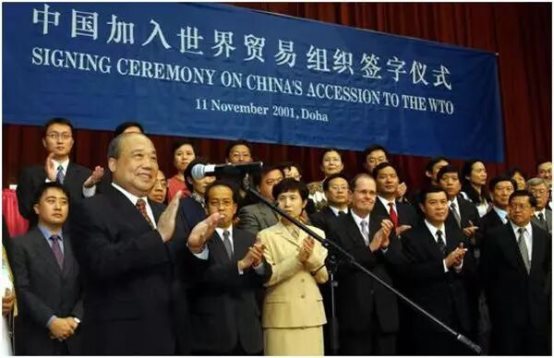
圖4: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第二,隨着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遊戲規則”一詞更加頻繁地出現在各種會議和各種傳媒當中,因爲這個完全人爲建立的組織的主要職能,就是制定和執行全球貿易的“遊戲規則”。“遊戲規則”相當於羅爾斯所說的“建制規則”,所以羅爾斯關於後者的論述應該說是與當代中國語境非常相關的。遵守世貿組織的構成性規則本身並没有道德意義。但是,就像體育運動一樣,並非只有具有道德意義的行動規則才是值得重視的。對於缺乏規則意識、没有遵守規則的能力和習慣的單位和個人來說,加入世貿組織是一個嚴峻的、常常需要付出沉重代價的學習過程。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雖然是否遵守世貿組織的構成性規則本身並不具有道德意義,但這些規則是否正義、自願加入世貿組織之後是否自覺遵守這些規則,還是具有道德意義的。這種集體行動層面上的道德意義不同於個人行動層面上的道德意義,但對於生活在複雜的現代社會中的人們來說,前者的重要性是忽視不得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羅爾斯的規則論與當代中國語境也是相關的。
第三,與此有關的是一個普遍性程度更高的問題,即在一個以立憲政治和市場經濟爲特徵的現代社會中,如何堅持“誠信”這個道德原則的問題。洛克(John Locke)說過,“誠實和守信是作爲人而不是作爲社會成員的人們的品質。”他甚至還說,“許可、諾言和誓言,是全能的上帝也要受到的約束。”洛克在這裏賦予誠信原則以自然義務甚至宗教義務的性質,但是這個原則在現代社會裏無疑具有更爲重要的意義,因爲現代社會中人們之間合作更加重要,而這些人往往是由一般規則而不是特殊紐帶連接起來的陌生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的“誠信”往往意味着他能在没有熟人監督的情況下、在不涉及特殊忠誠關係的情況下信守自己有關一般規則而不是某件特定事情的諾言。關於羅爾斯的規則概念與當代中國語境提倡誠信原則的這一任務的關係,我們不妨借助於一個具體例子作比較詳細的分析。
二〇○二年十二月的一份報紙上曾經有這樣一則報道說,上海有一所大學決定在馬上開始的期末考試中發給每個學生一紙《誠實承諾書》,内容是“我鄭重承諾:在考試中決不作弊,奉守誠實原則,嚴格約束、規範自己的言行,不做任何違反校紀校規的行爲,並願意以此接受主考老師的監督。”據說這種“誠實承諾”受到了全校同學的回應,馬上要在全校推廣。
但是,一位科學家讀後對此非常不滿,說“假如我是這所大學的學生,我就絶對不接受那《誠實承諾書》,我會認爲那是對我人格的侮辱!寧可退學也絶不賭那樣的咒,發那樣的誓!”
現在的問題是:這所大學的學生是不是應該簽這份《誠實承諾書》?這份《誠實承諾書》所要承諾的是大學期末考試中不作弊,大學期末考試,或者一般地說考試,是一種社會建制,而這種建制又是整個高校教育的構成性部分即不可缺少的部分之一。按照通常的理解,考試的構成性規則是不能作弊。用羅爾斯的術語來說,作爲考試的構成性規則的不作弊,是一個建制性要求,它與來自公平原則的不作弊這種道德職責不是同一回事。顯然,成問題的不是考試能不能作弊,因爲一個允許作弊的考試,顧名思義就不再是考試,就好像——用前面提到的羅爾斯舉的例子一允許擊四球而不是擊三球的球類運動根據定義就不是棒球運動一樣。
成問題的、發生爭議的是:學生有没有道德職責去履行與考試這種建制或實踐方式相聯繫的建制性要求——不作弊?
根據前面所講的羅爾斯的觀點,考慮人們有没有一個建制性職責,取決於兩個因素。第一,這個建制是不是正義。第二,一個人是不是自願加入這個建制的。既然没有理由說我們目前高校實行的考試制度怎麼不合理不正義,也没有理由說大學生進入大學、接受大學教育、參加包括考試在内的各個教學環節是對他們不利、是強加於他們的,那麼,結論應該是很清楚的:不作弊不僅僅是考試這種建制的構成性規則,而且是參加考試的人們的道德職責。這種職責對他們的約束力,並不産生於他們承諾不作弊的時候。考試不作弊作爲一種建制性的道德職責,在他們自願地加入高等教育這個建制、進而自願參加期末考試的時候,就已經具有約束力了。從這個角度來說,承諾考試不作弊完全是多此一舉。
還可以從承諾本身的特點來看這個問題。根據羅爾斯的觀點,承諾作爲一種社會建制,它的構成性規則是“凡許下的諾言都要遵守”,但這種守諾規則並不等於同樣要求信守諾言的誠信原則。要引出誠信原則,還要求用公平原則來考察許諾這種建制是否正義,以及人們是否自願加入這種建制。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承諾考試不作弊非但是多此一舉,而且很可能適得其反。在考試之前要學生簽署《誠實承諾書》,與要求顧客在進入商店之前簽署《不偷竊承諾書》没有甚麼區别,那位科學家對那所大學的做法感到氣憤,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從這點上說,這種承諾並不符合正義建制的要求,因而信守這種情況下許下的諾言並不是一個道德職責。那些迫於教師和同學壓力而簽訂這份承諾書的人,如果這樣來看待自己所做的承諾的話,並不是一點道理也没有的。
至於那些像那位科學家一樣“寧可退學也絕不賭那樣的咒、發那樣的誓”的學生,則更可能提出這樣的質問:我們没有做不作弊的承諾,是不是就可以不受“不作弊”這條規則的約束了?而對於或許更多的人來說,這種形式的承諾似乎是在向他們暗示,既然没有做過這樣的承諾,他們就不具有承諾所涉及的那個職責,作弊起來就更心安理得了。
再進一步說,考試有一個是否作弊的問題,承諾也有一個是否作假的問題。僅僅作爲一種儀式的承諾,並不能保證所做的承諾是一定會兑現的。說得刻薄一些,當一所大學的學生公開承諾他們的個人履歷將是完全真實的之後,人們有理由擔心,這所大學的畢業生是不是更容易用自己的虚假履歷騙取用人單位的信任……。爲了防止出現這種情況,我們是不是要再做一個承諾:承諾不做虚假的承諾?從邏輯上說,這個承諾的序列可以無限延伸下去。
當然,那所大學的管理人員會說,他們之所以要求大學生簽署誠實承諾書,完全是出於無奈。不這樣做的話,有的學生可能會忘記自己在考場該做甚麼、不該做甚麼。不這樣做的話,有的學生會認爲,既然自己没有做過承諾,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違反考場規則。
但問題的嚴重性正在這裏。一般來說,需要承諾的東西是只有承諾了之後才具有約束力的東西。我許諾明天給你十元錢。“給你十元錢”這一點本身是没有任何約束力的,但許諾了之後就有約束力了。我許諾明天還你以前借你的十元錢。“歸還所借的錢”固然不需要這個承諾才具有約束力,因爲“借”的錢,顧名思義是要還的,否則就不是借了。所以,當我許諾明天還你以前借你的十元錢的時候,我並不是直到這個時候才受到“歸還所借的錢”這一條的約束,而是受到“明天還錢”這一條這個約束,而“明天還錢”這一條的約束力本來是没有的,只是許了諾之後才有的。
以此類推,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上面所說那所大學的做法:這所大學之所以要號召學生簽署考試不作弊的承諾書,是因爲在學校的管理人員看來,不作弊這一條在學生當中已經没有任何約束力了;除非做出不作弊的承諾,不作弊這一條本身就是不具有約束力的。見識過一些由幹部、大款們參加的成人教育考試場面的人,對這種想法是不會覺得奇怪的。
這樣看來,那所大學的做法雖然從道德理論角度來看是很成問題的,但對於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的人來說,它卻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個案,從中看出我們的社會在道德狀況方面出現了甚麼問題,應該採取甚麼樣的相應辦法。
從本文主題來說,同樣值得重視的是,從上述例子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在中國語境中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它有助於捍衛某個“主義”,而且也在於它有助於解決一些“問題”。
文字编辑:林上、李哲
推送编辑:杜姝寰、陈立采
审核:孙飞宇、许方毅
文章出处:童世骏,2002年,《社会理论学报》,第五卷第二期:405-430。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