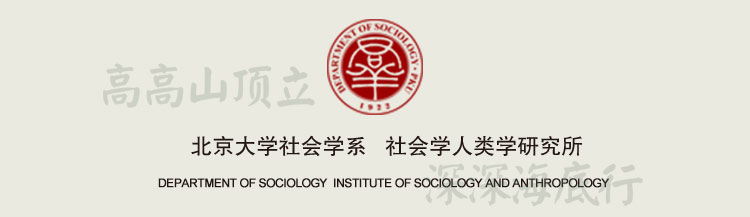羅蘭:中國社會學與西歐社會學:距離與接近
羅蘭(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摘要:得到新生的中國社會學正在再次騰飛。如果說在初始階段西方社會學對中國社會學的重建背景產生過一定的影響,那麼今後國際社會學領域中,再生於一個充滿活力和生機的日新月異的社會中的中國社會學很可能使兩者關係倒轉過來。中國社會學通過不斷的理論、姿態和方法的創新在中國和國際學界鞏固自己的位置,這些創新與西方思想的關係時而平行、時而合作、時而對立。中國同行們重新解讀甚至將西方理論本土化,創建着他們特有的多元的社會學思想。

本文作者罗兰(Laurence Roulleau-Berger) 法国社会学家 图源:Google。
雖然1949年前飛速發展的中國社會學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間受到全面禁止,但在得到新生以後,它很快就再次騰飛。的確,社會學在1980年代成爲中國學術界的先鋒學科。中國思想史和中國社會的複雜性爲它源源不斷地注入了學術活力,而它則通過層出不窮的科研成果向世人展示出這種活力的強大及其與衆不同之處。
如果說在初始階段西方社會學對中國社會學的重建背景產生過一定的影響,那麼今後在國際社會學領域中,再生於一個充滿活力和生機的、日新月異之社會中的中國社會學很可能會使兩者的關係倒轉過來。中國社會學通過不斷的理論、姿態和方法的創新在中國和國際學界鞏固自己的位置,這些創新與西方思想的關係時而平行、時而合作、時而對立。今天,中國同行們正在重新解讀甚至將西方理論本土化,創建著他們特有的多元的社會學思想。
.png)
從中國社會學的研究現狀中我們看到在學院領域存在著一種科學的多元性局面,其中沒有哪一種綜合性的一般理論佔據主導地位,事實和理論解釋之間的關係簡單明瞭,沒有哪一種學術流派能以優越的姿態出現。中國社會學界似乎接受多種科學合理化規範,這使多樣性和不同觀點的共存成爲可能,當然其條件是實踐與社會學理論之間存在一種真正的辯證關係。任何理論如果沒有經驗研究的支持都是不能成立的。這些科學性條件可以說是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中國社會學家眼中的法國社會學似乎有理論主義的嫌疑。
在中國,一些社會學理論看上去比其他理論更結構主義,或更注重理解或互動過程。但科學領域內同時存在的研究立場的多樣性在學院領域內顯得完全合理,它們互相之間沒有互相排斥的關係,它們各自都能分別幫助理清同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過程的不同側面。
60年代法國社會學的發展主要圍繞著生成結構主義(布迪厄)、行動和社會運動社會學(圖海納維、杜貝、維沃爾卡)、功能和策略學說 (Crozier/Friedberg)、方法論個人主義 (Boudon) 展開;自80年代起,它吸收了建構主義社會學(柏格和魯克曼)、芝加哥學派 (Grafmeyer/Joseph)、互動論(高夫曼、休斯、貝克、布魯默、斯特勞斯)的思想;90年代得到發展的則是辯護社會學(泰弗諾,波爾坦斯基)和科技社會學 (Callon, Latour)。70年代末以來,後兩極的地位越來越明顯。客觀主義和它們之間的對立面不斷增多並逐步擴大,而理解主義和闡釋主義之間則較爲接近。
蜜雪兒·維沃爾卡認爲從70年代起法國的馬克思主義已失去活力精華,結構主義弱化,批判思想變得過於批判。他記錄到以下幾點變化:
-圖海納所說的“‘社會的’的終結”和“全面”思考社會學對象的必要性。
-主體的強力上升:“主體不是行動者,但如果條件允許它將給人以成爲行動者的能力,它將讓人有可能行動、建構自己的經驗並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己的經驗”。對主體的思考同時也是對“反主體”的思考。主體的強力上升意味著當代個體成爲法國社會學辯論的焦點。
-研究者在超越政治領域的公衆領域中的投入程度問題。
-宏大理論系統的衰弱和大範式的分化:法國社會學家逐漸放棄建樹大覆蓋面的理論的做法。

Michel Wieviorka 法国社会学家 图源:Wiki。
作爲法國社會學家,我們怎麼看待27年來的中國社會學?通過研究,我們得出以下結論:
-中華文明的過去和今天的影響日益增強。
-通過結構化分析“生產社會”這一觀點不斷發展。
-通過主觀性和互動問題個體的地位日益突出。
-中國學者希望創造獨立自由的理論以擺脫文化殖民形式和西方看中國社會的居高臨下的眼光。
符號互動論、民俗論、理性選擇理論、交往理性理論、歷史性理論性理論(?)、生成結構主義……之間互相拒絕承認對方的合理性,好像有別於中國的情況。其原因可能是中國思想史中各種傳統的歷史家譜沒能以連續的方式得以撰寫。
.png)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中國社會學家對歐美社會學流派瞭若指掌。他們在不同研究中區分或聯繫各種理論,卻從不否認它們的合理性。但他們對不同範式進行組合,創造出能夠解釋社會事實不同側面的複雜性的社會學。他們認爲社會學是資本主義文明的產物,他們成功地將自己的社會學扎根於昨天和今天的中華文明裏,同時也扎根於與歐美社會學的承襲、搬用、混血中。
我們清楚地看到中國對歐美尤其是法國和美國社會學理論的承襲。第一次當然是1917年即引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社會學至今帶著這個淵源的烙印。不過今天這個歷史關係已經不是唯一的了。我們還記得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Robert Park和他的女婿Robert Redfield在1931–1932和1948年兩次赴中國任教。另外,北美的實用主義和互動論、柏格和魯克曼的建構主義、理性化理論、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策略分析、行動者理論、圖海納和維沃爾卡的行動和社會運動社會學……還有關係更新的批判社會學、布迪厄的生成結構主義以及頻繁被引用的哈貝馬斯、貝克和吉登斯的學說,都在对中國社會學家發生著影響。
理論學說片段的搬用屬於非常複雜的問題。搬用就意味著翻譯,對在特定背景和特定時刻建構出來的概念進行加工,使其適用於新背景。在這項工作中,社會學家應時刻注意翻譯過程中是否包含意義添加或缺失的危險。理論片段的搬用的確伴隨著加工、再詮釋和借用,但我們先前已見到中美或中歐社會學之間已形成概念的接觸地帶,西方概念可以被漢化,不同社會學之間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接觸點。
爲適用過去和今天的新文化背景,概念需要重塑。混血總是以重塑爲基礎而發生的。由於中國社會學家充分重視背景問題,他們能夠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從新的視角將理論片段聯繫組合起來。我們在概念可譯地帶發現中西思想之間的矛盾和分歧能(或不能)催生混血,我們也在不可譯地帶發現“認知空白”,即中西學科間無法互相呼應的空間。的確,概念的不可譯性是中西思想間的永久問題,這不是說社會學交流的失敗,而是說本體不對稱關係是知識產出的基礎。
還有一些重要社會學家的名字很少出現在中國社會學舞臺上。比如法蘭克福學派的德國學者,齊美爾……參考書目裏找不到方法個人主義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的代言人和歐洲研究當代個體的學者。北美全球化問題的專家也鮮被引用。這些作者的缺席從反面刻畫出中國社會學的邊線。
布迪厄、圖海納、莫蘭、哈貝馬斯、貝克、霍耐特和吉登斯的學說在歐洲社會學界當然有其無可替代的地位,但也有其他的研究力圖消除不同社會學傳統之間的對立關係。西歐社會學頻繁借鑒美國學者尤其是實用主義和互動理論的思想。而結構主義的影響在當今的法國仍然很深。以馬努埃爾‧卡斯特爾和薩司其亞‧薩森爲代表的全球化問題專家以及以裏查德‧塞耐特或格蘭諾威特爲領軍人物的新經濟社會學家在歐洲的地位舉足輕重。但直到現在,在歐洲社會學家的參考書目中都還是很難找到中國學者的名字。
如果說歐洲社會學有民族中心主義和閉門造車的問題,中國社會學卻完全不是這樣。後者在向歐美社會學學習之後已經明確地建立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思想。中國社會學中理論範式不斷位移和交叉,拒絕民族中心姿態、抵制前殖民思想模式霸權、堅持思想的地方性——而歐洲社會學恰恰在這個問題上難以容納非西方思想。
.png)
中國社會學和歐洲社會學之間的距離是很難定位和測量的。在這裏我們主要討論二者之間區別比較明顯的幾個主題:
-轉型和現代性問題
-碎片化和社會結構的變化
-城市化、隔離和整合
-個人、社會和承認問題
(一)轉型和現代性
當代社會的現代性是個複雜的問題。什麼是現代社會?我們根據什麼來判斷現代性的有無?西方世界中社會這個概念被廣泛地與現代性相聯繫。作爲西方人,我們認爲現代性有不同種類並且我們將親眼見到社會的終結。
圖海納認爲思想的理性和對個人權利的尊重是現代性的標誌。在這個定義中他提到了現代性的統一性和現代化路徑的多樣性。圖海納會提出不同社會共存的假設:將現代性和現代化相聯的社會、將工具性現代化和強化統治整合制度相聯的社會、還有既達不到現代性又找不到現代化道路的社會。這裏的現代性概念包含有普世性的評判,理性知識超越一切其他的對各種現象的解釋模式,權利概念適用於所有個人,主體概念應佔據對每一個問題的思考的中心地位。

Alain Touraine 法国社会学家 图源:Wiki。
圖海納首先將個人定義爲享有權利的個人;主體概念意味著變化,自我的創造,與自我的靠近,這個概念依然與社會和文化鬥爭、新的社會運動和未來發展意義和承認的集體行動緊密相連。對圖海納而言,主體概念應與現代性一起被思考,但當個人和群體面對多種統治和衝突時,我們也必須將主體和社會運動概念相結合去解釋社會衝突與在特定社會中對社會資源、文化資源、符號資源的調動之間的關聯。
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要研究中國社會的現代性問題,就必須要研究經濟和社會的轉型問題。轉型問題中包含了部分現代化和發展的元素但又並不局限於此。根據孫立平的定義,社會轉型有其自身的邏輯和方法,身處其中的個人在實踐中實施著與中國今昔文化的大背景相適應的策略和技巧。更明確地說,研究者可以將社會轉型和另外兩種變化放在一起研究: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以及農業社會向傳統社會的轉變。最後,孫立平在他的發言中會闡明如何在轉型過程與工業化和全球化之間建立聯繫以理解中國社會的巨變。他發展了一套將社會轉型視爲共產主義文明——價值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生活制度的文明。
(二)碎片化和社會結構的變化
對中國社會學家來說,研究社會分層的問題不能脫離市場經濟問題。改革以來,中國社會日益分層,以社會職業標準來看分化成爲四個階層。中國社科院的社會學家提出了十個社會階層分類,這十個階層大致上構成四個大的社會階級:上層階級,中產階級,大衆階級以及無業、失業和半失業人員階級。這些學者強調指出中國社會的四大特徵:社會結構複雜化,社會群體差異化,社會路徑多元化和流動機會不平等。不同階級間的收入差距日益增大。於是孫立平提出“斷裂社會”的概念,以突出社會多極化——這一在過去十年內發展起來的過程——的迅速。
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李春玲的研究展示了社會流動路徑從1978年起呈現多樣化趨勢,結構性屏障重新定義。此次大會發言中她重點闡述1949年前經濟資本的決定性在1949年到1980年期間成爲負面因素,而文化和經濟資本又在今天社會流動機制的建設中再次扮演重要角色。她解釋了改革的矛盾:改革大大增加了流動的機會,但同時又更加明確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界限。

李春玲著《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 图源:当当网。
最後,中產階級的上升逐漸成爲社會風景中最重要的現象之一。
中國中產階級上升的條件也讓我們再次思考這一階層的社會和象徵邊界的性質。但法國相關的研究表明中產化趨勢並不是由生活方式的统一来确定,相反,是區隔方式的多元化和轉移體現了精英和統治階級的地位在法國社會裏的強化。而與中國相比,歐洲國家相對以間接的方式——通過對制度和機構開放程度的調控——去影響社會結構。中產階級表徵和定義如何形成、被拋棄又在近幾年被重新拾起的過程,她分析了中產階級爲了存在所運用的篡權策略——其中一部分被統治階級破解,因爲後者爲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強化了集體、社會和制度屏障。
(三)城市化、隔離和整合
在經歷了1949到1979年間的停滯以後,城市化進程從1979年起大幅加速,與工業化一起齊頭並進。這兩個進程在西方用了幾百年的時間,在中國卻只用了20年。社會學分析共同指出城鄉碎片化的明顯趨勢,尤其由於戶口作爲社會差異的主要原因產生了兩種不可疊加的地位制度。但人口流動的加強使城鄉對立問題逐漸消失轉化成爲城市中的下層階級問題。
李友梅則提出街區的治理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基礎。她解釋,經濟政治行動者通過政治革新積極參與新舊制度間的結構張力的協調,而農民又是運用舊的地方性知識實現了自我保護。這些處在城市空間和制度中不同地點的不同行動群體製造了新的集體行動的方式。隨著經濟改革在行政治理領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隨著政府職能不斷下放,街區、國家代表和市民中不同利益集團共同建設著治理的方式。於是,在今天中國的國情下,城市中誕生了公民社會。

李友梅、孙立平、沈原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 图源:当当网。
在國際化和流動加劇的背景下,歐洲的城市在社會和經濟動力作用下成爲經濟、文化、社會和符號財富聚集地帶。因此,城市問題再次成爲歐洲社會學的中心問題。不同的市民階層,佔據不同等級的城市和空間地位,需要面對城市和勞動市場的重建以及随時可能的社會衝突,他們之間的張力格局呈多樣化趨勢。不論歐洲還是中國,面對碎片化、脫離和分散,社會空間分隔和城市隔離的重新定義問題再次被提出。正如 Grafmeyer 所說,不論在哪里城市都被認爲是社會事實和社會化空間。城市永遠充滿張力:距離和近鄰,中心和邊緣、囚禁和流動、整合與遠離。它還被認爲是政府和治理的地點,集體行動協調的地點——後者建立在妥協、集合、和超越城市競爭範疇的代表的基礎上。
(四)個人、社會與承認
80年代末互動理論被引進法國後,“認同”這個概念在歐洲——法國——社會學舞臺上佔據了中心地位。然而在中國卻沒有發生這個現象,強勢佔領整個中國社會學領域的是“關係”這個問題。不過中國的社會心理學家卻在他們的研究中將“認同”與“關係網”聯繫起來。
楊宜音解釋了有關“關係”的各種理論在文化心理學和跨文化心理學中的發展過程。她提出建構互動秩序的過程會產出一個“雙重的我們”;強調定義人際關係時需要將親緣關係的影響以及雙方互相信任和責任關係考慮進來。在她的理論中,“我們”的概念在雙重機制下產生;一方面是“我”的特定邊界,即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的特定邊界;另一方面則是類別化、認同和社會歸屬感。在我們看來,中國社會中自我和別人眼裏的身份認同就是通過這個“雙重的我們”的概念被建設起來的,而在歐洲,身份認同是在個人發展過程的某一時間點的“本我”和“自我”,在與“他人”接觸過程中,個人認同中有可能發展出“我們”的概念。中國人因此是多重的,他處在一個轉型社會中,他所擁有的社會資源決定著他能夠進入的社會化空間的數量。
劉世定也對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進行了研究。他選取的角度是產權這個中國的中心問題。根據他的描述分析,1979年以來公有制、集體所有制和私有制並存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其產物之一就是混合型經濟機構的出現,另一方面又促進的“自我擁有”的發展。由此可見個人存在的基礎也已經改變。與此呼應,Robert Castell區分兩種個人:擁有一定面積、一定位置和財產因而成爲自己的主人的“過剩個人”;以及不受集體制度保護或無法進入能提供保護的集體,擁有少量資源和支援,因而在“擁有自我”的過程中困難重重的“短缺個人”。通過中國所有制,社會認同秩序的問題浮出水面。

刘世定 图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我們注意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20年來,當代的個人,不管他是不確定的、自省的還是獨立的,總在歐洲和法國社會學界佔據中心位置,然而在中國社會學舞臺上卻幾乎見不到這樣的個人。這個現象證明,在歐洲有這樣一個個人化過程,“獨立”標準在人們生活中日趨重要。它意味著個人面對的機會和失敗風險是等量的。
正如考夫曼所發現的那樣,過去,社會結構支撐個人,個體的反思(或反身性)水準與社會結構相一致;但今天個人要採取行動必須首先要有一個身份認同,只有首先能夠管理自己才能實現個體化。François Dubet認爲,社會作爲一套完整的組織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日趨明顯的等級化與階級關係,形式多樣的集體表徵和行動,和社會制度自身功能的削弱。“獨立”於是成爲衆心嚮往的理想但同時又帶有極大限制性的標準而使不同個體在它面前不平等。主體性在歐洲社會已經成爲一個集體問題,一個“不確定的個體”於是誕生於這個背景中。這個個體需要面對能導致不良後果的各種不確定情景,根據他在不同歸屬空間和活動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他在社會尊重與蔑視之間來回,在自尊與羞愧間遊蕩,總之難以真正成爲自己。
.png)
由於研究這個問題本身固有的困難,中國社會學和西歐社會學之間的接近顯得又真實又虛擬。很難說清孰近孰遠。以下要討論的是我們認爲有共同點的主題:
-國家與集體行動
-勞動市場與就業
-不平等與“碎片化社會”
-公衆領域和多重規範秩序
(一)國家與集體行動
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在中國社會學中佔據的地位不容忽視。這個問題的提出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理論角度。它時而與權力問題粘連,時而與治理方式相關,與公衆空間建設、對抗形式或集體行動的各種方式相關。雖然在過去公衆領域和政治領域之間有混淆的趨勢,但今天這兩個領域之間的界線有逐漸明朗化的跡象,這種分化促進了享有權力的、對自己行爲負責的、獨立的個體在公衆領域形成過程中的緩慢誕生。很有意思的是,部分學者用一種實用主義的眼光看待中國現實,把它看成是其成員連續不斷的建構,這建構的意義就來自於建構它的活動本身。在這裏,統治不被看成是民間社會平常情境與國家之間的一種連續長期的關係。2000年開始中國社會學裏又多了一片新的工地,那就是集體抗爭和動員的新形式。這些研究以農民、工人和城市中產階級居民抗爭運動爲焦點。這些抗爭形式的主角是那些在公民社會成型過程中同國家、地方政府和個體行動者有着對立關係的群體。
這些研究處於社會運動社會學和暴亂社會學之間。因爲它們接近圖海納、杜貝和維沃爾卡所定義的社會運動——有組織的、在特定的社會類型中發生、由中心社會衝突演變而來、集體行動者在其中組織社會鬥爭的具體形式——的社會學。但是中國有關工人農民運動的研究同時也讓人聯想起法國有關城市暴力和暴亂的研究,這些暴力和暴亂充分表達了由“社會寵兒”和備受汙名化、歧視和隔離的“受內部排斥的人”之間不平等和不公平發展而成的社會衝突。
(二)勞動市場和就業問題
90年代初以來,勞動市場的形成受到衆多研究者的關注。從90年代末起,對網路問題高度敏感的中國社會學家先後重新解讀了波蘭尼的“大轉變”理論和布洛維有關當代共產主義國家市場變化的“二次大轉變”理論。於是,沈原提出中國處在兩次大轉變的交界地帶。衆多研究成果中,勞動市場被定義爲是誕生於這兩個大轉變的經濟制度,它是與共產主義秩序相聯的社會建設產物,引發深層結構變化,導致出現新的社會分層。同時,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促使勞動市場上經濟協調新形式的出現,而勞動市場的重構則被認爲與中國高速活躍的社會分層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社會分層體現的是正在形成中的勞動市場的內部分割。以劉世定爲代表的社會學家突出了區分國家和地方勞動市場、農村和城市勞動市場對理解中國雙重經濟轉型的重要性。
歐洲尤其是法國的學者曾在80年代大量應用美國的勞動市場分割學說以及二元對立學說,90年代起,爲了解釋中國勞動市場的變化,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社會學家身上。以李強、李培林和李春玲爲代表的一部分社會學家提出了中國勞動市場二元化的假設:在這個大市場內首先存在一個一級市場,他雇用的是勞工擁有高學歷、領取高工資並且享受舒適的工作條件和牢固的社會保障;其次還有一個次級市場,進出其中的则是流動人口組成的劳工,他們技術含量低,工资微薄,而且不能享受有利的工作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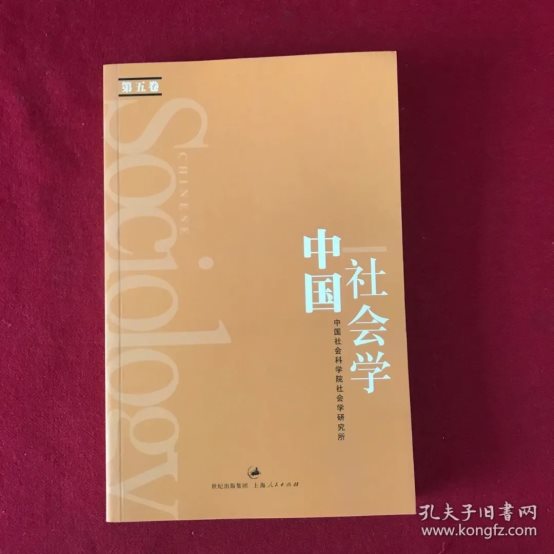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社会学》辑刊,图为第五卷 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中國經濟社會學中主要採用的是網路、社會聯繫、社會資本這些角度。學者普遍認爲家庭和社會網在社會化、去社會化和再社會化過程中起了中心的作用。網路概念的使用提出了“聯繫”概念的使用問題。Granovetter的學說從90年代起在法國得到廣泛應用,在中國也一樣。值得指出的是,中國與法國的經濟社會學借鑒同一批北美的部分研究以期各自找到特別的道路。
在法國也存在類似的科研:有關失業多種形式、貧困新形式產生和次就業形式的制度化,大眾階層子女的就業情况的弱势化,移民的勞动市场民族割據的新形式等,它們完全可以與上述這些中國的科研成果建立對話。
(三)不平等與“碎片化社會”
李培林(2002)、陸學藝(2002),李強(2002)和其他一部分社會學家強調的則是在經濟轉型與社會變革同時進行的大背景中所產生的社會碎片化的不同形式。對於李培林來說,碎片化在三個範疇發生:1.城鄉之間。這一範疇的碎片化在進城尋找工作但不果的移動人口身上尤爲明顯。2.藍白領之間,更確切地說是“新貴”和藍領之間。3.在市場經濟中就業並佔有普遍承認的社會地位的人群和被迫在非正式經濟或違法經濟領域内從事非正式工作的人群之間。經濟改革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1978年起,社會流動的路線開始變得多樣化,而其中的結構性障礙也經歷了重新定義(李春玲2005)。李路路提出兩種統治機制:1.經由國家和社會規則制度化的權力;2.統治集團通過社會和符號統治而“天然化”的社會等级關係。李的理論與布迪厄的遺傳結構主義有一定的呼應,但他的再生產與社會統治帶有強烈的共產主義文明氣息,其中的制度化的權力和符號統治通過與中國社會歷史相關的文化、社會、制度和政治秩序而建立的。
孫立平 (2002, 2003) 在他的著作中揭示了中國社會的兩個極端。其中一端是被他稱作是“新貴”的階層,另一端則有兩個極爲貧困化的兩個階層構成:西北和西南向來處於劣勢的社會群體和由失業人員、下崗工人及農村流動人口組成的新群體。後兩個階層可以說是中國社會正在形成中的“底層階級”的主體部分。孫立平特別指出,在轉型社會中,各種主要的社會整合形式以融入市場經濟爲中心,中產階級開始形成,而其中兩極分化只用了十年時間就形成,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高速度的過程。於是相應的新現象就是社會中就出現了一些邊緣化區域。隨著國企結構精減,私有經濟高速發展,農村就業增長減速,失業以不同形式出現,觸及不同人群——如下崗工人(佟新,2003, 2005)和大學畢業生。

佟新 图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上述分析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與法國的 F. Dubet 和 R. Castel 的觀點相呼應。F. Dubet 提出法國社會中的現代性強化了社會差異,使社會不公的領域增多。R. Castel 曾將法國社會定義成社會附著力程度不同的三個區域的集合體:以爲穩定的職業融入和牢固的社會關係爲特徵的整合區;生產活動缺席和社會孤立共同導致的脫離區;以不穩定工作和脆弱人際關係爲特徵的日趨擴大的脆弱區域。
(四)公衆領域和多重規範秩序
張靜的文章分析的是1968年至今公共言論評價的建構模式的變遷。雖然在過去公衆領域和政治領域之間有混淆的趨勢,但今天這兩個領域之間的界線有逐漸明朗化的跡象,這種分化促進了享有權力的、對自己行爲負責的、獨立的個體在公衆領域形成過程中的緩慢誕生。我們也能從這個分化中看出社會平等和公民權利的承認逐漸上升成爲公衆行動的規範。在公共言論評價中贊同與反對都遵守道德社會標準,而由於正當性理據、行爲、實踐、言論的多樣化,規範和承認秩序產生分化並且在“公衆事物”的分享問題上產生衝突。儘管商業和農村的名種協會和民間組織可以在受控制的前提下進入其中,這個公衆領域依然與民主公衆領域差異很大。

张静 图源:山东大学。
法國的部分研究將公衆領域定義爲“歸屬與認同互相發生聯繫和碰撞的政治原始舞臺”,它們與上述中國研究可以進行對話。更確切地說,與這些中國研究可以對話的是那些對於“公衆角鬥場”的研究,所謂“公衆角鬥場”事實上是一些多標準空間,其中包括評判、相信、存在的多種正當化的方式,它們是被不同等級的憲法原則、法律機制、制度框架和公民普通生活認可的。
.png)
中國社會學家從文明秩序出發,又將結構化過程、主觀性和互動整合進他們的分析。於是,文明、結構化過程、主觀性和互動之間的不同組合產出不同的理論觀點。在國際社會學界,他們所創造的理論空間非常新穎,因爲互動、主觀、結構和文化等秩序在這裏交匯。他們就是憑藉這樣獨特的社會學思考方法是一些出人意料的理論空間升起在西方社會學思想中。中國的社會學理論中,有一些以正式的學派存在,另一些則不然。
(一)從實踐社會學到轉型社會學
在正式的學派中,孫立平爲他的社會學起名爲“實踐社會學”:“它分析社會事實有活力、動態而非靜止的方面,認爲只有在實踐情境中才能找到它們的正常狀態,當然同時也不忽視結構和制度因素。相反,應該更多關注結構和制度在運作過程中所產的效應。其次,它的重點在於事物和現象在實踐中的邏輯,而這種邏輯在靜止狀態中難以發現……第三,實踐的地位‘高於’靜止的結構或制度。”在他提出的社會學裏,行動者有意識地扮演角色,主觀性與社會實踐的多樣性和動態活力、歷史事件和“隱形”社會形式之間建立聯繫。
90年代起,郭于華和孫立平對文革期間中國農民做了研究,他們借助口述史去解讀國家和農村社會的建構。這些工作就是實踐社會學最好的實例。同樣,沈原提出分析工人勞動的微觀情境、經濟制度和二次大變革(波蘭尼和布洛維學說的綜合)背景以便分析工人階級的重構過程,他也處於同一個理論空間。
另外,研究者們將社會轉型看作完全不同於東歐國家的中國特有的共產主義文明的產物——文明作爲價值和社會生活運作體系——他們會運用實踐社會學來深化社會轉型理論。實踐社會學和轉型社會學將共同努力,來分析中國社會的社會變遷和中國社會學家身處的文明轉捩點。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末的實踐社會學將結構化、文明化、互動和主觀性放在同一高度;之後這些概念之間逐漸地出現了等級關係,結構化和文明化成爲主導概念。我們有理由假設這是因爲轉型的分量使得學者們賦予結構化以新的地位。不管怎麼說,庫恩意義上的理論範式正在成型。
(二)科學多元性和理論變奏
在沒有“名”的學說中我們找到三種理論,由於賦予概念的地位不同,它們對“結構化/實踐行動/互動/主觀性”之間的關係的建構方式也不同。應該說明的是,同一個社會學家有權力根據研究對象而改變研究角度。中國社會學家與法國同行不同,由於他們始終考慮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因此表現出明顯的認知靈活性。
這些理論分別與結構主義、互動論或個體/社會關係學說有一定的淵源並相當堅守自己的研究範。
-結構與策略
一部分社會學研究的對象要求運用結構化和文明事實這兩個工具。這主要包括經濟社會學中有關“單位”和經濟制度變遷的研究以及有關社會再生產的課題。研究者根據共產主義文明做過調整的結構主義傾向在此較爲突出。另外,關於城市化和社會分層的成果揭示個人和集體如何在經濟政治制約的條件下制定策略,這裏行動者的行動能力受制於轉型背景。
-互動、集體行動和結構
中國社會中,不同人群要求社會給予各種不同的承認。對社會運動和集體動員的研究使我們瞭解轉型背景如何在這些人群中生產互動和集體行動。正是這些人的所做所爲建設著社會。行動者的詮釋能力成爲一種真正的結構性的反省能力。有關國家和個體關係的研究從互動出發以結構爲終點,社會學家不懈地研究互動與結構之間的關係,他們堅信這種關係絕不是一種穩定的平衡關係。
-社會結構、個體和社會
還有一部分社會學家,他們更關心受制於轉型中的國家和市場的行動者。正如對流動人口經濟社會整合的研究所顯示的那樣,行動者在這裏被看作是有反省能力的、能夠成爲主體的個體。中國社會以客觀現實和主觀現實的雙重身份出現,而這兩種現實永遠處於動態的隨時需要重新定義的對稱關係中。個體的建構問題因此被提出來。中國社會學家解釋說在西歐民族國家的形成促成了現代公民的產生,而在中國,個體永遠在不同歷史時刻借助與個人和集體命運的關係中出現。對主觀性的理解是另樣的,在社會分層、社會沖突突顯和對他人信任危機的背景中,它與“我們”和“他們”的形成息息相關。
法國的社會學建立在個人主義/整體主義、客觀主義/主觀主義、微觀社會學/宏觀社會學這些永遠的對立基礎上。而中國社會學的主導思想卻見不到兩分論,它是多元的。我們可以思考一下爲什麼中國各種社會學思潮不停探討西方社會學的範式。庫恩認爲在科學發展過程中歷史的角色舉足輕重,我們則認爲在理論創造的方式和類型問題上文化的影響值得深究。
文献來源:《社會理論學報》,2009年,第十二卷第二期,267-288頁。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文字编辑:刘展华、罗影、许方毅
推送编辑:李家乐、罗影
审核:孙飞宇、许方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