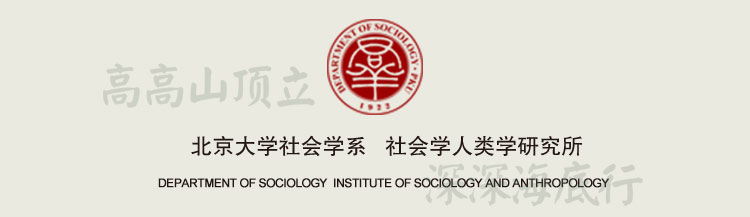謝立中:走向“多元話語分析”:後現代思潮的社會學意涵(下)
謝立中(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儘管對“後現代挑戰的社會學意涵”有著種種不同的理解,但本文作者傾向於接受的看法是:這一挑戰最主要的內涵就是試圖否定作爲全部現代主義社會學理論之基礎的“給定實在論”傳統,用一種多元主義的“話語建構論”的立場來取代之;儘管這一立場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評和詬病,具有某些爲一般人所難以接受的“缺點”或“局限”,但正如塞德曼、布朗等人所指出的那樣,它其實蘊涵著一種與人們通常所熟悉的那些現代主義社會學硏究框架很不相同的社會分析框架,從而有可能爲社會學硏究開闢一條新的發展方向和研究路徑。
.png)
一種“精神錯亂”,一種“巨大的無意義的虚空”,一種“心智死寂之時”——多倫多大學的J. 奥尼爾(J. O'Neill)教授在其所著《後現代主義的貧困》一書中使用這樣一些辭彙來稱呼“後現代主義”思潮。至於後現代主義者們,奥尼爾說,則“應該被理解爲一些宗教狂熱分子,或者理解爲打破上帝偶像的破壞者,而根本不能被视爲現代科學和藝術的智者。”
如引言中所述,在社會學以及其他一些學科內,對後現代主義思潮加以拒斥是常見的一種反應。J. 奥尼爾只不過這些人當中的一個典範而已。人們常常批評後現代思潮與現代科學思維準則(如概念明確、表達清晰、邏輯嚴謹等)背道而馳、其論述常常自相矛盾(如一方面抨擊大敘事,另一方面自己又構造出一些新的大敘事等)、對社會現實的批評和分析都缺乏有效的規範基礎等等。因此,就像奥尼爾做出的那樣,人們常常抱怨說:這樣一些人及其思想爲什麽應該被我們所記住呢?

約翰·奧尼爾(John O'Neill,1933-2022),知名社會學家,多倫多約克大學教授,提出“野性社會學”概念。圖片來源:社會學會社公眾號文章《奧尼爾 | 人類身體的未來形態》。
當然,在社會學家們當中,對後現代主義思潮持拒斥立埸的人並不都像奥尼爾那樣尖刻。持溫和拒斥態度的也不乏其人。Z. 鲍曼(Z. Bauman)和G. 瑞澤爾(G. Ritzer)就是其中的兩個代表人物。儘管他們也認爲後現代主義思潮從總體上看是一種不可接受的東西,我們無須也不應該接受作爲一種新的社會研究程式和方法的“後現代主義”,但另一方面他們也都承認後現代主義思潮並不是像一些人說的那樣一無所是,而是包含著許多“對社會學理論非常有用”的觀點,對於這些“有用的”觀點我們應該認真地加以思考和吸收,用來補充和修正我們現有的社會學研究模式。
與奧尼爾、鮑曼、瑞澤爾等人在不同程度上明確地拒斥後現代主義的立埸不同,S. 塞德曼(S. Seidman)、R. 布朗(R. Brown)、S. 哈丁(S. Harding)、B. 阿格爾(B. Agger)、N. 登辛(N. Denzin)、C. 勒麥特(C. Lemert)、W. 斯科特(W. Scott)和L. 埃德爾曼(L. Edelman)等社會學家則對“後現代主義”思潮採取了一種積極認同和明確接受的立埸。儘管在對後現代主義基本思想及其所含相應社會研究模式的理解和闡釋方面不盡相同,但他們都一致認爲,現代主義社會學正日益明顯地暴露出它那固有的局限,後現代主義思潮正爲現代主義社會學提供了一個可行的另類選擇;後現代主義並非只是包含著某些可以用來補充、修正現代主義社會研究模式的觀點而已,而是蘊涵著一種與現代主義社會研究模式完全不同的社會研究模式。因此,他們大都致力於將後現代主義的一些基本思想引進吸收到社會學領域當中來,試圖爲社會學研究嘗試某些新的思路。
正如後現代主義者所已經指出的那樣,無論是拒斥者的態度還是擁抱者的態度,對於它們的是非對錯我們其實都無力做出最終的評判。但作爲一項個人的選擇,筆者個人傾向於後一種態度。因爲我覺得它至少可以給我們提供一次機會,讓我們得以考察一下在傳統的(現代主義)社會研究模式之外,還有沒有其他一種不同的社會研究模式?如果有的話,與傳統的社會研究模式相比,這種新的社會研究模式究竟又有何特別之處?
我認爲,正如塞德曼、布朗、勒麥特等人所說的那樣,與傅統的(現代主義的)社會研究模式相比,後現代主義思潮——如果能夠對其中所包含的上述諸多基本思想恰當地加以理解和闡釋的話——的確隱含了一種可供我們選擇的新的社會研究模式。與前面關於現代主義社會學及後現代主義思潮之特點的敘述相對應,後現代主義思潮所隱含的這種社會研究模式的基本特徵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簡要地加以描述和勾勒:
首先,與傅統的(現代主義的)社會研究模式相比,後現代主義思潮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對社會研究的對象提供了一套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新認識。既然無論是社會結構、社會事件等“外部世界”還是意識、無意識、本能等“內部世界”都不是一種給定的實在,而是由有關的行動者(日常生活中的行動者或科學研究過程中的研究人員等)借助於特定的語言符號(及相應的話語/文本/理論)建構起來的,那麽,當我們在對這些現象進行研究之時,就不能把它們再當作一種獨立於人們所使用的語言符號之外的給定性現實,而必須要把它們當作是一種話語的建構物來加以看待。
這也就意味著,要想理解這樣一些“現象”的產生和變化,就既不能像實證主義者所倡導的那樣把各種被看作是既定“事實”的社會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及其規律當作自己的探求對象,或像批判理論家們所倡導的那樣把各種社會現象在社會與歷史總體當中的“客觀”邏輯關聯來作爲自己的研究對象,也不能像詮釋社會學家或現象學社會學家們所倡導的那樣把行動者賦予行動之上的主觀意義及其意向過程當作自己的探求對象,而是要把行動者在特定話語系統的約束或指引下建構特定“社會現象”乃至“社會世界”的過程與機制當作自己的探求對象,通過對這一過程與機制的瞭解來理解和解釋被人們用某一特定話語形式(概念結構、陳述模式、修辭模式、文本模式等)來加以標示和述說的那種社會現象或社會世界,以及這一現象或世界的存在與變化。
例如,對於“今年北京地區的失業率已經下降到4%”、“我國城鄉之間社會兩極分化的程度近年來持續擴大”、“恐怖分子昨襲擊了海灣物資大樓”等這樣一些“社會現象”,我們就既不能將其作爲一種純粹給定的“客觀事實”來加以描述和分析,也不能將其作爲一種某些行動者(記者、學者、政治家或普遍百姓等)的主觀釋義來加以看待,而應該將其作爲某些行動者在特定話語系統的約束或指引下以某些特定的概念、陳述、修辭和文本模式等所完成的一種話語建構來加以看待。
當然這並不是說,上述語句所陳述的那些現象都不是“事實”(或“實在”),而只是一些“話語”而已。而只是說,這些“事實”(或“實在”)都是一些與特定的概念(如“北京地區”、“失業率”、“城市”、“鄉村”、“兩極分化”、“程度”、“擴大”、“恐怖分子”等)、陳述、修辭和文本模式相聯繫的“事實”(或“實在”),由特定的概念、陳述、修辭和文本模式構建起來的“事實”(或“實在”)。離開了這些特定的概念、陳述、修辭和文本模式,它們就可能不存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確實可以說“文本之外別無它物”);當人們使用另外一些特定的概念、陳述、修辭和文本模式來觀察和理解社會世界時,所獲得或建構起來的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些“事實”(如“今年北京地區的失業率沒有變化”、“我國城鄉之間社會兩極分化的程度近年來有所下降”、“自由戰士昨襲擊了敵軍需倉庫”等)。
因此,要想使我們對這些所謂的“事實”(或“實在”)有一個適當的把握,我們就必須意識到它們的話語建構性質,將它們被特定的概念、陳述、修辭和文本模式建構起來的過程和機制當作我們對其進行考察時的首要探求和分析對象。因此,受後現代思潮啓發而形成的這種社會研究模式將是一種以社會世界的話語建構過程爲對象的研究模式。
顯然,對於這樣一種研究對象的探求和分析,同樣也不能借助於傅統(現代主義)社會研究模式常用的那樣一些以“給定實在論”爲前提而形成的方法(如實證分析、批判分析、詮釋學或現象學的意向分析等),而只能借助於二十世紀後半期以來在語言學、社會學、新聞學等學科领域中新興的一種方法即“話語分析”或“文本分析”方法。因此,正如勒麥特所指出的那樣,這樣一種由後現代主義思潮啓發而來的社會研究模式“將把話語既當作主題又當作社會學分析的手段”。鑒於此,我們也可以首先把這種社會研究模式稱之爲“話語分析”模式。在這方面,受後現代主義思潮啓發的社會學家們可以從韓禮德、格賴斯、薩克斯、迪克、费爾克勞夫等“話語分析”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中學習、借鑒許多富有價值的方法和技巧。

《話語分析――社會科學研究的文本分析方法》書影,[英]諾曼•費爾克勞( Norman Fairclough )著,趙芃譯。圖片來源:豆瓣讀書。
當然,同樣需要說明的是,將話語分析作爲社會研究的主要方法這一點也並不意味著以往人們在社會研究過程中所採用的那些分析方法就完全沒有意義了。像因果分析、批判分析(辨證分析、總體分析)、意向分析(現象學分析)等分析方法都仍然可以使用,只不過它們的意義將發生巨大的變化:它們將轉化成話語分析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那種因果分析、批判分析(辨證分析、總體分析)、意向分析(現象學分析)。
以“因果分析”爲例:在以社會現象的話語建構過程爲探討和分析對象的社會研究者那裏,對以特定的概念、陳述、修辭和文本模式等建構起來的不同“事實”(如“自殺率”與“氣候”、“年齡”、“受教育水平”、“社會整合程度”等)進行“因果分析”也仍將可以是一個重要的分析內容,只不過不僅此時的“因果”概念不具有既定的“客觀意涵”(它本身乃是一種話語的建構,其涵義乃至其本身的存在與否均依不同的話語系統而有所不同),而且其分析所得結果也不再像以前那樣被認爲是對諸既定“客觀事實”之間因果關係的揭示,而只是對由特定話語建構起來的諸“事實”之間之因果關係的揭示。因此這種“因果分析”實際上只是話語分析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
其次,與傳統的(現代主義的)社會研究模式相比,後現代主義思潮也對我們在社會研究過程中使用來作爲社會研究和分析之直接材料的那些話語或文本(資料)的性質也提供了一種與以往全然不同的新認識,對我們理解和詮釋這些話語和文本資料指明了一條新路徑。後現代思潮對表現主義的批判,使我們意識到人們構造出來的任何話語或文本,都既不是對某種給定現實的“再現”,也不是純粹對人們主觀意識的一種表達,而是一種在特定話語系統約束和指引下所完成的話語建構物,是一種被人們生活於其中的話語系統所過濾過的、由人們依據自己的話語系統而建構起來的、因而是依話語系統的變化而變化的東西。
實際上,人們對世界的一切感知、一切言說、一切書寫,都是以特定的話語系統爲前提的。離開了特定的話語系統,人們就什麽也無法感受、言說和書寫。在很大程度上,人們只能感受、言說和書寫他(她)們的話語系統當中已經(顯在或潛在)擁有的一切。人們所能夠感受、言說和書寫的一切,實際上歸根結底只是從某個或某些特定的話語系統轉換而來的關於客觀或主觀世界及客觀或主觀世界某個方面、某個部分的具體話語或文本而已,而不是什麽客觀或主觀“世界本身”。
按照這一理解,我們在對社會研究中所使用的那些文本資料(問卷、統計、歷史文獻、訪談等)進行分析時,就不能像以往的現代主義者們那樣或者將其當成是作者對其所感知到的“客觀社會現實”的一種表達,力圖從作者所處的社會及個人的客觀歷史情境當中去尋求理解和詮釋這些文本資料之意義的線索;或者將其當成是作者對自己個人心路歷程和主觀意識的一種表達,力圖從作者個人的主觀意向過程當中去獲取理解和詮釋這些文本資料之意義的根據;而是要把它們當作它們的作者(文獻作者、訪談對象等)在一定話語系統的約束與指引下對自身社會生活經驗的一種話語建構,力圖從約束和指引著這些文本資料產生和變化的那些話語系統中來獲得理解和詮釋這些文本資料之意義的線索,以及通過對這些話語系統的分析、解讀與揭示來逵到對那些文本資料之生產、分佈和流通過程的理解和詮釋。
不過,這也並非是說“再現”一詞從此就完全不能使用,而只不過是說假如我們還需要使用這個詞的話,那我們對它的涵義也必須做一全新的理解。我們或許仍然可以說某句話語或某個文本是在“再現”著什麽,但它所“再現”的決不能是一種給定的實在,而只能是由特定話語系統所建構起來的一種話語性或文本性的“實在”。
此外,與人們通常所理解的不同,強調話語系統對人們感知、言說和書寫行爲的約束和指引作用,並不一定意味著對人們在感知、言說和書寫過程中之“主觀能動性(agency)”的完全否定,而只是意味著要對這種“主觀能動性”做一種與以往非常不同的詮釋。在感知、言說和書寫的過程當中,人們的主觀能動性依然存在(因而即使是在同一話語系統約束和指引下,不同的人或者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條件下也還是可能會有不同的感知、言說和書寫行爲)。但這種主觀能動性是受到了既定話語系統約束的,是一種在既定話語系統限制之下的主觀能動性,而不是一種無限制的能動性。
試圖通過對話語系統的探討來理解和詮釋話語的生產、分佈和流通過程,是福柯等人的一大貢獻。然而,在晚期的著述中,福柯更試圖通過對話語和權力之間關係的探討來進一步揭示系統形成及變化的動力與機制。他將話語系統形成和變化的動力與機制與權力的運作相聯繫,認爲權力關係是促成各種話語系統形成和變化的主要因素。
顯然,福柯的這種論點與我們這裏闡述的論點之間有著某種衝突之處。因爲按照福柯的這種論點,前述後現代思潮對“給定實在論”的批評就不能成立:因爲至少有一種“實在”是給定的,這就是權力;“文本之外別無它物”的說法也就不能成立:因爲至少有一種“事物”是在文本之外,這也就是權力。因此,假如我們接受後現代思潮對“給定實在論”的批評,那我們就必須否定福柯關於權力規定著話語系統形成和變化的基本論點。
第三,後現代主義思潮也對社會世界的話語建構過程以及對這一過程進行分析之結果的多元化狀態提供了一種更爲適當的理解。在受現代主義(無論是實證的、詮釋的還是批判的)社會科學觀念影響的行動者(也無論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動者還是社會科學研究者)那裏,獲取和表達關於對象(外部的社會世界、內部的主觀意圖等)的唯一“真理”都被視爲是一切思維和言說活動的基本目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則告訴我們,在包括日常生活和科學研究過程在內的人類所有的思維和言說過程當中,思維和言說活動結果的多元並存局面都應當是一種正常狀態,而非一種反常狀態。
以日常生活中有關社會世界的那些思維和言說過程而言,如前所述,在後現代主義者們看來,由於人們的思維和言說活動不是對獨立於我們的話語系統之外的那種“給定社會現實”的一種呈現或再現,而只是行動者在特定話語系統的指引和約束下以特定的話語形式對通常被視爲“客觀現實”的那些社會現象的話語建構過程;而在不同的時間、空間條件下研究者可能會擁有不同的話語體系,這些不同的話語體系將會使人們建構出非常不同的關於社會世界的圖像(image)(對於在話語系統A的約束和指引下被建構爲a的一個事件,在話語系統B中有可能被建構爲非常不同的另一事件b);而由於話語系統之間的不可通約性,由這些不同話語系統轉換或建構而來的不同社會圖像之間也將是無法辨別其真偽的。換句話說,它們將具有同等的“真實性”。
因此,面對著“今年北京地區的失業率已經下降到4%”/“今年北京地區的失業率沒有變化”、“我國城鄉之間社會兩極分化的程度近年來持續擴大”/“我國城鄉之間社會兩極分化的程度近年來有所下降”、“恐怖分子昨襲擊了海灣物資大樓”/“自由戰士昨襲擊了敵軍需倉庫”等這樣一些表面上看來互相矛盾的陳述時,我們首先要做的不是去尋找更多和更新的“證據”以辨明哪一個陳述才是更爲“真實的”或“正確的”(今年北京地區的失業率到底是下降了還是沒有變化?我國城鄉之間社會兩極分化的程度近年來到底是持續擴大還是有所下降?“海灣物資大樓”的襲擊者到底是恐怖分子還是自由戰士?),而是要去弄清楚這些互相矛盾的陳述各自都是在一些什麽樣的話語系統之下建構起來的,並由此認識到從不同話語系統來看它們各自所具有的確實性與合理性。
這也使我們進一步意識到,對於每一種現有的“社會世界”或“社會事件”圖像而言,在它之外都有可能存在著許多其他種類的相應圖像。它們可能都從不同的角度,豐富著我們對現有這一種“社會世界”或“社會事件”之圖像的認識。因此,儘量去獲取和增加與現有的某種“社會世界”或“社會事件”圖像相對應的其他圖像,應該是我們在社會研究過程中自覺努力的一個方向。
上述看法也同樣可以而且也應該被反思性地應用於“話語分析”這種社會研究過程本身之上:我們借助於一批文本資料和“話語分析”方法來對人們的話語建構過程進行分析後所得到的結果,也不是對這些話語建構過程的一種純粹“客觀再現”,而同樣只是一種被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所採用的話語系統所過濾過的、由我們依自己的話語系統而建構起來的、因而是依話語系統的燮化而燮化的“話語建構”圖像。因此,對於同一批資料文本,也就可以產生許多非常不同的理解或詮釋,獲得許多不同的分析結果。這些非常不同的理解或詮釋也都是同樣有效的,不能用其中的一個來排斥其他的那些理解或詮釋。話語分析的結果永遠不會是只有一種,而應該是並且也常常是多元化的。
在後現代主義思潮或受後現代主義思潮啓發的社會學家們看來,話語分析的任務也並不在於(像某些現代主義話語分析學者們所做的那樣去)尋求某種唯一的、最終可以得到公認的結果,而恰恰在於去尋求對同一文本資料的多種不同的理解(以豐富和擴展我們的認知),以及幫助不同的分析者、詮釋者去實現他們之間的溝通和對話。
因此,話語分析結果的多元化局面也不但不是一個有待於我們去努力加以消除的消極状態,而恰恰是一個我們在話語分析過程中應該努力去加以追求的目標状態。這種對話語建構及話語分析結果之多元化状態的自覺認可和追求,應該是後現代主義思潮所蘊涵的社會研究模式與以往那些話語分析模式之間的一個重要不同之處,也是我們爲什麽將這種社會研究模式稱之爲“多元話語分析”的主要原因。
當然,這裏也有一點需要說明之處。和前面討論中所涉及到的有關問題一樣,上述這些看法也不是要完全否定以往那種“真僞之辯”的價值和意義,而是要使我們對這種“真僞之辯”的價值和意義重新加以詮釋和界定。這種新的詮釋和界定就是:只有在同一話語系統內部這種“真僞之辯”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而在不同話語系統之間,“真僞之辯”毫無意義。
第四,後現代主義思潮還爲社會研究提供了一種反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如前所述,本質主義乃是各類現代主義社會學(實證主義社會學、詮釋社會學或現象學社會學、批判社會學等)研究模式所共有的思維方式。按照這種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我們從事社會研究時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透過各種具醴的社會“現象”去把握住這些具醴“現象”後面所共有的、規定著這些具醴“現象”之存在的那些“本質”特性。迄今爲止,這種思維方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我們的各類研究文獻和社會學教科書。
後現代主義者則告訴我們,我們在科學研究中所使用的所有概念和範疇都不能被看作是對所謂事物內在之固有本質屬性的標示,它們其實都只是這些概念和範疇的制定者在特定話語體系的約束和指引下對事物(的內涵和外延)所進行的一種符號“切割”或話語建構。不同的話語體系,對對象世界會有不同的“切割”或建構,形成不同的概念和範疇網路。這些概念或範疇既可以用不同的符號來標示,也可以用相同的符號來標示——例如,即使是同樣採用“家庭”這兩個漢字符號來表示的概念,在不同的話語系統中其內涵也可以有很大差別。如下圖所示:
.png)
原文圖表。
在話語系統A中,“家庭”概念由a、b、c、d四個基本特徵構成,在話語系統B中,“家庭”概念由a、b、c三個基本特徵構成,在話語系統C中,“家庭”概念由b、c、d三個基本特徵構成,在話語系統D中,“家庭”概念由a、b兩個基本特徵構成,在話語系統E中,“家庭”概念則由a、d兩個基本特徵構成。在a、b、c、d這四個基本特徵中,沒有一個是由上述五個話語系統中的“家庭”概念所共有的。自然,採用上述不同話語系統中的“家庭”概念來觀察“現實”就可能會形成完全不同的“家庭”外延。因而受不同話語醴系約束和指引的人,對於研究對象也就常常會有非常不同的界定或話語建構,並進而對研究對象得出一套與在其他話語醴系之下進行研究時可能得出的完全不同的研究結果。
例如,當我們把“家庭”界定爲是“建立在姻緣關係和血緣關係基礎上的人類共同生活的初級社會群體”時,應用這一概念去對“家庭”現象進行考察所得到的結果,與我們把“家庭”界定爲“建立在親密情感關係基礎上的人類共同生活的初級社會群醴”時所得到的結果就將會有相當程度的差異。當我們將“自殺”界定爲“行動者出於達到使自己死亡的目的而以主動或被動方式自願殺死自己的行爲”,而不是像塗爾幹所做的那樣界定爲“任何一樁直接或間接導源於受害者自身主動或被動的行爲,且受害者知道這一行爲的後果的死亡事件”時,我們對“自殺”現象進行考察所得到的結果也就將與塗爾幹當年所得到的结果大不一樣。
因此,我們在對某一項社會現象(如“家庭”、“階級”、“賣淫”、“自殺”等)進行研究時,就必須既意識到自己所用概念的話語局限,又應該努力去超越自己所屬話語體系的限制,嘗試一下從其他話語體系來考察這“同一”現象時將會得到什麽樣的結果,從而擴展和豐富我們對“這一”現象的知識,而決不應該去追求有關這一現象的某種唯一的“本質”認識。
當然,這也不是說“本質”一詞從此就完全不再能夠採用了,而是說這一概念也最多只是在某一話語系統內部才能加以言說。在某一話語內部,我們仍然可以沿用“本質”一詞來表示我們在對某一事物進行界定時所表述的那樣一些“特徵”。只不過在這樣做時我們應該記住這些所謂的“本質特徵”即非是事物固有的(而是我們的一種話語建構)也非是唯一的(其他的話語系統會有不同的建構)。
第五,後現代主義思潮對現代主義思想中所含“基礎主義”立埸的批評也使我們對西方思想中關於一般和個別、普遍與特殊、同一和差巽、總體和局部、中心和邊緣、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等知識之間關係的問題有一種新的認識。
後現代主義思潮修正了西方思想中關於一般和個別、普遍與特殊、同一和差巽、總體和局部、中心和邊緣、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等知識關係問題上的傳統解釋,批評了現代科學(包括社會科學)研究中片面追求一般性、普遍性、同一性、總體性、中心性和連續性知識,將這些方面的知識置於優先地位,把它們視爲更爲根本和更爲基礎的知識,甚至以它們來排斥與它們對立的那些知識的“基礎主義”以及與此相連的“普遍主義”、“中心主義”等思維傾向,使我們意識到個別性、特殊性、差異性、局部性、邊緣性、非連續性等方面知識的價值和意義,意識到理論概括的局限性,以及試圖簡單地用某種一般理論知識統攝所有具體知識的非適當性,從而使我們從一種新的立埸、以一種新的眼光去看待我們的知識世界。
我們也可以用下圖來解說一般和個別、普遍與特殊、同一和差巽、總體和局部、中心和邊緣、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等知識之間的關係。在這一圖式中,我們假定人們像上述話語系統E那樣依據a、d兩大特徵的有無來界定“家庭”概念。但即使如此,從這一圖式可以看到,在由這同一話語系統建構起來的社會世界中,處於不同情境之下的家庭也可能會有一些不盡相同的特點。例如,在情境A之下的家庭具有a、b、c、d、e五種特徵,而情境B之下的家庭則具有a、b、c、d四種特徵等等……。
.png)
原文圖表。
按照傳統的現代主義理論模式,人們通常會將對上述各種情境條件下不同類型家庭之具體特徵的描述看作是有關家庭的特殊(個別、局部)性知識,而將對不同類型家庭之共同特徵(a、d)的描述看作是比這些特殊性知識更具普遍(一般、總體)性的知識,認爲對於“家庭”這種社會現象的認知來說後者比前者處於更爲基礎性、中心性的地位,具有更爲重要的價值或意義。只要而且也只有把握住了家庭的這兩個普遍(一般、總體)特徵,我們對於“家庭”這種現象也就有了基本的認識;至於不同類型家庭各自具有的那些非普遍(一般、總體)性的、邊緣性的特徵,對於我們理解家庭現象的存在和變化則屬於可有可無的知識。
然而,在後現代主義者那裏,情况則完全不同。後現代主義者們認爲,對於各個具體情境條件下“實際”存在的那些“家庭”來說,其存在和變化不僅是由所有類型家庭共有的那些特徵而且也是由各類家庭獨有的那些特徵所共同規定的;因此,如果只是掌握了有關所有類型家庭共有特徵方面的那種普遍(一般、總體)性知識,而沒有掌握包括這兩大類特徵在內的所有那些情境(特殊、個別、局部)性知識,就不可能對特定情境條件下那一類型家庭的存在和變化状况有適當的理解。
那種排除了有關非共有特徵方面知識的單純的“普遍(基礎、一般)性”知識是一種空洞的抽象,對於我們恰當理解研究對象來說並不具有比那些非共有特徵方面的知識更爲優越的價值。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對於理解各種特定情境條件下那些家庭的存在和變化這一任務而言,包含了普遍和特殊兩類特徵在內的情境性知識要更優越於只是概括性地包含了普遍特徵的那些一般性、總體性知識。後現代主義者們的這樣一種看法,顯然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值得我們參考借鑒。
和前面幾處討論時所遇到的情况一樣,這裏也並非是說那些“普遍(基礎、一般)性”的知識就完全沒有意義了,我們從此就不能去建構這種“普遍(基礎、一般)性”的知識了。其實,無論是有關一般性、普遍性、同一性、總體性、中心性、連續性的知識,還是有關個別性、特殊性、差異性、局部性、邊緣性、非連續性的知識等,都是我們人類生活所必需的知識。按照某些極端後現代主義者們的立埸,我們得到的就有可能只能是在數量上無限膨脹的各種零零碎碎的局部知識或無限多樣的“局部性知識”或“小敘事”,而無法得到一個有關世界或我們的社會生活整體的“示意圖”。這將使我們失去人類生活所必需的那種宏觀視野,甚至失去我們的認知與社會行動能力本身。
因此,我們既需要意識到“普遍(基礎、一般)性”知識的局限,也不能完全否定這種知識的價值。而只是應該在“反實在主義”或“話語建構”的立埸上來重新理解和詮釋這種“普遍(基礎、一般)性”知識的性質。我們應該意識到,我們通過歸納概括等過程所得到的那些“普遍(基礎、一般)性”知識也只是話語建構的一個結果,而非事物自身固有的屬性;對於某一同“名”的事物,不同的話語系統可能會有不同的“普遍(基礎、一般)性”知識。
.png)
或許我們還可以做一些進一步的討論,但我認爲,以上的描述和分析已經足以讓我們感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既不像奧尼爾等人所說的那樣只是一些精神錯亂者的胡言亂語,也不像鮑曼和瑞澤爾等人所認爲的那樣僅僅只是包含著一些對傳統社會學有益、可以用來補充和修正傳統社會學研究模式的“真知灼見”;在後現代主義思潮當中蘊涵著的,對社會學研究人員來說也當是最具深長意味的價值,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研究模式;這種社會研究模式是一種建立在(多元主義的)“話語(或文本)建構論”立埸之上、以話語分析爲基本特徵的研究模式(“把話語既當作主題又當作社會學分析的手段”);這裏的“話語分析”既繼承了迄今爲止哲學、語言學、社會學、新聞學、心理學等學科領域中話語分析研究的諸多成果,但在本體論、認識論的基本預設和具體研究程式方面又與它們有著相當的區別:和以往那些話語分析模式相比,它不僅在本體論、認識論的基本預設方面更多地突出和強調話語本身的建構性質、否定“實在”的給定性質,而且在具體研究程式方面也更自覺、更明確地追求話語建構和話語分析結果的多元化狀態。
綜合起來看,相對於以往那些被本文稱之爲“現代主義社會學”的社會研究模式而言,這種社會研究模式至少有以下兩點可稱道之處:
第一,和傅統的、現代主義的實證社會學、詮釋社會學與批判社會學研究模式相比,它無論是在研究的對象、研究的程式和方法,還是在研究的任務和目標方面,都的確爲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正像布朗和勒麥特等人所說的那樣,後現代主義思潮的確包含著一種“具有使我們社會學事業的方法、對象及其概念本身激進化的潜能”,以此爲基礎便可以發展出一種新的社會研究模式。儘管我們目前對這種新的社會研究模式給我們可能带來的利弊得失尚不能做出精確的評估,但可以肯定的是,作爲一種新的選擇,這種新的社會研究模式至少能夠讓我們的視野有所轉換,使我們對“社會世界”的理解和詮釋有所變異,因而值得我們用它去進行一些新的嘗試。
第二,從我們上面的描述和分析可以領悟到,和許多人通常所想象的有所不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後現代主義思潮所蘊涵的這種“多元話語分析”社會研究模式,在經過適當的理解和詮釋的情況下,實際上並沒沒有也並不必然要照以往傳統的那些“現代主義”社會研究模式的內容、概念及方法徹底地加以否棄,而是可以以一種新的方式將它們包容在自身之中,賦予它們以一種全新的意義和價值。譬如,我們可以否棄傳統現代主義的那種“給定實在論”立埸,但並不必須要否棄曾經與這種立埸相聯繫的“實在”概念以及相應的一些分析方法(因果分析、意向分析、批判分析等),而是可以在一種新的意義上來理解和詮釋它們並將它們重新包容進後現代主義思潮所蘊涵“多元話語分析”社會研究模式之中。一如前述,對於“現代主義”社會研究模式的其他一些內容、概念和方法來說,也是如此。
可見,這種新的社會研究模式所徹底否棄的,只是在傳統的“現代主義”意義上來理解和詮釋的那種“實在觀”、“再現觀”、“真理觀”、“本質觀”和“普遍觀”等,而非是曾經與這些觀念相連的內容、概念及方法本身。因此,我們其實可以將後現代主義思潮所蘊涵的這種“多元話語分析”社會研究模式與以往傳統的那些社會研究模式之間的關係比擬爲愛因斯坦相對論物理學與牛頓機械力學之間的關係,或非歐幾裏德幾何學與歐幾裏德幾何學之間的那種關係。在所有這樣一些關係當中,前者都只是否棄了後者所蘊涵的那種本體論、認識論方面的基本預設,以及與這些基本預設相連的那種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標的理解與與詮釋,並未將後者的內容、概念及方法完全否棄,而是在經過一番再詮釋後把它們重新包容於自身之中。無疑,儘管我們不能說這意味著前者比後者要“進步”,但至少我們可以說與後者相比,前者的內涵要更豐富些,因而當是更加可取。
概而言之:後現代主義思潮並非洪水猛獸,而是一座值得我們去深入開掘的寶藏;對於社會學研究人員來說,“多元話語分析”就是這座寶藏當中最具價值的東西之一;我們不應對其採取一種忽視或者輕視的態度,從而錯失改善或更新我們社會研究框架的機會。
文字编辑: 曹佳韬、代欣怡、吕灵
推送编辑:苟钟月、毛美琦
审核:孙飞宇、许方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