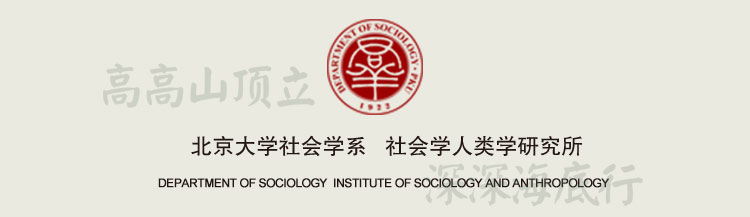謝立中:走向“多元話語分析”:後現代思潮的社會學意涵(上)
謝立中(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儘管對“後現代挑戰的社會學意涵”有著種種不同的理解,但本文作者傾向於接受的看法是:這一挑戰最主要的內涵就是試圖否定作爲全部現代主義社會學理論之基礎的“給定實在論”傳統,用一種多元主義的“話語建構論”的立場來取代之;儘管這一立場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評和詬病,具有某些爲一般人所難以接受的“缺點”或“局限”,但正如塞德曼、布朗等人所指出的那樣,它其實蘊涵著一種與人們通常所熟悉的那些現代主義社會學硏究框架很不相同的社會分析框架,從而有可能爲社會學硏究開闢一條新的發展方向和研究路徑。
儘管後現代主義思潮對孔德以來的西方社會學理論傳統所構成的挑戰已不是什麽新聞,也儘管已經有一些國內外的社會學者對這一挑戰的社會學意涵進行了富有價值的思考,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一挑戰在(包括中國社會學界在內的)大多數社會學者們那裏迄今仍然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和反響(用“置若罔聞”一詞來描述衆多社會學者,尤其是從事經驗研究的那部分社會學者對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態度恐不爲過);這一挑戰對於社會學研究(包括經驗研究)來說所具有的一些最重要的意涵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和廣泛的認可。
因此,深入考察和進一步闡釋這一挑戰的基本社會學意涵也就依然是一個既富有重大理論與實際意義又具有寬廣開拓空間的研究課題。本文(及相關系列論文)即是作者在《後現代主義方法論:啓示與問題》一文的基礎上就此課題再次所做的一個嘗試,目的是希望引起更多的人來關注和討論此一課題。
儘管對“後現代挑戰的社會學意涵”有著種種不同的理解,但本文作者傾向於接受的一個看法是:這一挑戰最主要的内涵就是試圖否定作爲全部現代主義社會學理論之基礎的那種“給定實在論”傳統,用一種(多元主義的)“話語(或文本)建構論”的立場來取代之;儘管這一立場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評和詬病,具有某些爲一般人所難以接受的“缺點”或“局限”,但正如S.塞德曼、R.布朗、C.勒麥特等人所指出的那樣,它並非只是爲我們修改、完善舊有的那些現代主義社會學研究框架提供了若干這樣或那樣的啓發,而是蘊涵著一種與各種現代主義社會學研究框架很不相同的社會分析框架,從而有可能爲社會學研究開闢一條新的發展方向和研究路徑。本文及相關系列論文的主要內容就是試圖通過理論與經驗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具體論述來說明這一基本觀點。
本文在結構上分爲三部分。在第一部分,筆者將根據自己對社會學文獻的閱讀和思考所得到的體會,對本文所謂“現代主義社會學”的基本特徵做一簡要概括;在第二部分,筆者也同樣將主要依據自己的體會來對本文所謂“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基本特徵及其對“現代主義社會學”所構成的挑戰進行描述和分析;以此爲基礎,第三部分則試圖對後現代主義思潮最主要的社會學意涵——它所蘊涵的一種與現代主義社會學不同的、新的社會研究模式進行一個初步的描述和勾勒。在本文的結語部分,我們將對蘊涵在後現代主義思潮當中的這種新型社會研究模式的相對合理性做一簡要的評論。
.png)
本文是在一個比較廣泛的含義上來使用“現代主義社會學”一詞,它在外延上涵蓋了現有社會學理論教科書上所介紹的絕大多數社會學研究取向或流派,這些名目繁多、表面上看來立場各異的“現代主義社會學”研究取向或流派也可以粗略地概括爲實證主義社會學、詮釋社會學和批判社會學三大基本類型(詳見下表)。

原文圖表。
這些不同取向、不同類型的社會學理論在基本預設、研究方法和具體理論見解方面儘管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但作爲“現代主義社會學”内部的不同派別或範式,它們相互之間也存在著一些基本的共同點。這些基本的共同點至少包括:(1)給定實在論;(2)表現論;(3)相符真理論;(4)本質主義;(5)基礎主義(將所有現象歸結到一些最普遍、最基本的本質及其原理)。
1.給定實在論(given realism)。
所謂“給定實在論”指的是這樣一種理論觀點,即認爲作爲我們感知、意識和言說對象的各種“事物”都是一種先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認知者或科學研究過程中的研究人員)的主觀意識及我們所使用的符號系統(話語/文本/理論)而存在、獨立於我們的主觀意識及符號系統之外、不依賴於我們的主觀意識及符號系統、有待於我們應用自己的主觀意識去認知和相應的符號系統去表述的一種純粹自主的、給定性的實在。更具體地說,在“實在”、我們的主觀意識以及我們所使用的符號系統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當中,“給定實在論”的看法一般是:“實在”是先於我們的主觀意識和所使用的符號系統而獨立存在的,而我們的主觀意識又是先於我們所使用的符號系統而獨立存在的。
實證主義社會學家大都是些比較典型的“給定實在論”者。無論是孔德、斯賓塞、塗爾幹、紐拉特一類早期的實證主義社會學家,還是帕森斯、默頓、達倫多夫、科塞、霍曼斯、布勞、科爾曼一類的後期實證主義社會學家,幾無例外都把作爲自己研究對象的“社會現象”看作是一種與自然現象類似、在我們的思想和言語之外獨立存在、由一些具有外在性和強制性的規律所支配的“物理性”實在。
例如,塗爾幹就明確地指岀“社會現象”是一種像“物質事物”那樣的“客觀事物”,它不僅外在於、獨立於、先於我們的主觀意識,而且也外在於、獨立於、先於我們所使用的符號分類系統(例如,原始的分類系統就不過是“社會”實在的一種表現而已);帕森斯雖然認爲社會實在中有一些“分析性的成分”是我們必須借助於一定的理論系統才能夠去認識和把握的,但他也依然承認這些成分是外在於、獨立於、先於我們的主觀意識和我們在認識它們時所需借用的這些理論系統而獨自存在的。

塗爾幹(Émile Durkheim,1858-1917),圖片來源:Wikipedia。
儘管詮釋社會學反對實證主義社會學關於“社會現象”是一種和自然現象類似的“物理性”實在的看法,主張各種社會現象(結構、組織、制度、事件等)本質上都不過是人們意向行動(或符號互動)的産物而已,社會世界是一個“意義世界”,要確切地把握社會現象,就必須理解和掌握建構這些現象的行動者在建構它們時賦予其行動之上的主觀意義。但和實證主義社會學相似的是,對於詮釋社會學家來說,作爲其理解對象的“行動意向”,對於作爲被理解者的行動者本人來說雖然是主觀的,但對於每個理解者(無論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認知者還是科學研究過程中的研究人員)而言,其實同樣也是一種先於其主觀意識及所使用的符號系統而存在、獨立於其主觀意識及符號系統之外、不依賴於其主觀意識及符號系統、有待於其去理解和詮釋的一種純粹自主的、給定性“實在”。
批判理論既反對實證主義,也反對詮釋學的社會研究模式,但儘管如此,自馬克思始的現代“批判理論”家們,其在“實在論”問題上的理論立場與實證主義和詮釋學兩大理論取向之間依然在不同程度上有著共同之處。
例如,和實證主義和詮釋學類似,經典馬克思主義就明確地指出社會是一個不依人的意志(包括意識藉以形成的語言符號)爲轉移的客觀實在,社會發展是一個由客觀規律所制約的自然歷史過程;雖然人們(主要是作爲集體而存在的人們)有意識的實踐在社會歷史過程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人類只有在掌握和遵循了社會歷史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才能做到這一點。馬克思以後的批判理論家們(如盧卡奇、葛蘭西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們)雖然比馬克思更多地強調和突出了“階級意識”在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重要作用,但他們依然承認:對於個人意識及其符號系統而言,社會依然是一個外在的、在先的、給定性的“實在”。
2.表現主義。
所謂表現主義,指的是這樣一種主張,即認爲我們的知識就是對各種純粹自主的、給定性實在的呈現、表現或再現(representation)。我們的知識(話語、文本、理論)和“實在”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表現”和“被表現”之間的關係。全部認識活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通過一些最佳手段和方法的運用來達到對各種既定的客觀實在的準確呈現、表現或再現。更具體地說,與前述現代主義關於實在、主觀意識和符號系統之間先後關係的看法相應,表現主義關於實在、主觀意識和符號之間“再現關係”的一般看法是:符號是意識的再現,意識則是實在的再現。
儘管在如何準確“再現”客觀現實這個問題上相互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但在把我們的認識/知識理解爲是對“客觀現實”的再現這一點上,實證主義社會學、詮釋社會學和批判理論之間也並無本質性的不同。
實證主義社會學家們認爲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之間沒有本質性的區別,都是一種“我們的意識無法滲入其中”的“物質性(或物理性)”的實在,因此,在認識和“再現”社會現象的程式與方法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也就不應該有什麽本質性的區別。我們只有通過應用在自然科學當中已經發展起來並被證明爲是卓有成效的那種“實證”科學方法(觀察、實驗、比較等)來認知社會現象,才能達到對社會現象的準確“再現”。儘管在具體的認知技術(如觀察技術)方面會有較大的差異,但社會科學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統一性。
詮釋社會學家們則認爲社會科學方法和自然科學方法之間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既然社會世界是一個意義世界,社會學家要瞭解各種社會現象,必須深入到行動者的主觀意識內部,去瞭解構造了這些現象的那些行動的意識過程,瞭解行動者在行動過程中賦予這些行動之上的主觀意義,那麽社會學家們爲把握社會現象而採用的研究方法就不能是自然科學中通用的那種簡單地從外部觀察去獲得認知的實證主義方法,而必須採用人們在閱讀和理解《聖經》等文本時所使用的那種“詮釋學”的方法即“理解”的方法。詮釋社會學家們認爲只有應用這種與實證科學方法不同的“詮釋”或“理解”的方法才能夠更好地把握與再現“社會現實”。
批判理論則認爲無論是實證主義的方法還是詮釋學的方法都不能夠幫助我們獲得對社會現實的準確再現,認爲它們之間雖然存在著種種對立和差別,但在以下這點上卻是共同的,即:它們都把研究對象當作是一種孤立的、靜止的東西來加以考察和分析,而未能看到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所具有的社會歷史性質,從而無法對社會歷史進程的總體作出適當的把握。
批判理論家們認爲社會歷史過程是一個通過主體和客體之間、理論和實踐之間、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相互作用而不斷趨向某種理想(自由、平等、解放等)狀態的“總體性”過程,認爲只有以辨證的“總體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社會現實,將社會現象置於社會的與歷史的總體過程當中,從它們在社會的與歷史的總體過程當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來確定它們的性質、意義,來對它們的産生、變化和發展過程展開一種批判性的考察,才能夠更好地把握與再現社會歷史進程。
在表現主義者(包括上述各種不同取向的社會學者)之間,就如何才能更好地再現“客觀現實”還可以有經驗主義(歸納主義)和理性主義(演繹主義)兩種理論立場之間的分歧。例如,在實證主義社會學家當中,塗爾幹(尤其是早期塗爾幹)可以視爲一個經驗主義者,帕森斯則是一個理性主義者;在詮釋社會學中,韋伯可以視爲一個理性主義者,布魯默則是一個經驗主義者;批判理論家們則多數是理性主義者。不過,無論是經驗主義者還是理性主義者,在認爲知識是客觀現實的再現這一點上也基本上是沒有區別的。
3.相符真理論。
既然知識是對客觀世界的表現或再現,那麽,判斷一項認知成果是否可以被接受的唯一標準就是看這項認知成果是否與其所試圖再現的客觀現實相符合。只有與其所試圖再現的客觀現實相符合的認知才能夠被稱爲“真理”,反之就是“謬誤”。現代主義者們一般都認爲真理具有唯一性,即就某個特定的認識對象而言,只能有一項認知結果(也就是最與其相符合的那項成果)可以被稱爲“真理”。因此“相符真理論”同時也是種“一元真理論”。
現代主義者們一般也都相信,通過將“理論”與“事實”相對照的辦法,我們也完全有能力來對認識結果的是非對錯作出有效的檢驗和判斷。通過這樣一種檢驗真理的途徑,我們就能夠不斷地把我們認知結果當中的“謬誤”性成分排除出去,而將其中的“真理”性成分積累起來,我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會越來越全面、越來越深刻
就“相符真理論”這一理論立場而言,現代主義社會學家們之間也沒有根本性的區別。
“相符真理論”在實證主義社會學中表現的最爲明顯。迄今爲止,對於包括實證主義社會學在內的所有實證主義者而言,檢驗“真理”的具體方式一直未有根本性改變,這就是將從一項認知成果中引申出來的經驗命題與從對客觀現實的經驗觀察得到的相應“事實”相對照,看前者是否能夠得到後者的足夠支援。
無論是塗爾幹、默頓之類的經驗論實證主義者,還是帕森斯之類的“分析實在論”實證主義者,或者是霍曼斯、布勞之類的演繹論實證主義者,儘管在社會學理論命題的發現途徑方面存在著種種爭議,但在“只有經過了經驗事實的檢驗、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得到經驗事實的支援、與經驗事實最大程度相一致的那些理論命題才是最終可以接受的科學命題”這一觀點以及“通過對得到檢驗的真理性知識的積累,我們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將會日益豐富和拓展”等觀點上卻沒有重大異議。
詮釋社會學家們雖然反對實證主義的社會觀及其方法論,認爲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問有著本質區別,主張只有採用詮釋學的方法、通過詮釋、理解人們賦予自身行動之上的主觀意義來理解和把握本質上由人們的意向行動所建構出來的各種社會現象,但在“相符真理論”方面與實證主義社會學家之間並無實質性差異。
例如,韋伯就明確指出,雖然意義詮釋是我們正確把握一項人類行動(及其産物)的必經途徑,但單純只是達到對行動的意義作出明確的、可理解的詮釋這一結果還並不足以讓我們宣稱對該項行動作出了正確有效的理解或解釋。韋伯認爲,對人類行動及其結果的一項適當詮釋應該顧及兩方面的標準,即“意義適當性”和“因果適當性”。前者指的是一項行動中相互關聯著的各個要素,可以根據我們的思維和情感模式而被確認爲構成了一種“典型的”意義關聯;後者則指“根據任一可被計算的、在理想情況下可被量化的概率規則,一個被觀察的特定過程(精神的或物質的)會依序跟隨(或伴隨)另一個特定過程而發生”;“事情前後序列的詮釋,如果我們根據經驗的規則發現它始終以同樣的方式進行,便是‘因果上適當的’。”也即是說,只有當一項行動既能夠在意義上得到明確的、可理解的詮釋,而這項詮釋又能夠得到經驗資料的證實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我們對於這項行動獲得了完全適當的詮釋。韋伯明確地宣稱:“一般說來,以結果來控制可理解的意義詮釋,正如每個假設需要透過時間過程來驗證,是不可或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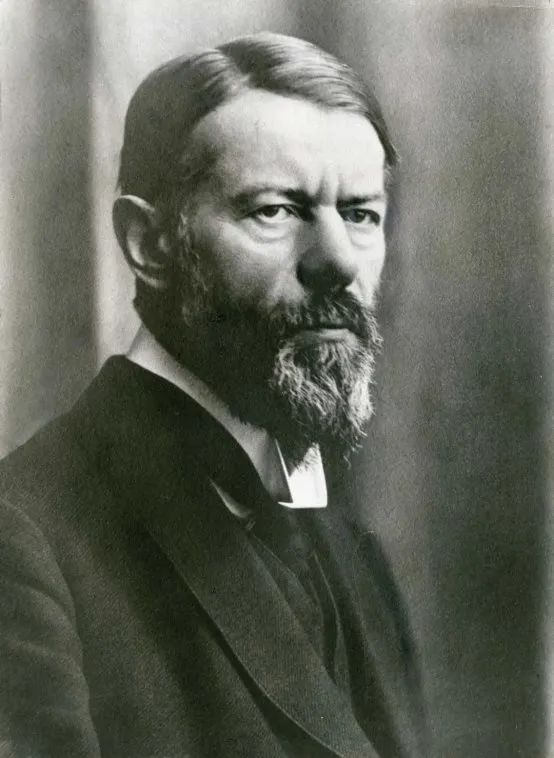
韋伯(Max Weber,1864-1920),圖片來源:Wikipedia。
馬克思主義雖然不同意像實證主義者(以及詮釋學者)那樣把“真理”的檢驗過程簡單地理解爲一種將“理論觀念”與“經驗事實”之間直觀對照的過程,主張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應該是人們的社會實踐,但儘管如此,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實質上依然是一種“相符真理觀”,只不過在這裏,一項理論觀點需要去與之“相符”的不是對既定現實進行觀察時所得來的“事實”,而是對人們在該理論觀點指引下從事的實踐過程的結果進行觀察所得來的“事實”。
4.本質主義。
現代主義思想把“客觀現實”區分爲“本質”和“現象”兩個方面:“本質”是事物的根本性質,是一事物得以存在及其與另一事物相區別的基本依據,“現象”則是事物的表面特點;“本質”是固定不變的、爲諸多“現象”所共有的,“現象”則是變化多樣、各個不一的;“本質”深藏於現象之後、只有通過抽象思維才能把握,“現象”則外露於事物的表面、是我們可以直接加以感受的東西;“本質”規定著“現象”,是“現象”存在的根據,“現象”則只是“本質”的表現形式;等等。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本質,這是現代主義思想的一個基本觀點(對一個概念下定義其實就是揭示該概念所指涉的那一事物的本質特徵,揭示該事物與其他事物之間的根本區別。反過來說,也只有準確地揭示了事物之本質的概念才是一種真正恰當的概念)。
按照這一基本觀點,我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就不僅是要達到對其現象的正確把握,更重要的是要透過現象達到存在於諸多現象後面的、爲諸多現象所共有的、規定著現象之存在的那些根本性質的正確把握,這樣才能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客觀現實”(當然,透過現象達到本質的手段和方式在不同的現代主義思想家那裏則可以是不同的)。
例如,我們在研究“賣淫”一類社會現象時,就是要通過比較(將存在於不同時間、空間範圍内的那些被我們稱之爲“賣淫”的具體“現象”進行比較,以及將這些被我們統稱爲“賣淫”的現象與其他那些未被我們稱之爲“賣淫”"的現象如“婚姻內性關係”、“通姦”、“一夜情”等現象進行比較等)方式得出“賣淫”這種社會現象的“本質”特徵,並以所得到的關於“賣淫”現象之本質特徵的知識去指導我們對此一現象所做的進一步觀察與研究活動,而不能簡單地停留在對不同時間、空間範圍內那些具體“賣淫”現象的描述和分析上。對“家庭”、“組織”、“階級”、“越軌”等等其他各種社會現象的研究也都當做如是觀。
幾乎所有的現代主義社會學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一個“本質主義”者。無論是孔德、斯賓塞、塗爾幹、帕森斯、默頓、達倫多夫、霍曼斯、科爾曼等實證主義社會學家,還是韋伯、舒茨、米德、布魯默、戈夫曼、吉登斯等詮釋社會學家,或是馬克思、恩格斯、盧卡奇、葛蘭西、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現代批判理論家,無不是以一種“本質主義”的態度來看待他們所研究的對象,來界定他們所使用的概念;也無一不是將透過各種具體“現象”來把握對象之“本質”作爲自己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
他們所使用的“工業社會”、“機械團結”、“有機團結”、“家庭”、“組織”、“結構”、“分化”、“整合”、“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階級”、“階層”、“性別(男性、女性)”、“人”、“理性”、“行動”、“傳統社會”、“現代社會”、“自由”、“平等”、“解放”等都是一些指涉著“客觀”社會現象某種固定不變之“本質”的概念。只不過在不同的現代主義社會學家那裏,對同一概念所指涉的事物“本質”的內涵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而已。
例如,以“現代社會”而言,孔德、塗爾幹、帕森斯等人都將現代社會的“本質”歸結爲“工業化”,韋伯等人則將現代社會的“本質”歸結爲“理性化”,馬克思主義者則將現代社會的本質歸結爲“資本主義”(“現代社會”中的其他現象則都只是“工業化”、“理性化”或“資本主義”的外在表現);等等。並且,這些不同觀點的主張者都堅持認爲只有自己對“現代社會”之“本質”的理解才是唯一正確的理解。這樣的爭論也同樣發生在對“家庭”、“階級”、“階層”、“組織”、“結構”、“社會”、“性別”等等幾乎所有其他概念所指涉的對象身上。這樣一些“本質主義”的爭論充斥著現代主義社會學的發展史。
5.基礎主義。
包括實證主義社會學、詮釋社會學和批判社會理論在內的全部現代主義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認同下列自柏拉圖以來在西方思想界就普遍得到流行的主張,即認爲現實事物之間的各種共性或同一性(本質?)在其普遍化或概括化的程度上具有等級性和種屬關係,我們關於研究對象的各種知識之間因而也具有等級性和種屬關係:普遍化或概括化程度越髙的知識在整個知識體系中就越是處於基礎的地位(以探究“第一原理”或“認識論原理”爲任務的哲學就是普遍化或概括化程度最高的知識,它是人類其他一切知識的基礎),普遍化或概括化程度越低的知識就越是處於派生的或從屬的地位;在普遍化程度較高的知識與普遍化較低的知識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蘊涵關係:前者已經包涵了後者,從前者中可以推演出後者來,把握了前者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後者。
我們關於客觀世界的知識在整體上構成一個由少數基礎性知識和許多派生性知識共同組成的樹狀結構。這種“基礎主義”的知識等級理論推動人們不斷地去追求對象之間更爲普遍的共性,由此形成許許多多具有基礎性地位的“整體性理論”或“宏偉敘事”。
就社會學領域而言,以下圖形所表示的知識結構觀念是實證主義社會學家、詮釋社會學家和批判理論家們都不會反對的:
.png)
原文圖表。
上圖也可以倒過來畫成樹形,其中宏觀基礎理論構成整棵樹的根須和樹幹,分支學科構成全樹的主枝杆,專題性研究及具體時空中進行的經驗研究則構成更細的枝杆和樹葉。
上述五個基本觀點中的前三個構成了羅蒂等人所說的西方思想中的“鏡喻”傳統,後兩個則構成了德魯茲和瓜塔里等人所說的西方思想中的“樹喻”傳統。它們共同構成了包括現代主義社會學在內的“現代主義”哲學和科學思潮的基本信條,“後現代主義”思潮則試圖將這些信條全部加以顛覆。
.png)
正如“現代主義”一詞一樣,本文也是在一個比較廣泛的含義上來使用所謂的“後現代主義”一詞,後者也是由許多立場、觀點不盡相同(甚至有較大差異)的理論取向所構成的一種內容廣泛、結構鬆散的思想潮流。它包括了庫恩、費也阿本德等人的“後實證主義”科學哲學,羅蒂的“新實用主義”哲學,加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德里達、拉康、巴特、福柯、德一曼等人的“後結構主義”(及解構主義)哲學、文學、精神分析學和“思想史”理論,以及布希亞、利奧塔德等人的“後現代主義”理論,等等。
這些不同領域、不同觀點的“後現代主義”者們之間在許多共同的主題方面也存在著巨大的分歧,但與“現代主義”思潮一樣,作爲“後現代主義”思潮內部的不同理論取向,它們相互之間也還是存在著一些基本的共同點。正是這些基本的共同點,使得我們可以將它們看成爲一種與上述“現代主義”思潮不同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爲了與上述“現代主義”思潮的基本點形成對照,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後現代主義”思潮對“現代主義”社會學所構成的挑戰,我們也將這些基本的共同點概括爲以下5個基本方面:
1.話語(或文本)實在論。
後現代主義者們普遍主張,作爲我們(無論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認知者還是科學研究過程中的研究人員)感覺、意識和言說對象的那些“事物”並非是純粹“自然”的或“給定”的,相反,所有作爲我們感覺、意識和言說之對象的東西以及我們的感覺、意識和言說本身都只是一種“符號/話語/文本性”的“實在”,都是由我們所採用的語言符號(及相應的話語/文本/理論)建構起來的。
事實上,語言符號並非像我們通常所以爲的那樣只是我們用來對某種給定的相應實在進行認知和表達的工具或媒介。相反,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那樣,語言就是我們的世界,就是我們的家。當然,這並不是說,在我們的語言符號之外根本沒有一個“客觀實在”,我們感受和意識到的一切都只是各種語言符號或“文本”而已而己;而是說,作爲我們人類感覺、意識和言說(乃至實踐)對象的那個世界只有經過特定語言符號的構造作用才能夠成爲我們的感覺、意識、言說和實踐對象。沒有語言符號,我們所感覺到的只能是毫無意義的一片“混沌”。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國哲學家,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圖片來源:潘易植《面向信仰與生活的的哲學方法論——海德格爾早期思想地形》,澎湃新聞。
後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家庫恩、新實用主義哲學家羅蒂、“哲學詮釋學”家加達默爾、後結構主義思想家福柯、拉康、德里達等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表達過上述主張。具體說來,後現代主義者們試圖說明:
(1)所有作爲實證科學之研究對象的“外部實在”都不是一種純粹給定的“客觀實在”,而是由一定的語詞符號(科學理論)系統建構起來的。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庫恩指出作爲科學家們研究對象的世界其實並非是一種純粹“自然”或“給定”的世界,而是由科學家們所採用的理論“範式”建構出岀來的。在不同範式之下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家們,所面對的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它們擁有完全不同的組成成分、結構聯繫以及運行規律。
例如,在亞里士多德的信徒們生活和工作的世界裏,不會有“擺”這樣的東西存在,也不會有關於“擺”的所有那些“客觀規律”存在;“擺”這種東西及其運動規律只能存在於伽利略及其信徒們的世界中。同樣,在道爾頓之前,化學家們生活和工作的世界,無論其成分、關係以及規律也都與道爾頓之後的世界大不相同:在道爾頓之後,“化學家開始生活在一個新世界中,在那兒化學反應表現出與以前大不相同的方式”。庫恩認爲,這種差異並非不同範式下的人們對同一個世界在“感覺”或“解釋”方面的差異,的的確確是兩個世界之間的差異。
在《反對方法》一書中,費也阿本德也表達過與庫恩類似的看法,指出在歐氏幾何學所描述的世界當中永遠不可能有“內内角之和不等於180度”的三角形,這樣一個三角形只有在非歐幾何學描述的世界當中才能被確認爲是一種“客觀現實”。
在《真理與方法》一書中,加達默爾則從海德格爾的思想出發,明確指出無論是作爲我們理解、詮釋之對象的“意義”世界還是作爲自然科學探究之對象的“自然”世界,都不是一些“只需我們堅守的固定而自在的對象”,一種我們能夠從人類語言世界之外的某個方位出發去遭遇的“自在存在的世界”。當然,這並非是說,在人類的語言之外沒有世界,而只是說“世界就是語言地組織起來的經驗與之相關的整體”、“世界自身所是的東西根本不可能與它在其中顯示自己的觀點有區別”、“一切認識和陳述的對象都總是已被語言的世界視域所包圍”,因此,“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能被理解的東西只是語言”,“誰擁有語言,誰就‘擁有’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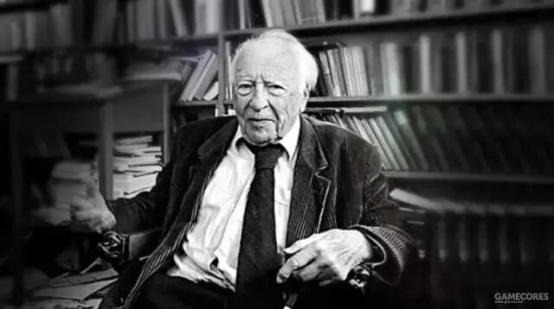
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德國哲學家,代表作《詮釋學:真理與方法》,圖片來源《鄧曉芒 | 從本體論向修辭學的突破 ——論伽達默爾詮釋學的語言學轉向 | 構建中國闡釋學》,新浪網。
(2)所有作爲我們“理解”、“詮釋”之對象的人類意識(“意義”)或“無意識”也不是一種純粹給定的“實在”,而是由一定的語詞符號系統建構起來的。
加達默爾上述“能被理解的東西只是語言”之類的說法已經包含了作爲我們理解、詮釋對象的意義世界(“某一事件的含義或某一本文的意義”)都是一種語言的構成物這一思想。除此之外,在《論文字學》等著作中,德里達也明確地反對一種被他稱之爲“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理論觀點,這種觀點認爲我們的一切經驗、意識和語言(包括言語和文字兩種形式)都只不過是對一種被稱爲“邏各斯”的本源性實在的表達或再現,而在經驗、意識、言語和文字這四者當中,依據它們與“邏各斯”之間的關聯程度,相互之間也存在著一種逐級再現的關係。其中經驗是對“邏各斯”最直接的把握,意識是對經驗的再現,言語則是對意識的直接表達,文字則只不過是對言語的一種再現。
德里達對這種“邏各斯中心主義”觀點進行了堅決的批判。德里達借鑒了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關於“語詞符號具有任意性”的觀點,認爲被人們通常稱爲“能指”的語詞符號的意義其實並不是來源於它與其“所指”之間的固定聯繫,而是來自於與其所在的語言符號系統中所有其他語詞符號之間的差異。“能指”與其“所指”之間的關係不是一種再現關係,而是一種建構關係:不是“能指”再現著“所指”,相反,是“能指”建構了“所指”。並且,“能指”對“所指”的這種建構關係還具有一定的任意性。
不過,與索緒爾等人不同的是,德里達特別強調書寫“文字”及“文本”的地位和作用。德里達指出,文字不僅不是言語的再現,文字實際上還是言語和思維的前提。在有文字的時代,我們意欲通過理解過程去把握的一切(言語、經驗等)實際上都是由特定的文字而建構起來的,人們不通過文字便無法思維和言說,“文字既構造主體又干擾主體。”
加達默爾和德里達試圖確認經驗和意識的語言性,拉康則試圖確認人的“無意識”的語言性。他試圖表明:人的“無意識”其實也是由話語(或文本)建構起來的。
在《哲學與自然之鏡》一書中羅蒂甚至認爲作爲西方近現代哲學(尤其是認識論哲學)之討論對象的“心”及其運作規律(如感性經驗如何被綜合成爲理性的概念與命題等)也根本不是一種純粹的給定之物,而完全是由笛卡兒、洛克和康德等人的哲學話語建構起來的一種東西;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一種不同的哲學話語,在這種哲學話語中,完全沒有“心”及其相關的概念,因此,在信奉此一哲學話語的人們所生活的世界裏,就根本不會有我們通常所熟悉的“心靈”、“思想”、“精神”、“意識”、“觀念”“知覺”、“心理表像”之類的現象及規律,有的可能只是各種神經突觸之間的相互作用、腦電荷結構的不斷重新組編以及相關的規律等等。這些人將非常奇怪“爲什麽我們認爲我們有那些被叫做‘’感覺’和‘’心’的東西”。
(3)所有作爲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及批判)之對象的那些社會分類範疇及其相互關係(如權力關係、支配關係)也都是由一定的語詞符號系統(知識/話語)建構起來的。
在《瘋狂與文明》、《臨床醫學的誕生》、《詞與物》、《知識考古學》等早期著作中,福柯力圖表明無論是作爲精神病學對象的“精神病”或作爲現代臨床醫學對象的其他各種疾病,還是語言、自然物、財産關係等知識對象以及作爲各種現代人文科學之核心對象的主體性的“人”,都並非是一種現成地存在於那裏等待著我們不斷去增進瞭解的純粹自在的現象,而是在歷史過程當中由特定的“話語構型”(discursive formation)所建構起來的。對福柯而言,“話語不是關於對象的,更確切地說,倒是話語構成了對象。”
在《監禁與懲罰》等晚期著作中,福柯則進一步提出即使是像權力關係這樣一些最基本的社會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特定的知識/話語建構起來的:“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構建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係”;“把科學僅僅看成一系列程式,通過這些程式可以對命題進行證僞,指明謬誤,揭穿神話的真相,這樣是遠遠不夠的。科學同樣也施行權力,這種權力迫使你說某些話,如果你不想被人認爲持有謬見、甚至被人認作騙子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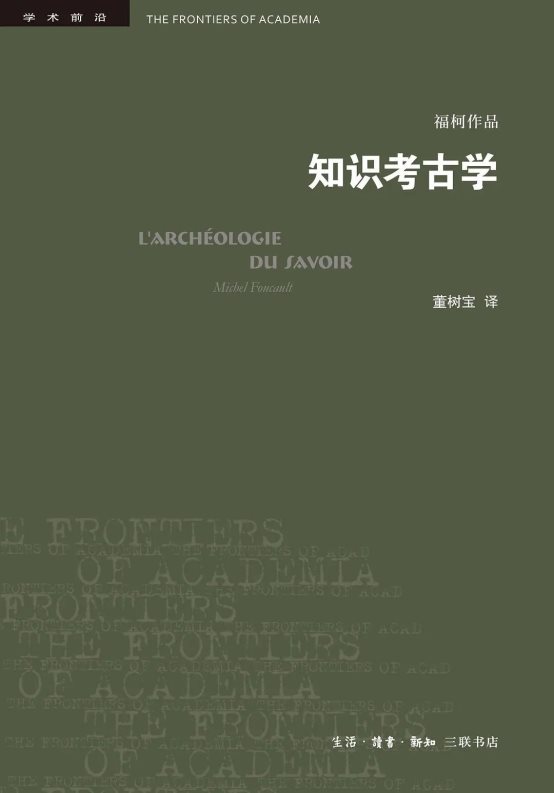
福柯《知識考古學》書影,圖片來源:豆瓣讀書。
2.反表現主義。
後現代主義者們認爲,既然不存在著什麽先於、外在於、獨立於語言符號的給定性實在,我們所能感覺和意識到的一切對象性存在都是由我們所使用的語言符號建構起來的,那麽我們對這些對象的一切認識或知識也就不可能是對既定“客觀實在”的一種純粹的表現、再現或呈現。“知識”就只是我們在特定語言/符號系統的約束和指引下所完成的一種話語建構,而不是什麽對“客觀存在”的表現或再現;我們能夠加以分析和討論的也不是客觀現實本身,而只是各種不同的“文本”而已;我們的認知目標也就不應是“正確”把握或再現既定“客觀現實”,而是去瞭解話語與相應“現實”之間的建構關係以及在各種具體的話語/文本後面約束和指引著這種話語建構的那些話語/符號系統。
(1)首先,我們對外部物質世界所做的各種描述和判斷以及由此構成的“理論”或“文本”不能被視爲是對既定“客觀現實”的表現或再現。
波普爾、庫恩、費也阿本德等後實證主義者們都指出過“觀察滲透著理論”這樣一種看法。一切經驗觀察和由此得來的相關理論知識都不可能是對純粹客觀世界的表現或再現,都不具有純粹的“客觀性”。其基本原因就在於一切經驗觀察及其觀察陳述都是由我們的語言/話語/理論建構起來的,其中不可避免地滲透著語言/話語/理論的成分。在不同語言/話語/理論指導下進行研究工作的人,對於所欲觀察的內容、所觀察到“現象”的感受、以及對觀察結果的陳述等都會有相當大的差異。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我們只會去且也只能夠去感覺、意識和言說我們的語言/話語/理論系統中已經包含的那些東西,我們不可能超出語言/話語/理論給我們設定的限制而達到所謂純粹的“客觀實在”。
此外,對於我們建構出來的某一科學理論是否“真實”、“準確”地再現了“現實”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其實也沒有能力做出確切的回答。由於歸納法的局限性、觀察命題本身的可錯性、理論判斷的正確性與其背景知識及預設條件的關聯性等原因,我們既無法簡單地通過某種“判決性的檢驗”來對判斷的“真實性”、“可靠性”最終加以“證實”,也無法簡單地通過某種“判決性的檢驗”來對判斷的“真實性”、“可靠性”最終加以“證僞”。因此,一項理論判斷是否正確地再現了某一“現實”之類的問題就是一個永遠無法得出終極答案的問題。將知識看作是對現實的再現,並因而將準確“再現”外部世界當作是認知活動的首要目標也就是一項毫無意義的事情。
(2)其次,我們通過各種途徑對他人行動意義所做出的“理解”和“詮釋”也不是對某種“本來意義”的表現或再現。與狄爾泰、韋伯、舒茨等人不同,加達默爾堅決反對把準確獲得行動者賦予行動或文本之上的主觀意義(本來意義)確定爲我們理解或詮釋的目標。加達默爾指出,由於我們對他人的理解總是依賴於(因而滲透著)我們自身的“前見”、“前理解”或“前 把握”,同時由於我們和他人的“視域”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可消除的差異”,使得我們對他人行動或文本意義的理解不可能成爲後者的再現。他人的主觀意圖是一種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達到的主體的精神活動,把他人的主觀意圖確定爲理解的目標也是種十足具有幻想色彩的論調。
(3)最後,我們對人及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的知識也不能被視爲對某種給定的客觀現實的表現。按照福柯的說法,這不僅是因爲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對象世界都是由相應的話語/知識建構出來的,而且這些話語/知識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一定的權力關係建構或“生産”出來的。
“在人文科學裏,所有門類的知識的發展都與權力的實施密不可分。……當社會變成科學研究的對象,人類行爲變成供人分析和解決的問題時,我相信這一切都與權力的機制有關——這種權力的機制分析對象(社會、人、及其他),把它作爲一個待解決的問題提出來。所以人文科學是伴隨著權力的機制一道産生的”; “認識主體、認識對象和認識模式應該被視爲權力—知識的這些基本連帶關係及其歷史變化的衆多效應”;“權力—知識,貫穿權力—知識和構成權力—知識的過程和鬥爭,決定了知識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領域”;因此福柯認爲,相信存在著一種客觀“真理”(如“性真理”)是一件令人“感到好笑”的事情。
反表現主義的思想在後結構主義大師德里達所說過的一句話那裏得到了最簡練的概括。這句話就是:“文本之外別無它物(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德里達認爲,閱讀“不能超越文本而把握到不同於文本的東西,把握到指稱對象,或把握到文本之外的所指(這一文本的內容可能出現或已經出現在語言之外,也就是說,出現在一般文字之外)”。這不僅是因爲只有通過各種文本我們才能夠接近各種所謂“現實”,而更主要的是因爲作者意欲通過“文本”去表述的一切實際上都是由文本自身建構起來的,因此這些文本就不可能是其之外某種純客觀事物的再現:在各種“文本”作者的現實生活中,在被定義爲他們的著作的東西之外和背後,“除了文字之外別無它物;除了替補、除了替代的意義之外別無它物。……絕對的呈現、自然、‘真正的母親’這類的語詞所表示的對象早已被遺忘,它們從來就不存在。”
.png)
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國哲學家,西方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圖片來源:Bing。
3.多元主義。
後現代主義者們認爲認識或理解的結果具有不確定性或多樣性,而我們又不可能獲得可用來幫助我們判斷認知或理解是否“真實”的唯一的客觀標準,因而也就不存在什麽對研究對象或文本的“正確”或“"錯誤”認識與理解;我們就同一對象或文本所得的各種認識與理解只不過是各種不同的“故事”或“語言遊戲”而已;不能把其中的一種看成是“真的”而將其他的加以排斥,而應該允許多種“故事”同時並存。如果一定要有一種評價標準的話,那也只能是“創新性”或與族群中現有認知的“協同性”等。
後實證主義者們首先在自然科學哲學領域中撐起了反對一元真理論、主張多元主義的旗幟。他們指出,由於缺乏對科學理論的真實可靠性最終加以判決的客觀標準,以及不同理論“範式”之間的不可通約性(不完全可比性),我們不可能在不同的理論範式之間做出唯一性的選擇,這就使得每一種理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此外,由於反駁一個既存理論的“事實”證據往往只有借助於一個與其不相容的其他理論來揭示,因此允許不同的理論同時存在、相互競爭也有十分的必要。
在此基礎上,費也阿本德明確提出了“認識論的無政府主義”這樣一個口號,主張認識論方面的多元主義。他認爲,無論是考察歷史插曲,還是抽象地分析思想和行動之間的關係,都表明了一點,即“只有一條原理,它在一切情況下和人類發展的一切階段上都可以加以維護。這條原理就是:怎麽都行。”按照這一原理,人們既可以堅持在目前得到“事實”充分確證的那些理論,也可以(甚至應該被鼓勵去)堅持與充分確鑿的“事實”相矛盾或與得到充分確證的理論相矛盾的那些理論(包括神話、宗教、巫術一類非科學理論)。在知識領域,應該鼓勵的行爲是讓不同的理論和模式相互之間進行富有成果的交流,藉此豐富我們對世界的認識,而不是簡單地選擇其中一個,同時將其他的理論或模式粗暴地排除在外。
加達默爾、德里達和巴爾特等人則肯定了人們之間相互“理解”、“詮釋”的多元性。加達默爾指出,由於“理解”總是我們自己的視域與本文視域二者融合的結果,而“我們自己的視域”在不同的時空境遇中又總是每每不同的,因此,對於處於不同時空境遇中的“我們”來說,同一件本文的意義就完全可以是不同的。這樣一來,“理解就不只是一種複製行爲,而始終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爲”;“如果我們一般有所理解,那麽我們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理解”因而就始終具有相對性和多元性。
德里達則從索緒爾的意義理論出發,提出由於語言或文本系統的非封閉性導致的符號之間差異關係的不穩定性、多變性和無限性,使得符號意義或所指的確定過程被無止境地拖延、推遲下去,成爲一個無限“延宕”的過程,從而使得對於任何一個符號,我們都永遠不可能獲得對其意義的最終理解。因此,“不存在所謂的語詞和本源的恆恒定意義,一切符號意義都是在一個巨大的符號網路中被暫時確定,而又不斷在區分和延擱中出現新的意義。新的意義進一步在延擱中區分,在區分中延擱。”巴爾特在其後期作品《S/Z》一書中則以巴爾扎克的小說文本《薩拉辛》爲例,具體地展示了對一個文本的意義進行多元解讀的可能性。
德里達以及福柯、德勒茲、利奧塔等後現代批判理論家們還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來倡導理論的多元主義。他們認爲,知識/話語總是隱含著一定的權力,“一元真理論”不可避免地隱含著“一元權力論”(唯一“真理”的掌握者同時也就必然是“權力”的唯一合法掌握者)。就像塞德曼指出的那樣,“隱藏在真理意志中的是一種權力意志。宣稱存在著普遍和客觀的理由可以作爲社會話語的正當理由,宣稱一種話語講述的是真理的語言,就是使那種話語、它的承載者及其社會議題特權化。”要消解“一元權力論”,就必須首先破除“一元真理論”,允許和鼓勵知識/話語/理論模式的多元並存。因此,取消一元真理論是一種“積極的解放運動”,“它使得極權主義成爲不可能”,“它肯定了‘聽、問、講’等更加平和的實踐。”
4.反本質主義。
後現代主義者否認本質和現象的嚴格區分,否認事物擁有某種固定不變的“本質”或者諸多“現象”後面存在著某種固定不變的“共性”,認爲事物“現象”之間存在著的只是各種“家族相似”之處;反對將把握事物的這種固定不變的內在“本質”當作認識活動的目的,而主張從各種不同的視角出發來探尋對象的性質及其對象之間的相互關係,揭示不同視角之間的差異,從各種視角的特殊性或與其他視角的差異當中來理解對象。
應該說,反本質主義這種理論立場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內在地包含在上述反實在論、反表現主義、多元主義的理論觀點之內。既然不存在著獨立於我們的語言符號之外的純粹客觀的對象世界,既然一切對象世界都是由我們的語言符號建構出來的,既然作爲“能指”的語詞符號與其“所指”、作爲“所指”的概念與其“指涉”之間的關聯都具有任意性,那麽,一個語詞符號的“所指(概念)”、或者一個“所指(概念)”的“指涉”對象在內涵和外延上怎麽可能具有固定不變的性質呢?
正是在這樣一種立論的基礎上,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才得以發揮其威力。正如羅蒂所說的那樣,德里達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反對必然導致對“本質主義”的反對,“德里達的反邏各斯中心主義不過是……反本質主義的一個特例”。
德里達致力於“解構”西方思想中源遠流長的各種二元對立(在場/缺場、言語/文字、自然/文化、中心/邊緣、哲學/文學等),這些二元對立無一不是以本質主義立場(認爲每一對立範疇的雙方都有自己某種固定不變的本質,而且,由於這些本質使得它們之間的等級關係也具有不變的性質)作爲自己的邏輯前提。通過對這些二元對立的“解構”,德里達說明了所有這些對立範疇之間的界限其實都是可變的(例如,“在場”總是包含了“缺場”,文明時代的“自然”總是包含了“文化”的成分,“中心”同時也是“非中心[邊緣]”,哲學也不過是一種文學等),所有這些二元對立其實都只是人們的一種形而上學的語言建構。“解構主義”就是要通過對某種概念或文本的理解當中所含內在矛盾的揭示來展現此一理解的不確定性、非本質性。
福柯、拉康等人對於作爲主體的“人”的“解構”也是後現代主義者反本質主義立場的一個典型實例。將“理性”、“主觀能動性”或“主體性”等屬性看作是人的固有“本質”(人與其他動物相區別的基本特徵),是現代主義思潮的核心觀念之一。在《詞與物》等著作中,福柯則明確指出對“人”的“本質”的這樣一種理解,與對“人”的“本質”的其他各種理解一樣,也並非是對人的真實“本質”的一種再現,而只是現代“知識型”的一種建構。在現代“知識型”形成之前沒有這種作爲主體的“人”,在現代“知識型”之後“知識型”的進一步演變也將導致這種作爲主體的“人”的再次消失。
因此,“(這種作爲主體的)人只是一個近來的發明,一個尚未具有200年的人物,一個人類知識中的簡單褶痕”,“一旦人類知識發現一種新的形式,(這種作爲主體的)人就會消失”。同樣,拉康也否認“主體性”是人與生俱來的固定本質,指出所謂人的“主體性”只是話語(符號界)建構的結果而已。
後現代女權主義者則否認了對性別的本質主義理解。在現代主義者那裏,“男人”和“女人”往往被理解爲是兩種有著自身固定不變之內在本質的客觀存在,後現代女權主義者堅決反對這種本質主義的性別觀,認爲它們其實也都只是話語建構的産物。在不同的話語之下,人們將會建構出不同的性別“現實”。
例如,在話語A之下,“男人”和“女人”可能被視爲兩種無論在體格還是在人格方面都有著根本差異的性別類型;在話語B之下,“男人”和“女人”則可能被視爲除了在體貌方面有著差異之外其他方面均無根本差異的人種類型;而在話語C之下,則可能根本不存在抽象的“男人”和“女人”的分類,有的可能是無窮多樣的男性和女性分類(如美國南部信仰基督教的中産階級的黑人女性,或美國北部信仰猶太教的工人階級白人女性等),性別存在將隨著“種族地位、民族地位、宗教地位、或階級地位以及與性取向、年齡或地理/地域特徵有關的那些因素的變化而變化”。
羅蒂也從實用主義的立場來倡導反本質主義,主張事物的“本質”並非某種內在於事物本身的東西,而只是我們從實用的立場出發所進行的一種建構。他明確地說:“對我們實用主義者來說,不存在任何……像X的內在本性、本質這樣的東西……,離開了其與人類需要或意識或語言的關係,就不存在像一個與X的實際存在方式相符的描述這樣的東西。”而實用主義本身也不過就是“運用於像‘真理’、‘知識’、‘語言’和‘道德’這樣一些觀念和類似的哲學思考對象的反本質主義。”
.png)
羅蒂(Richard Rorty,1931—2007),美國新實用主義哲學家代表之一。圖片來源:Bing。
5.反基礎主義。
後現代主義者否認各種知識之間存在著等級和從屬關係,否認可以依照知識之間的這種等級和從屬關係,通過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等途徑將知識整合成一種總體性的話語體系或“宏大敘事”,認爲它們之間真正存在著的乃是一種交互指涉、交互纏繞的“互文性”(Intertextual)關係或網路關係;不可能簡單地從一種知識中推論出另一種知識來,每一種知識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反對各種“總體性理論”或“宏大敘事”的有效性,轉而鼓勵各種“局部性理論”或“小敘事”。
在《千高原》一書中,德勒茲和瓜塔里提出了“塊莖(Rhizome)結構”模型來取代現代主義思想家們的“根-一樹(root-tree)結構”模型,用以描述知識之間的關係。
德勒茲和瓜塔里認爲“塊莖”結構具有著與“根-樹”結構完全不同的特點:
第一,連結的異質性:與根一樹結構中的每一點作爲多層次的“主幹-分支”體系中的一個環節都只能與體系中特定方向的樹幹或分支連接不同,“塊莖中的任何一點都能夠並且必須與任何其他一點相連接”;
第二,複雜多樣性:與根一樹結構中表面上看繁華多樣的枝葉最終都可以也必須歸結於樹根這個“一”不同,在塊莖結構中所有的點都“不再與一有任何關係”,不必再歸結於或附屬於某一個“一”;“就它們填充和佔據了它們所有的維度而言,所有的多樣性都是平展的:我們因此可以談論一種多樣性的連貫平面,即使這個平面的維度隨著在它上面創造的連接的數量的增加而增加。”
第三,“非意指斷裂”性:與根-一樹結構中那種將不同結構分離開來或單一結構切割開來的斷裂不同,塊莖在特定地點上雖然也可能被破裂和粉碎,“但它卻可以在某條舊的路線或新的路線上重新開始”,這些路線總是相互聯繫、相互交錯著的,從而使得塊莖結構中事物的演化將不再遵循樹狀的模式,“不同路線之間的橫向交流攪亂了譜系樹”;
第四,無中心性:“樹狀系統是一種具有意指和主觀化的中心、像有組織的記憶一樣進行中央自動控制的等級系統”;與此相反,塊莖結構則是“一種無中心、無等級、無意指的系統,沒有將軍,沒有組織化的記憶或中央自動控制,僅僅只被狀態的運行所限定”。
德勒茲和瓜塔里明確地提出“思想不是樹狀的”,並感歎“樹喻”何以“一直統治著西方的現實和所有的西方思想”,“所有樹狀文化,從生物學到語言學,都是在它們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們疾呼“我們已經厭倦了樹;我們應該停止相信什麽樹和根了。它們已經讓我們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他們提出的口號是:“製造塊莖,不要根,決不要植根!”

吉爾·德勒茲、菲力克斯·加塔利《千高原》書影。圖片來源:豆瓣讀書。
在《兩個講座》中,福柯也從另一角度對各種“通用的、總體化的理論”進行了批評,極力倡導各種“特殊的、局部的、區域性的知識”。從他的權力的微觀物理學觀點出岀發,福柯提出我們應該將社會研究的焦點放在微觀的、局部的日常生活領域,而既有的那些“通用的、總體化的理論”對於這種“權力的微觀物理學”的研究不僅不能提供一種有效的指引,而且還構成了一種障礙:除了不能恰當地揭示彌散在日常生活各個不同領域中的那些局部性的、其起源和運作機制各個特殊的權力關係與權力技術之外,這些既定的總體化理論本身也構成了一種支配性的權力,“這種理論以真正的知識的名義和獨斷的態度對之進行篩選、劃分等級和發號施令”,凡是與這些總體化的理論不一致的理論與知識生産都將受到壓制,從而使一大批“局部的、特定的、缺乏普遍意義的”知識成爲被忽略、被埋葬的知識,使得權力的微觀運作機制永遠得不到恰當的揭示。
福柯指出,要想使權力的微觀運作機制真正得以揭示,就必須“廢除總體性話語及其等級體系在理論上的特權地位”,建構一些以“冷僻知識和局部記憶的結合”爲特徵的“特殊的、局部的、區域性的知識”。福柯把這樣一種知識稱爲“譜系學”知識。這種譜系學知識的任務不是要提出一整套與既有理論不同的理論或思想體系,而是要“對抗整體統一的理論”、“關注局部的、非連續性的、被取消資格的、非法的知識”,以獲得對於權力機制的另類認知,爲人們理解和批判現實提供一些“有用的零件和工具”。福柯認爲,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走出壓制、鬥爭、新的壓制這樣的惡性循環,爲人類反抗支配的鬥爭開闢新的可能性。
對基礎主義和宏大敘事的否定在利奧塔德的《後現代狀況》一書中得到了最引人注目的宣揚。在這本書中,“精神辯證法、意義詮釋學、理性主體或勞動主體的解放、財富的增長等”各種總體性“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衰落和崩潰不僅被認爲是一種“應該”,而且被確認爲是一種事實狀態,即“後現代狀態”。利奧塔德指出,在現代狀態下,各種具體的科學知識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一直是以這樣一些“宏大敘事”作爲自己的理論基礎或合法性依據的。
例如,思辯哲學就是通過把分散的科學知識視爲“精神”運動的不同環節而將它們連接在一個統一的總體性敘事之中這種方式來爲科學知識提供一個理論基礎或合法性依據;各種“自由”、“解放”理論則通過把科學知識視爲實現某種價值理想的手段而將它們納入一個統一的總體性敘事之中來爲科學知識確立一個理論基礎或合法性依據。

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當代法國著名哲學家,後現代思潮理論家,解構主義哲學的傑出代表。圖片來源:Bing。
然而,隨著科學自身的進步以及“事實一價值”二元分立觀念的形成,這些總體性的“宏大敘事”都開始遭到了人們的懷疑:學科邊界的不斷變動和重疊使得“知識的思辯等級制”(這是思辯哲學的理論前提)不斷被摧毀;對“事實陳述”和“規範陳述”之間差異的認識也使人意識到科學不過是諸種語言遊戲中的一種而已,它“有自己的遊戲規則,但完全沒有管理實踐遊戲的使命”。這樣一來,各種“宏大敘事”的基礎或合法性功能便被消解了。
面對宏大敘事的消解,社會管理階層試圖以效率原則、哈貝馬斯則試圖以通過對話取得的共識作爲科學知識的合法性依據。利奧塔德認爲,前者“將帶來某種或軟或硬的恐怖”,後者則是一種從未達到過而將來恐怕也難以達到的遠景(即使有也只能是局部的、臨時性的),因而都不是一種可接受的立場。利奧塔德呼籲,我們應該將追求各種“小敘事”、追求差異作爲知識合法性的新依據。因爲只有這樣一種追求才會“産生思想,即産生新的陳述。”
後現代主義的上述觀點從根本上顛覆了現代主義社會學所賴以成立的各項理論預設,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與傳統十分不同的社會學思維模式或知識論立場。這種新的思維模式或知識論立場對社會學研究顯然應該有著非常重要的啓迪作用。
文字编辑: 曹佳韬、代欣怡、吕灵
推送编辑:李家乐、毛美琦
审核:孙飞宇、许方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