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飛宇:論舒茨的“主體間性”理論(下)
孫飛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舒茨所代表的現象學社會學認爲,韋伯止步於個體的意義分析,而這只是一個高度複雜的世界之起點。始於個體意義的現象學社會學必得面對他者的出現,主體間性在這裏成爲必需的問題,而主體間性的可能性,在舒茨的思想中始終是缺席的,現象學所特有的意識分析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本文從海德格爾的生存哲學入手,將問題引入更爲本源的生存狀態。這條路徑進一步的意義在於,對於現代社會的主體,共同體,以及對於現代社會自身的思考。
在《笛卡爾的沉思》中,胡塞爾區分了三種自我:(1)“同一我”(identical I),即生活在意識流中的,不斷構成的自我;(2)“個體我”(personal I),約略相當於舒茨所説的生平情境中的自我;(3)自我(ego)完全意義上的自我,包括在意識流中所有被構成的客體,胡塞爾借用萊布尼茨的説法,也稱之爲“單子”。
.png)
德国著名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代表作《笛卡尔的沉思》图书封面。图源:豆瓣。
如此,胡塞爾開始了自己在超驗領域解決此問题的嘗試,首先進行的是進一步的還原(或者是第二次懸置)。即排除直接或間接指向他人的主體性的意向性活動,只要與他人有關,就要加以懸置,包括文化客體,與他人共在的世界以及我自己的指向他人的領域。
“我們不必考慮一切可與陌生主體直接或間接相關聯的意向性的構造作用,而是首先爲那種現實的和潛在的意向性的總體關聯劃定界限。”
如此懸置以後,就只剩下我自己的自我的構成性東西了,這是一個“恰當領域”(proper sphere)。而這個超驗領域仍然是我的實在存在的決定部分,所以胡塞爾稱之爲原初世界(primordial world)或原初超驗(primordial transcendence)。在這様的還原中,陌生者的現實的和可能的經驗並没有受到影響,也就是説,“在我的心靈的存在中,就包括了爲我存在著的世界的全部構造,也包括了把這個世界劃分爲兩個構造系統,一個構造本己之物,另一個則構造陌生者。”這也就是舒茨所謂的,自我的超驗領域被分成了兩個部分:一爲自我的恰當領域;一爲並非自我的領域。
但是這兩個領域如何區分?舒茨認爲在這裏至少有五個困難。(1)如何區分什麽對我來説不是合適的?(2)他人具體指的是什麽?(3)胡塞爾認爲每一個對可能的客體我們(Us)與主體我們(We)的指涉都被第二次懸置所排除,但是這怎麽與在自我的恰當領域中,所保留的對他人的實際與可能的經驗相協調?(4)如何區分我們的自我意識與我們對他人的主體的意識?(5)第二次的懸置,由誰來執行呢?
胡塞爾的第二步是在原初領域内的他我構成。在這裏,胡塞爾將活生生的身體(living body)與感覺域(fields of sensation)分開。在自我的恰當領域,另外一個人對我的顯現,首先是軀體,然後成爲活生生的身體,進而成爲他人的而非我的身體。這個時候,我與他人是處於同一“原初世界”中,在這個原初世界中共在此(Mit-da),使得這種共在此成爲可能的,胡塞爾稱之爲“共現”(Appräsentation)。這様的過程,是通過類比的方式進行的:“只有在我的原真領域内把在那裏的那個軀體與我的軀體結合起來的類似性,才能夠爲把前一個身體當作另一個身體的類比化把握動機的基礎。”
所謂類比的方式就是如前所述的結對聯想,它們是被動綜合的原初形式。舒茨認爲,胡塞爾的顯現理論(theory of appresentation),尤其是它對於建立能指(sign)與所指(signatum)、符號與被符號化的聯接的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在這裏作爲結對聯想的基礎,就不同了。簡單説來,就是,我的身體與他人的軀體怎麽能夠類似呢?他人的軀體是被我看到的,而我自己的身體則是被我經由内在知覺與運動感覺所感覺到的,總是原初被給予的組織,這兩個路徑截然不同,不能夠得到類似的結論。
這只是一個基本的批評,並且在舍勒、薩特、梅洛龐蒂以及盧克曼諸人那裏都可以見得到。舒茨本人對於這一思路的批評如下:在什麽時間以及何種情況下,我可以合適地(一致地)將他人的軀體經驗成身體?假如可以確定這様與他人有關的合適的精神事件,那我對它的感覺是什麽呢?進而,什麽是合適什麽是不合適的?假如要在前構成的層次上來談論這個問題,那就只有兩種可能:或者是第二次懸置還没有執行徹底,而我們試圖達到“恰當的”純粹領域的努力根本就是錯誤;或者是我在此領域内將他人的軀體從一開始就經驗成他人的身體,而這個思考方向,顯然是錯誤的,因爲我們所預設的,正是進入這個領域所懸置掉的東西。
他人在我的原初領域的顯現,既包括其原初領域也包括完全意義上的實體顯現,是要經過一個修正的。我將他人顯現爲與我類似的,共存在“那裏”的自我,以這種方式,另外一個單子在我的單子之中構成性的顯現。這兩者就形成了一個單一的,同時顯現(presenting)與共現(appresenting)的感覺。所以胡塞爾認爲,自然客體對於我的“這裏”與他人的“那裏”是相同的,儘管實際的感覺可能會不同。
如此,客體的自然同様會構成一個經驗的現象。經由感覺他人,我的原初構成領域就會産生第二個共現的層級,它處於我的原初構成自然的同一性的综合統整體之中。這一综合確定了原初給予與共現给予的相同自然(nature),也就構成了我與他人的共存,並且還構成了共同的時間形式,“‘我—你的综合’……從某種意義上説,這又是一種時間化,即自我極的同時性的時間化,或者每一個自我都知道自己處於其中的那個個人的(純粹自我的)地平線的構成之時間化,這是一種作爲一切自我—主觀的‘空間’的普遍的社會型”。
舒茨首先提出,在這様的過程中,他人的原初世界,换句話説,他人自我的“恰當”領域,是如何共現的呢?在這一過程中被給予我的他人的心理物理我,不足以提供這種充分性,因爲那様一個“恰當”的領域,包括他人所有實際的與可能的主體過程,那我如何來達到這種實際的與可能的領域呢?通過我的實際與可能的領域嗎?但是我的在這裏與你的在那裏本身就包含著必要的“我能從這裏,但是你不能從哪裏”的預設。而這様的困難是不能夠通過我們彼此位置的交换來完成的,因爲這事實上意味著任何人都具備能夠的前提,而這又意味著主體間性的預存。
另外一個不夠自明性的事實是,我們如何能夠從他人的心理物理我而得出完整的他人單子?而第二層級在我的原初領域的出現,能夠構成客觀自然的充分條件嗎?胡塞爾認爲,自然客體同一性的综合统整體作爲原初發生物被給予我並且經由經驗他人而增加了共現層級。但是客體自然對他人的構成過程不也與跟我的過程一様嗎?如此豈非又預設了一個我群關係,預設了一個開放性的共同體?而胡塞爾也確實在《觀念II》中,將主體間性的可能性建基在溝通的可能性上。

奥地利裔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现象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1899.4.13-1959.5.20)。圖片來源:The Schutz Circle。
胡塞爾在《觀念Ⅱ》中,區分了自然化的(naturalistic)態度與個體化的(personalistic)態度。在自然化的態度下,自然首先是作爲物質事物的實體,然後才作爲精神生活的實在存在的。他人對我的顯現過程,如前所述,是從物質性的身體到精神,精神生活“隷屬於”可見的軀體。而先前所述的同情過程,則導致了世界之主體間性客體的出現,以及物質性的實體與作爲物理心理整合體的人的構成。而自然態度週圍的世界,則僅限於個體所“知”的部分,主體不但要面對物理事物,而且要面對與物理事物相關的他人。個體與他人所構成的這種共同的週圍世界,就是胡塞爾所謂的溝通性的週圍世界,他人並非客體,而是我所面對的主體。但是在這裏没有清楚的説明,在我對他人的同情過程中,他人的精神生活是如何建構起來的?而這裏一個明顯的循環論證是,作爲主體間性基礎的溝通性的世界,事先所需要的,就是主體間性的可能性。。
.png)
胡塞尔著作《现象学的观念》。图源:bing。
胡塞爾的人的概念,從一開始就是社會中的人,我不但處於他人之中,而且還與他人相互具有意向關係。胡塞爾指出這裏存在著一個意義轉换的過程,從“我”到“他我”進而是“我們全體”。這是作爲懸置的結果出現的,但是執行懸置的,卻只能是作爲哲學家的,個體的“我”。如此説來,每一個人,只有在進行了超驗主體性的操作以後,才能夠作爲一個持有超驗主體的人被理解。但是超驗性的自我卻並非自然狀態之人的心理的實在部分。這裏開始接觸超驗主體間性的核心問题。
胡塞爾指出,個體主體間性的存在,是作爲先驗的群體主體間性的結果出現的。但是他卻並没有指明我們如何能夠達到一個先驗的我群主體間性。對我而言,從他人的軀體到他人的超驗主體性的出現,儘管胡塞爾有一套完整的現象學分析,那也不會産生超驗的共同體或者説超驗的“我們”,每一個超驗自我的構成,都“只是爲了他自己而非爲了所有其他的超驗自我。”
這様胡塞爾的主體間性其實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一個是客體世界,包括他人的構成,另一個是溝通。解決這一問题的辦法是,承認有一個對我們而言是共同存在的共同體,而不是你我的共同體的“重合”。但是這様一來,由於超驗主體間性的可能性條件即自然世界中的事物,即我群關係,就陷入了循環論證。
通過如上分析,舒茨認爲,主體間性的可能性,在超驗領域是不能夠得到解決的,它是一個生活世界的概念。人的存在,從一開始就是以主體間性與我群關係爲基礎的。所以只有構成現象學分析之下的生活世界本體論才能夠解决主體間性的問題,進而能夠爲社會科學奠定基礎。
正如斯蒂文·瓦庫斯(Steven Vaitkus)所言,舒茨後期思想的一個顯著特徵,即是將主體間性作爲一個社會群體(social group)的問题來考察,這裏的社會群體,所強調的就是社會行動者身處其中的日常生活。舒茨通過對胡塞爾的批判指出,社會群體這様一個背景對於個體來説是預存的,而個體意識則在原初就是社會性的,“社會並非由意識獲得或者強加給意識的次級層次”。在以現象學入社會學,應用於社會學的意義分析與生活世界的建構過程中,事實上,舒茨在這個時候已經接觸到了對於胡塞爾現象學的批評,並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其中與主體間性有關係的是第二個問题:
我們每一個人都屬於這個生活世界,如果自然態度的生活世界是作爲超驗現象學的意義基礎的話,那麽,在這一世界構造的活動中,我的超驗主體性,從一開始就與他人的超驗主體性相關聯。而這様的生活世界是將所有向度的關係都包含容納統一於其中的。但是這能夠解釋他人的問題嗎?能夠解釋基於真實世界的人的互動嗎?
舒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從胡塞爾的思想入手的,表明在思想轉變時期,他對主體間性問题的態度,雖然仍没有脱離胡塞爾的體系,但已經開始與胡塞爾的回答不同。他認爲這個生活世界從一開始就不是我自己的生活世界,而是與他人共在的一個世界,而他人是與我具有相同種類身體與意識的他人。在現象學的懸置完成以後,我所經驗到的世界就是一個主體間性的世界,“這意味著它適用於每一個人”。所有的文化客體(人的産品),都向回指向某個最初的主體或者構成性的意向。這正是胡塞爾在主體間性問题上的起始點,胡塞爾在先驗還原了的純粹意識生活領域内,所經驗到的世界就是一個主體間性的世界,“是爲每個人在此存在著的世界,是每個人都能理解其客觀物件(Objekten)的世界。”
在這裏還没有發生體系上的轉變,探索的路徑依然是超驗現象學式的。首先是第一次的懸置,或者説存而不論,即將所有與他人主體性間接或直接相關的構成活動懸置掉,還原到我自己的超驗領域,即原始領域(Primordial sphere)。這是一個我自己的世界,而非客觀的世界。還原過程中我能夠得到的一個特殊現象是我的身體;作爲身心整合的身體,我能夠加以控制,並通過它感知外在世界。以類似的方式還原他人,會得到一個類似的實體。這様,在還原的領域内我們可以得到他人的身體的概念。而根據前面所説的相應感知與結對聯想概念,在還原的領域裏,他人必定以身心統一體的面貌出現,即舒茨所説的一個“次級自我”(second ego),或者説,一個在那裏(there)的他我。
這様,我(me),原始身心整合的我(I),以及預顯經驗的他人,作爲天然的共同體,形成了所有其他更高層次的主體間性的基礎,不但屬於我的原初領域,也屬於他人的原初領域。我與他人的觀點不同,是由於他人的“那裏”與“這裏”的不同,易地而處,則會有相同的觀點,當然這裏的“易地”,並非簡單地指地點方位的變化,在胡塞爾那裏,涉及到了對他人統覺中的構造功能。
因爲他人的身體通過我的预顯而呈現,根據相應感知與結對聯想,我也被他人的經驗所感知,以此類推,“所有主體共同獲得的事物即開放的單子共同體,胡塞爾稱之爲超驗的主體間性”。當然這種超驗的主體性首先是純粹的出於我的主體的,它純粹由我的意象性起原而構成,但是以此方式,每個人都形成自己超驗的主體間性。在這種超驗主體間性的構成中,同時也就形成了一個统一與統整的客觀世界。但這只是舒茨自己對這一問题回答的起始點,是以胡塞爾的思想來對這一問题的回應。舒茨已經對這様的一種思考路徑提出了批評。他自己對於這一問题的回答,已經從超驗現象學領域轉到了日常生活領域,儘管後者的分析,仍然是現象學的,即舒茨所説的構成現象學(constitutive phenomenology)。
我們已經開始接觸到舒茨思想後期的生活世界概念。與胡塞爾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不同,舒茨所強調的生活世界是一種文化世界:“因此必須切記,生活世界對我而言是既存的,任一自然態度的人都將生活世界視爲其文化世界,即,是有意義的世界。”這様的生活世界主要由個體的經驗意識構成,具備複雜的構成結構,具有一個絕對的“零點”(null point),同時以複雜的詮釋结構與他人接觸。這様的生活世界是統一的,並且從一開始就賦予社會行動者。以上所有這些在原則上都可以由現象學的構成分析來解決,“由自然的本我(apodictic ego)開始,最終結束於完全具體世界的超驗意義,而後者就是我們綿延不絕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説,舒茨的生活世界從一開始就是有意義的,而與此並存的特徵是與他人的可接觸性,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舒茨前期思想與後期思想之間的關聯。舒茨一直強調主體間性對於日常生活中的行動者來説,是先驗的,在後來的實用主義階段(假如我們可以這麽説的話),儘管舒茨放棄了超驗現象學的基礎,但是仍然沿用這一解決方案,即主體間性的可能性是從一開始就賦予日常生活中的行動者的。
“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文化上的主體間性的世界。之所以是主體間性的,是因爲我們居住其中,如同我們居住於他人之中,受制於他人,經由共同的影響與工作而瞭解他人,同時成爲他人瞭解的物件。它是一個文化的世界,因爲這個世界從一開始就我們來説,就是一個意義的宇宙,比如,是一個我們必须加以證釋的意義結構,以及我們必須通過生活世界内的行動方能設定意義相互關係的結構;它是一個文化的世界,因爲我們永遠會意識到它的歷史性,是我們在傳統與習慣中所面對的世界,且因爲這個世界指涉自己的活動或他人的活動,所以是可以被檢驗的沉澱物。我生於此生活世界且以自然的態度居住於其中,是實際的‘此時此地’的歷史情境内的世界中心;我是‘構成世界的零點’,换言之,這個世界首先通過我並對我具有重要性與意義。”
這様,生活世界就是一個具備多種關聯性領域,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密度與完整性,並可以開放的可解釋的範畴。各領域對行動者的熟悉性與陌生性各不相同,而整體的生活世界也具備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海德格爾對於舒茨的影響,儘管並没有明確指出,但是可接近性與相應感知/結對聯想同時存在的後果就是海德格爾所説的“在週圍世界中照面的存在者”的特性:
“操勞所及的工件不僅在工場的家庭世界中上手,而且也在公衆世界中上手。週圍世界的自然隨著這個公衆世界被揭示出來,成爲所有人都可以通達的。”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9.26.—1976.5.26)。图源:wikipedia。
也就是説,這様的結果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動者通常假定,對我有意義的每一件事物,對於他人來説都同様是有意義的。同様的,他人的生活世界的種種特徵也是我可以瞭解到的。而經由同様的意義假定,我與他人的生活世界彼此是交叉的,就是説,我自己的意義生活的某些片斷是屬於他人的生活世界,反之亦然。
這在自然態度的行動者,是一個多層面的取向。我預期他人能夠理解我的活動,那我就已經先有了活動的意義,而這個時候我的模型就已經受到了所預想的他人模型的影響;同時,當他人影響我時,我也能夠理解他人的行動以及結果。由於這些都是與他人相關聯的,如此,這些建立意義與詮釋意義的相互活動就構成了舒茨所謂的主體間性的社會世界,所有的社會現象與文化現象皆以此爲基礎。而這様的過程在日常生活中是不言自明的。
上面的分析構成了舒茨後期在主體間性問題上的核心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在處理主體間性的問題上,舒茨的基本立論開始發生變化,將主體間性的基礎放置到了日常生活之中。他將日常生活中交互的意義脈絡視爲主體間性的可能性所在,這様的處理方法,已經與胡塞爾的超驗現象學有了截然不同的特徵。胡塞爾同様假定在自然態度中,存在著一個客觀的時空現實,“按照這個一般設定,這個世界永遠是事實存在的世界”。但是胡塞爾隨即就將自然態度加以懸置,不予考慮:“我們現在不是要停留於這種態度上,而是建議徹底的改變它。”也就是説,將自然態度存而不論:“我們使屬於自然態度本質的總設定失去作用……”,然後開始解決他我的問題。舒茨則不同,舒茨將自己的分析鎖定在被胡塞爾所懸置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態度上,將他所認爲的主體間性可能性放置在日常生活的意義脈絡之中,而不再是超驗的意識分析。儘管他所用的方法仍然是意識分析,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舒茨的可能性已經脱離了胡塞爾的自我意識領域。所以儘管這様的分析仍然是從胡塞爾的現象學出發,但是結論的立足點卻並不一様。
但是舒茨在以日常生活中意義的交互脈絡來面對主體間性的問題時,所回答的問题仍然是主體間性的發生,而非主體間性的可能性。因爲舒茨並没有進一步回答這様的問題:日常生活中的行動者,爲什麽從一開始就能夠將與他人的主體間性的可能性視爲理所當然?儘管舒茨認爲自己回答了日常生活中主體間性的可能性,但那只是一個分析的起點,只是描述了發生的情形,而没有解釋主體間性的可能性來源。舒茨自己無意中將這兩種情形進行了置換。
從舒茨後來在這一問題上的討論也可以發現這一置換。舒茨後期對於主體間性的可能性的分析處於生活世界的體系中。在日常生活中,同伴的意義行爲對我來説是既存的,我通過我的庫存知識對同伴的表達行爲,諸如軀體動作等等加以詮釋;而我的表達性行爲也爲他所證釋,“日常的生活世界因此在根本上是主體間性的”。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態度下的行動者理所當然地認爲,他人存在於我的世界中。不但存在著身體意義上的他人,而且他們也具備與我一様意識。這様,生活世界從一開始,就不是我自己的生活世界,而是一個主體間性的生活世界,基本特點就是共享。
同様的,我所接觸到的外在世界的客體,以及自然,由於已經被前輩們所經驗過,理解過與命名過,所以處在一個通用的(common)詮釋體系内,所以對於“我和我的同伴來説,在根本上都是一様的”。非但如此,對於同時代人來説,也是如此。他人類型化的行動以及産品,包括語言與符號,也是與一定的意義相關聯的。甚至,“即使是工具也不僅是作爲外在世界中的事物被經驗到,而是在計劃的興趣與背景之下主觀指涉圖式”。對於一個日常生活中自然態度的行動者來説,從一開始,這個世界就是一個主體間性的世界。
與前期思想相比,舒茨在後期對於社會科學的思考更加系統化。舒茨對於主體間性的考察,是放置在對社會科學思考的體系之中的。我們在前面提到過對於現象學的四個問题,其中第四個涉及到的是現象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問題的核心在於,將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加以懸置的現象學,如何宣稱自己能夠爲前者提供方法論基礎?這個問题所涉及到的另一個問题是,什麽是社會科學?
韋伯已經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在這個解答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作一區分,首先是在研究客體上的不同,社會科學的研究關涉到的是個體的意義,進而可以追溯到個體的主體性。所以相對於日常生活中的行動者對於世界的建構來説,社會科學是屬於二級建構,在研究方法上也與自然科學截然不同。社會學中的基本問题:社會世界對於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意義是什麽?這就意味著這様幾個前提性的問题:這個社會世界對被觀察者意味著什麽?被觀察者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表達什麽?要回答這様的問題,就要首先面對日常生活中的行動者所視爲理所當然的行動與意義,賦予意義的過程,以及人類相互理解的主體間性。而行動者行動的意義,在舒茨那裏,主要指的就是行動的兩種動機:原因動機與目的動機。“所有社會關係的原型就是主體間的連接舆動機。”
.png)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4.21—1920.6.14)。图源:wikipedia。
在這裏我們要注意區分社會科學的觀察者與日常生活中的行動者之間的不同。這様的區别顯然是從社會科學引入的視角來作出的,所以主要集中於日常思維中思想客體的建構與社會科學中思想客體的建構。
日常生活中,個體關於世界的常識性知識是一種類型化的建構體系。我對於思想客體的認識,主要來自於我的手頭的庫存知識(the stock knowledge of hand),並以類型化的方式來認識我所遇到的客體。除非遇到例外,否則一般客體都會在這一體系内找到自己的位置。類型之下又有此類型,具體的實在客體會具有特別的特徵,與經驗發生衝突的,則會被視爲“問题”。手頭的庫存知識來自於生平情境(biographically situation),即行動者當下所處情境的歷史,過去經驗的沉澱。
日常生活世界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主體間性的世界,是一個文化的、有意義的宇宙。在主體間性的層次上的思想客體建構,是社會化的。這種社會化包括三個方面:(1)觀點的相互性,或者説知識的結構社會化;(2)知識的社會起源,或者説知識的起源社會化;(3)知識的社會分佈。觀點的相互性包括,我的“這裏”與他之“那裏”不同,我的生平情境與别人的生平情境也不同。而克服這兩種差異需要兩種基本理想化,(1)觀點可换的理想化,如果我與他人易地而處,我之這裏換爲他之那裏,則我會與别人採取相同的類型化來看待事務;(2)關聯體系一致的理想化,除非有反證出現,否則生平情景的不同會被理所當然地認爲,與行爲的目的無關,“我們會假設,我們都會以一種等同的方式,或至少是‘經驗上等同’的方式,即對實際目的而言充分的方式,來選擇與詮釋共同的行動客體及其特徵。”知識的社會起源指的是我對社會的知識只有極少部分來自於我自己,絕大部分來自於社會,而這本身就包含了社會性。
比如説語言。所謂知識的社會分佈指的是不同的知識在社會那裏的分佈是不同的,另外,就個人而言,也意味著每個人都是三種形象的一體:專家(expert),路人(the man on the street)與廣博見聞的市民(the well informed citizen)。這様,在我群關係之外,我同時與同世界之他人共在並以類型化的方式與他們打交道;而從時間向度上來説,則有前輩世界與後人世界。日常生活中的行動者,如前所述,會以社會行動來應對他人轉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原因動機,所以總是能夠理解他人的行動。這是與社會科學的觀察者非常不同的一點。由於日常生活中的被觀察者總是處於一種互動的意義脈络之中,所以對於彼此的理解可以得到即時的檢驗舆糾正。
而社會科學的觀察者,最大的困難首先在於,作爲社會科學的觀察者所秉持的,不同於日常生活的態度。“當他(社會科學觀察者)決定科學地觀察這個生活世界時,即意味著他不再把自身及自己興趣條件當作世界的中心,而是以另一個零點取而代之,以成爲生活世界現象的取向。”社會科學的觀察者,並非以日常生活的參與者的形象出現的。即使是在訪談類的觀察中,也非如此,儘管訪談的特徵是雙方的互動,因爲訪談一旦發生,被觀察者的日常生活也就停止。要完成一個從日常生活的至尊現實世界到社會科學世界的躍遷(leap),就必須將自己從實際的日常生活中抽身出來,“並將自己的目的動機限制在如實地描述與解釋所觀察到的社會世界中去”。
而描述與解釋所運用的一個重要的工具就是理想類型。首先針對被觀察者建構出典型的行動過程類型,然後再整合爲個人理想類型與行動者的模式,另外,這些理想類型的行動者是有意識的。這裏的意識指的是目的動機,以對應於被觀察之行動過程的目標。另外還賦予典型原因動機。所有的相關資料,都由研究者賦予,舒茨以具備意識的木偶來比喻理想類型。建構理想類型的法則包括關聯性假設、適當性假設、邏輯一致性假設與相容性假設。
.png)
韦伯著作《社会科学方法论》。图源:豆瓣。
如此可知,社會科學中涉及到方法論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主體間性。無論對於被研究者的日常行動者來説還是對於社會科學家來説,都是如此。而對於這個領域的分析,則是現象學的任務。自然態度之下的行動者所獲得的意義現象,“原則上可以在一般性的主題内給予精確的描述與分析。在世俗的主體間性層次上完成這些工作,是世俗的文化科學的任務,而仔細説來,澄清他們時所使用的方法,則是自然態度構成現象學的一部分”。舒茨在首次提及這一問題時,仍然以胡塞爾的超驗現象學爲思考的起點。但是在後來系統討論社會科學方法論時,就已經將自己的思考基礎放置在了日常生活之中:“實證的社會科學終將發現其真正基礎並不在於超驗現象學,而是在自然態度的構成現象學。”
但是舒茨自己的構成現象學,並没有真正解決主體間性的可能性問题,而是簡單的將其置於日常生活中:“通過我手頭知識庫對他身體行爲以及表達性行爲等的闡釋,我同伴的行爲稱爲可以理解的,如此,我只是簡單的接受他的意義行爲的可能性。進而,我知道我的行爲也會相應地在他那裏,被他的詮釋行爲中被詮釋爲有意義,並且‘我知他知我知’。日常生活世界因此在基本上就是主體間性的。”但是他在後期的討論爲我們提供了進一步思考的線索。舒茨最後將主體間性的可能性簡單的歸於日常生活,而不再多加討論。所以下一個問題就是,就主體間性的問题而言,日常生活中所預設的,究竟是什麽?
.png)
舒茨在後期開始放棄胡塞爾的超驗現象學,但是他在主體間性的問題上並没有解決他人是如何可能的這一問題。無論前期還是後期,自始至終,他所努力的方向,都在於描述主體間性發生的現象,而没有關注主體間性發生的可能性。對於舒茨而言,這様的困境源於理論基礎胡塞爾的思想。所以我們可以從海德格爾對於胡塞爾的轉向來分析舒茨後期所説的“日常生活中的預設”。在先於舒茨日常生活的地方,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的討論可以用來做一個分析的嘗試。海德格爾對於胡塞爾的批評以及在共同世界上的討論,爲我們提供了在主體間性可能性問题上的討論空間。
主體間性的可能性,在海德格爾那裏,在於Dasin,即此在。主體之所以能夠溝通,原因在於他的常人狀態,在世之在。在世之在並非指的是日常的社會世界或者生活世界先於主體間性,在世之在指的是先於意識的一種存在狀態,常人在這個時候,在消散於世界的時候,是與他人共在的,這種共在,提供了主體間性的可能性。
.png)
海德格尔著作《海德格尔文集: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图源:商务印书馆。
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一直懸置了對於自然態度與日常生活的解釋。而這兩個概念,在舒茨的思想體系中,是至關重要的。舒茨前期以現象學的方法發現了社會世界中行動者的生活世界,而後期更將自己的立論基礎直接放在了日常生活中。但是日常生活與自然態度,在舒茨那裏究竟意味著什麽?爲什麽舒茨會將主體間性的可能性直接賦予日常生活?在舒茨那裏,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態度,一個重要的特徵即理所當然的態度(take it for granted)。從進入社會生活的第一步,行動者就將這個世界理所當然地視爲主體間性的。而舒茨的生活世界體系,也在這一基礎之上得以建立。那日常生活中的行動者,能夠進行這種理所當然的態度的前提在哪裏呢?這就是我們進而追尋主體間性的可能性的途徑。
現象學是什麽?在胡塞爾以《邏輯研究》爲現象學正名以來,這個問題不斷地被提出,正如梅洛龐蒂所説,這都並不意味著這一問題已經被解決了。現象學並非一個可以嚴格加以限定的概念,當然也不可能被當作現成物拿來使用。現象學的反思能力本身决定了它是一個不斷發生著的過程。所以海德格爾與舍勒都將自己的思想稱爲“現象學的”,而非現象學,因爲現象學這個概念,首先表示著某種思維的方法。這種方法,得以將現象學運動與其他哲學區分開來。這也適用於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關係。
胡塞爾稱之爲“無前提性原則”或者“從先於一切觀點的東西開始:從本身被直觀給與的和先於一切理論活動的東西的整個領域開始”。海德格爾同様認爲,現象學研究,首先要擯棄立場,也不要有方向,強調的是自明性。這種無立場性和無方向性所説的其實就是“面向實事本身”。但是我們面對什麽様的事情又或者説,我們需要面對什麽様的現象呢?在這一點上,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回答已經不一様了。胡塞爾所面對的主要是純粹意識體驗與意識生活,後來則是先驗的意識生活與主體性。
這様的思考方式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了舒茨對意義問題的思考,進而影響著對主體間性問题的解决。而早期的海德格爾則轉向了有“内容”的現象學,這種轉向有兩條路徑或者説其實只有一條路徑:存在者之存在。二者的區别由此産生。按照海德格爾的觀點,舒茨在對社會學的意義概念的討論中遵循胡塞爾的現象學路徑,本身就成爲了非現象學的思考,也就是説,他首先將胡塞爾的意識分析當作了自己的立場和原則,而没有真正的面對日常生活本身。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海德格爾對於日常生活的關注,來源於他的哲學觀。在思想早期,海德格爾在確定哲學主題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關注人之週圍世界(Umwelt)。海德格爾的這一關注來源於他對哲學主题的提問,而他的回答,則不想與胡塞爾一様,落到對生活之理論與人的知覺方面。因爲胡塞爾將體驗作爲本質直觀的物件,將現象學放到先驗領域的理論,會將活生生的生活排斥掉,“理論化使我們的大多數原初經驗非指明化、非歷史化、非生活化和非世界化”。哲學對於邏輯與科學的追問,必须追回到前科學的生活中去,海德格爾反對科學將世界非生活化以及理論以概念來代替生活的趨勢。他認爲,真正的現象學的“看”,所觀察的領域並非超驗的領域,而應該是前理論的,前世界的(pretheoretical preworldly)東西,這才是真正的朝向實事本身:“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在它們的動力和趨勢中,從經驗上經歷這些活生生的經驗。總而言之,我們必须去理解生活。因爲,生活不是非理性的,它是徹底地可理解的。作爲原初經驗之經歷的現象學的直觀是解釋學的直觀。”
基本的哲學觀使得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截然不同。胡塞爾仍將哲學視爲傳统的學科,並希望建立一個作爲嚴格科學的哲學,而海德格爾則不再對先驗層次感興趣;胡塞爾的現象學懸置首先即要求將自然態度下的生活“放入括弧”,不再對其考慮,而這正是海德格爾所思的進階;胡塞爾希望能夠以超驗領域的研究來爲時代尋找根據,而海德格爾則對此表示懷疑。
“具體説來,海德格爾對胡塞爾先驗本質現象學的改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向上:一是把先驗意識的現象學改造成爲‘存在現象學’或‘此在現象學’;二是把本質直觀的現象學改造成爲‘現象學的解釋學。”
胡塞爾將現象學的操作基本規定爲:“由於事關原則,因此這裏更重要的問题在於:現象學就其本質而言必须提出這様的要求,它要求成爲一門‘第一哲學’,並且它必须爲所有須待進行的理性批判提供手段;因此它要求最完善的無前提性和對自身的絕對反思性明察。它的最獨特的本質在於,最完善地澄清它自己的本質,從而也最完善地澄清它的方法原則。”而海德格爾在討論到相關問题時,指出,“惟有現象學批判標準才是理解的明證和明證的理解,是在本質中自在和自爲的生活。現象學的批判……是去理解被批判的命題,理解這些命题的意義起源在哪裏。批判就是聽出真正的動機。”
在胡塞爾那裏,明證就是直觀,但是在海德格爾那裏卻並非如此。海德格爾那裏的領會與解釋緊密相連,並與此在有著密切的聯繫,它既是獲取被領會者的過程,也是自身形成的過程。解釋是對已被領會的世界的釋義,它能夠把某物作爲某物來解釋。任何解釋都是有領會前提的,領會本身就具備一種“在先”(Vor)的結構。
胡塞爾的“立義”(Auffassen)概念,指的是意識活動的功能,即將某物立義爲某物,將感覺材料賦予某種意義,並得到統一而成爲我的物件。也就是説,胡塞爾的立義是通過賦予意義而使某種東西被給予我,所以這就是原初的活動。海德格爾的“解釋”卻是將原來已有的東西釋放出來,展現出來,它與領會相比,具有在後性。儘管兩個概念所講述的内容大概相同,但是在各自體系中的位置卻不一様,在胡塞爾那裏處於原初性的意義賦予過程,在海德格爾這裏成爲了第二性的。在海德格爾那裏,胡塞爾所強調的源初的“無前設性”和“無先見性”都成爲了第二位的,取而代之的,是“領會”。
舒茨儘管放棄了胡塞爾的超驗基礎,但卻仍然認爲現象學直觀所面對的意義賦予的過程,是社會學領域内最原初的東西,所以他並不能夠解決主體間性的問題,因爲他仍然在使用胡塞爾的現象學觀念,這總有一個建構的問题,這様的原初活動,即意識構成分析,與海德格爾的領會相比,就已經處於第二位了,這也是我們需要從海德格爾入手來面對主體間性問題的原因所在。胡塞爾的意識分析是將作爲最終根據的無前設放到了意識之中,舒茨前進了一步,將自己的分析基礎放到了日常生活之中,但是他在此之上進行的分析,所構造的生活世界,是以現象學的方法來構造的社會學上的“理想類型”,而没有以現象學的方法來“直面”活生生的,正在進行中的生活世界本身。舒茨在理解主體間性問題的時候,將主體間性的可能性放到了日常生活之中,之後就忽略了真正的日常生活,而只關注於其理論建構,並將之視爲真正的日常生活。
所有的領會都是人的領會。日常生活,包括諸種科學的活動都是人的活動,人作爲一種存在者,有著與其他存在者不同的特徵:“這個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與這個存在本身發生交涉。”只有人可以領會著存在並且對存在發問,在存在論層次上發問,這是人的與衆不同之處,海德格爾用此在來表示這様的存在者。
此在的特徵有兩點:(1)此在的“本質”在於“去存在”(Zu-sein;To be),假如我們可以用“本質”這個詞的話。我們要明白此在這種存在者是什麽,就要從它怎麽様去“是”(ist),從它的存在(existentia)來理解。存在對於是什麽或者説本質(essentia)具有優先地位;(2)“這個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對之有所作爲的那個存在,總是我的存在。”也就是海德格爾所説的“向來我屬”(Jemeinigkeit)的性質。此在以各種方式是我的此在,這種向來我屬早已決定好了,問题只是以何種方式向來我屬。但是無論以何種方式向來我屬,“此在總作爲它的可能性來存在”。這種可能性並非某種屬性,而是説,此在本身就是這様一種可能性,此在可以選擇自身,也可能失去自身。
此在就本質而言可能擁有本己時,也就是可能失去自身之時。對於此在的研究,並非從某種“差别相”來進行,反而恰恰要從日常生活中混沌的“平均狀態”(Durchsschnittlichkeit)來進行,當然這種平均狀態並非意味著一無所有,它反而是某種積極的現象,“一切如其所是的生存活動都從這一存在方式中來而又回到這一存在方式中去”。這是此在最近與最熟知的東西。我們可以通過某種结構來把握此在的生存論性質,但是在此之後尚需進一步討論。
日常在世的一個基本特點在於,在世界中,與世界打交道,或者説,交往。此在並非僅僅在世界之中,而是以一種非常的方式與世界聯繫。此在與世界最切近的交往並非認識某物,而是操勞某物。這種操勞某物在很大程度上近似於舒茨所説的視爲理所當然之境,在日常生活中是被人所遺忘的。在這種操勞活動中照面的存在者即爲用具(Zeug),用具只有在“用具整體”中才能夠“存在”。在這一整體中有一種“爲了作……的東西”,即從某種東西到另一種東西的“指引”(Verweisen)。用具的整體性,要先於個別的用具,因爲只有在整體中,在勾連指引中,用具才可能成爲用具。
在此在與世界打交道之際,在打交道的隨心所欲,也就是舒茨所謂的日常生活的毫無問題之際,用具才能夠如其所是地來照面,此即用具的上手狀態(Zuhandenheit)。而這種切近的上手事物的特徵就在於:“它在其上手狀態中就彷佛抽身而去,爲的恰恰是能本真地上手。”作爲用具的上手之物,存在結構可由指引來規定。運用用具所製造出來的東西稱爲工件,與工件一起照面的,不僅有上手的存在者,而且世界也一起來照面,這個世界是我們的世界,操勞所及的工件也在公衆世界上手,週圍世界的自然也伴隨著一起顯露出來,成爲所有人可以通達的。上手之物通過觸目、窘迫以及膩味這些様式,將在手性質映現出來。這様,我們可以説,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尋視而非專題的消散於那組建著用具整體的上手狀態的指引中。”也就是説,這一世界的整體性是由上手之物引發而來,在上手之物中,世界就已存在。
上手之物具有指引結構,它於其本身被置指引向某種東西,從而與某種東西發生關係,海德格爾稱爲“結緣”。由此,可以説,上手之物的性質就是“因緣”。存在者向來就有因緣,將這様的因緣追問到底,就是一種“爲何之故”,這種爲何之故在此在這裏,就是此在本質上爲了存在本身而存在。而作爲這一過程的了卻因緣本身,就已經意味著“一切上手事物之爲上手事物的開放”。因緣的開放本身就已經證明了因緣的整體性,而上手之物的合世界性也就已被揭示出來。
世内存在者首先向之開放的那種東西,必已先行展開,這裏的先行展開,海德格爾指的是領會。領會總是某種活動的領會,所以我們可以説,“如果此在本質地包含有在世這種存在方式,那麽對在世的領會就是此在對存在的領會的本質内涵”。比如上述作爲追尋結果的爲何之故,則必定有一個先行的領會,再比如此在先於存在論也領會著自身,即在“何所在”中領會著自身,這種“何所在”就是先行存在者向之照面的“何所向”。“何所向”讓存在者以因緣存在方式來照面,它“自我指引著的領會的‘何所在’,就是世界現象。而此在向之指引自身的‘何所向’的結構,也就是構成世界之爲世界的東西”。這裏的世界既非主觀的世界也非共同的世界,而是一般的世界之爲世界。由於在世是此在的生存論規定,所以世界之爲世界本身就是一個生存論環節。
如前所述,此在的一個重要性質是“向來我屬”。但是這個向來我屬並非指在存在者層次上的“我”,或者是主體性。因爲假如這様的話,在存在論上就會成爲一種向來總已自明的封閉領域,一個具有自我性質的主體,就假設了某種實體,此在就成了“現成實在”的東西。但是在海德格爾那裏並非如此,此在分析的入手之處並非已經先行給定的主體或者是“我”。“從首先給定的‘我’和主體入手就會完全錯失此在在現象上的情形。”也就是錯失此在在現象上的可能性,因爲主體這個觀念在存在論上事先預設了可見現象之下的東西,就是亞里士多德用以與形式相對的“質料”。從這一假設出發,在存在論上就會出現一種向來總已經自明的封閉領域,一個具有自我性質的主體,此在就成了“現成實在”的東西。海德格爾認爲這些都不是此在,反而恰恰是非此在的存在方式。日常此在的這個“誰”,向來都不是我自己。那麽此在爲誰?
胡塞爾與舒茨的現象學,都從某種自明性的東西入手來展開自己的分析。在這裏,自我的給定性是一切給定性的源頭。胡塞爾與舒茨所運用的都是“素樸的,形式上的反省”,從我的知覺所給與的東西來展開分析,所展開的是形式上的意識現象學。在胡塞爾與舒茨那裏的“我”顯然並非此在,這是兩條根本不同的路徑。
按照海德格爾的説法,此在談及自己時,往往在“我”並非這一存在者時才會真切感受到,也就是説在海德格爾那裏,“我只是某種東西不具約束力的形式標記,這種東西在當下現象的存在聯絡中也許會綻露自身爲它的‘對立面’”。對於此在的追尋不能夠從“我”出發,如前所述,首先存在的,或者説,一直就存在的,並非一個無世界的單純的主體,當然更不是與他人絕缘的封閉的自我。在週圍世界中,隨同用具共同照面的,不但有上手之物和現成的自然,還有他人。他人不但與用具與自然有别,而且還有自己的此在存在方式,工件就是爲他人而設的。指引所及的物件,對他人來説就是上手之物。這様,在此在的上手之物與現成的自然之外,有某種他人的此在的存在方式,它作爲此在,也是在世界中,在他的此在存在方式中,他人同様是在世界中的,而另一方面,這個在世界中的他人,又以“在世界内的方式來照面。這個存在者既不是現成的也不是上手的,而是如那有所開放的此在本身一様——它也在此,它共同在此”。
這様,世界向來總是我和他人共同享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就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與他人共同存在。這裏的共同在此,意味著他人敞開此(Da)的狀態,此在與他人共在,因爲此在本身就是共在,此在與他人共同享有此在這種對事物和世界的敞開狀態。
但是這個他人並非另外一個主體,這裏也不包含某種此在移情(同情)或者結對聯想的問题,這毫無疑問隱含著我之爲此在的危險。海德格爾認爲,他人並非我之外的主體,這様“我”就會凸顯出來。這裏的他人與此在一様,他人是“我們本身多半與之無別,我們也在其中的那些人”。所以説此在的世界是共同的世界,在世界之中,是與他人共同在世界之中。此在向來就與他人共同存在,此在與他人一様,都是從週圍世界來照面,此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共在。此在從週圍世界來領會自身,而他人的共在也在同時,從上手之物來照面。
這裏的領會,並非由認識所得來的知識,而是“一種源始的存在方式,惟有這種源始的存在方式才使認識與識知成爲可能”。此在的存在之領會中,就已經包含了對他人的領會。在這之後才能談論對於自我的認識,自我識知要以他人的共在爲基礎,要以此在與他人的有所操勞的操持之展開爲基礎。此在消散於所操勞的世界中,也即消散於與他人的共在中,這個時候,此在並非它本身,而是常人。這個常人就是此在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他人並非指與主體相對的我的他人,如前所述,當然也非指一些人,一切人,而是中性的“常人”。常人的生存論性質是“平均狀態”,平均狀態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庸庸碌碌,夷平状態,以平整作用將一切例外排除。這個常人卻並非具體的某人,如此可以以預定的一切判斷與決定將日常生活中的責任卸除。以上種種性質就是此在的常駐状態,是此在作爲共在的存在方式,“日常生活中的此在自己就是常人自己,我們把這個常人自己和本真的亦即本己掌握的自己加以區別。一作爲常人自己,任何此在就涣散在常人中了”。自我意義上的“我”並不首先存在,“我”要“晚於”以常人的方式出現的“他人”。
此在存在者的“此”,就是“這裏”與“那裏”,並非截然可分,它們的可能性共同基於這個“此”的本質性的展開。本質即是“展開”的此在是以情緒之方式展開。此在總有情緒,但是這種情緒是作爲此在的源始存在方式出現的,這種現身情態(Befindlichkeit)並非與理解或者認識同類之物。情緒與“主體”或者“内在”無關,當然更與外在無關,情緒是“作爲在世的方式從這個在世本身中昇起來的”。所以現身在這裏意味著世界、共同此在和生存同様源始地展開了——展開的狀態就是在世。此在如此的現身,在海德格爾看來,就是内省能發現“體驗”的原因。
現在可以回頭來看薩特在主體間性問题上對於海德格爾的批評。按照科克爾曼斯(Kockelmans Joseph J.)的説法,薩特對於海德格爾的批評源於這様的事實:“他錯誤地理解了海德格爾賦予‘存在論狀態上的’和‘存在者狀態上的’這兩個術語的意義(科克爾曼斯,1996)。”海德格爾對於此在的考察從存在論入手,但是存在論層面不能夠與存在者層面分析割裂開來,此在分析並非分析實在某物,存在論層面的分析也不同於具體的東西。這裏不存在具體與抽象的關係。
使得事物和此在的存在得以理解的東西就在於存在論,因爲此在的與衆不同之處就在於它在自己的存在中與這個存在本身發生交涉。“對存在的領會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規定。此在在存在者層次上的與衆不同之處在於:它在存在論層次上存在。”所以我們需要清楚,此在的基本結構並非建構出來的,而是海德格爾加以描述的實事之所是。薩特對於海德格爾的理解,並未脱離傳統形而上學的抽象與具體之對立的命題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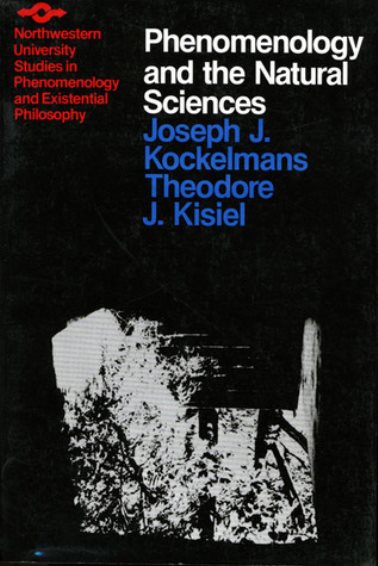
Phenomenology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 by Joseph J. Kockelmans。图源:Goodreads。
與現身同様源始地構成此之在的,還有領會。領會並非指一種具體的認知模式,而是使某種具體的認知模式得以可能的可能性。所有的領會都與現身情態有關,並参與決定在世的存在様式——也就是説,源初的領會中,人的存在様式顯現爲“能在”,這種能在並非指某種具體的可能性,而是説,它本身就是成爲某種具體可能性的“可能性”,此在本質上就是一種能在,“此在事實上生存著的時候,它總是一定的可能性,並因此而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此在是一種可能性,儘管它“向來已經陷入某些可能性”。
源初的領會總是對整體的此在在世的領會,並且由於本身具有一種“籌劃”的生存輪結構而能揭示各種可能性。這種籌劃不但包含著此在的“爲何之故”的籌劃,而且也同様源始地包含著使此在的當下世界成爲世界的籌劃。這様,在籌劃的性質上,領會構成了海德格爾所謂的此在的“視”(Sicht)。在如此的基礎意義上的“自我認識”,即對於具有内涵的自我的完全而又豐富的認識,海德格爾認爲,並非如胡塞爾所説的是通過素樸的感知和反思而來的,自我認識“是貫透在世的所有本質環節來領會掌握在世的整個展開狀態。”就是與敞亮(Gelichtetheit)相對的那種“境界”,在其中,存在者本身無所遮掩的前來照面。所有的視都植根於領會,而非從純直觀而來——海德格爾由此取消了胡塞爾的純粹直觀的優先性。
領會的籌劃活動具有使自身成爲某種可能的可能性,而這様的成形活動,海德格爾稱爲解釋。解釋植根於領會,但是領會在解釋中成爲自身,解釋是領會的可能性的發展。但是解釋並非是給與一種説法,或者根據意向性地構造結構將某種意義賦予,海德格丽的解釋是説,把世內東西的因緣説出來而已。領會中展開的東西總是按照“作爲”結構出現的,某種東西總是作爲某種東西被領會,“這種‘作爲’構成了每一被領會之物的明晰性的結構,它就是我們稱之爲解釋的構建性因素。”因緣整體性是尋視著解釋的本質基礎,領會先就有一種在先(Vor)的結構,這是解釋的基礎所在。解釋基於源初領會的勾連指引,儘管上手之物在此與世界之間的關係在這裏並不需要被主題式的把握,但是某種主題式的解釋,也是植根於源初的領會的,也即海德格爾所説的“解釋學的情境”(hermeneutic situntion)。
所以我們可以説,胡塞爾所謂的意向性分析,與此在存在的結構分析相比,並非是最源初的。但是這並不是説海德格爾要否定胡塞爾的意識分析,而是説,胡塞爾的分析並不是完善的。海德格爾在這裏要強調:“人們所説的意向性——單純的朝向某物——必须被回置到那個‘先於自身的—在之旁的—在之中存在’(Sich-vorweg-sein-im-sein-bei)的統一的基本結構中去。這種存在才是本真的現象,它與那種非本真地,僅僅在一種孤立的方向上被當作意向性的東西是相符合的。”海德格爾要做的是從意識分析中抽身出來,回到更源始的此在存在結構。在海德格爾看來,將意識看作現象學研究的出發點,並没有真正的堅持“朝向實事本身的”原則,比如説意向性的基礎,意向性自身的結構基礎都没有釐清。海德格爾認爲胡塞爾種種缺陷的根源在於將意向性等同於意識本身,而没有對意向行爲和被意向者的關係做一個清晰的分析。而笛卡爾以來的近代哲學的基本錯誤,就在於對人之主體性的理解。將人之主體“我”作爲確定性的根源,然後展開世界與其他的主體的分析,比如説主體間性的分析,這様的路徑從根源上就是構造的。從這様一個主體出發,海德格爾認爲,現代哲學並未能夠真正面對實事,而是以人與世界及他人割裂爲前提,進而再反過來尋找某種“契合”(convenientia),這就是説,首先就將現象變爲碎片,然後再將現象重新合成。但是這一工作只能夠進行到描述主體間性的發生過程,至於它所由來的可能性,則根本不在主體間性的範疇之内,所以從主體出發,對於主體間性之可能性的追尋,並没有可以依循的路徑。
所以説,主體間性可能性的問題本身,不論是胡塞爾後期還是舒茨的構成現象學,只要是對主體間性可能性的追尋,事先已經预設了某種錯誤的前提——設置了一個主體。儘管我們不能由此來否定舒茨在所謂構成現象學中對於主體間性發生過程的討論的有效性,但是主體間性的可能性,顯然並不能由此而來。在海德格爾看來,這並没有真正面對事實本身。由此所導致的認識問題也就步入歧途,就是説,從主體開始對認識問题進行探討,首先預設的前提是一個封閉的,有內在活動的“主體”,然後是主體與客體的區分,這様,認識的問題才會出現,比如説認識是如何可能的?認識他人是如何可能的?
從海德格爾的路徑來看,這種種問題都錯失了在現象上更爲本源的東西,即“漏過了這個認識主體的存在方式問题”。以海德格爾的方式來看待這一問题的話,認識方式首先就稱爲在世的一種存在方式,然後,,它其實是一個衍生而非原生的問题,它直接同存在相關,而這様的存在是已經寓於世界而存在了。認識的可能性則直接奠基於操勞活動的某種“殘斷”,然後才可能同世界發生照面,才會有所謂的觀察,而這種觀察又總是已經選定了方向的觀望,是“在如此這般發生的‘滯留’中發生對現成東西的知覺”。海德格爾所謂的知覺就是將某某東西看作某某東西,也就是解釋——最廣義的解釋。在這種解釋的基礎上,直覺成爲規定,進而由話語説出,被保持和保存下來。
但是海德格爾在這裏所説的仍然不涉及主體以及“在內”的問题,也並非從內在的某某地方出去,而是説,它一向就在世間鋪排開來,依寓於世界存在。知覺並非説作爲主體的“我”從外部世界獲得某種東西回到自身來,而是在這種知覺中,此在依然“在外”。這裏的認識與主體同世界的交往並不首先相關,當然也並非是由主體與世界之間的關係而來的,認識是此在植根於世的方式。海德格爾將此在領會爲已經在世界中存在的存在者,它向其他的事物和具有此在模式的其他存在者開放,他們共同存在,擁有這個世界。在主體性之前,人與世界並非截然分開,此在與他人共同享有一個世界。此在與他人的共在,才是主體間性得以可能的所在。而舒茨所説的主體間性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那裏的預設,也當由此來尋找。因爲向他人的存在作爲共在,總是伴隨著此在的存在而存在著,此在總與他人共在,“並不是説‘移情’才剛組建起共在,倒是‘移情’要以共在爲基礎才能可能”。這様,我們現在可以暫時這麽説:主體間性在日常生活中預設的可能性,就在此在之爲共在。
.png)
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立者埃德蒙·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胡塞尔(德语: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4.8—1938.4.26)。图源:Wikipedia。
.png)
但是事情還沒有完結,對此在之爲共在的分析需要放置在海德格爾對存在的思考中才能真正理解。此在之爲共在這種日常狀態將自己交付給常人,組成了此在的日常生存模式:沉淪。此在的沉淪在情緒中展開來,人也由此而進入非本真狀態,與這種非本真狀態相比而言,源始的被抛狀態(die Geworfenheit),是對未來有所籌劃的。有所籌劃是說,人永在可能性中而無規定性:在人之“去是”(zusein, to be),先於“所是”,用傳統形而上學的話來說,就是存在先於本質(der Vorrang der Existentia vor der Essentia)——也就是可能性要先於本質的意思。海德格爾希望藉由對此在之存在的展開來獲得絕對存在。
但是將主體間性的可能性放置於海德格爾的此在也不是沒有危險的。或者是說海德格爾的此在有沒有可能是一種極端的主觀主義?或者是說,運用海德格爾的此在分析來面對主體間性是否過於簡單?這裏我們遇到了德里達,勒維納斯,讓呂克·南希(Jean Luc-nancy)等人的批評。由此甚至可以認爲,“海德格爾的本來意旨是要反近代以來的主體形而上學傳統,但自身終究也未能跳出這個傳統的範圍”。所以關於主體間性的討論,就思想史的批評來說,討論遠未結束。海德格爾後期對這樣的危險也有所警醒,並有“轉向”,開始向“在”尋思。即,就現象學社會學的主體間性理論來說,在海德格爾後期消除了主客之分的存在之思後,主體間性的問題已經消解,那我們應該如何來面對這一問題的重新建構?就這一問題而言,本文同樣只是一個起點。
社會學中對於主體間性的思考,必定牽連意義問題,韋伯指出,現代社會的意義問題要由個體承擔,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現象學的思考在此恰恰可以有所作爲,這裏我們不能繞過海德格爾後期所思的意義發生之:這是主體問性問題從意義角度來思考的一個方向。主體間性問題關涉到現代社會的可能性,所以海德格爾在本文中的一個隱含的意義在於,如何從主體性的角度來重新審視現代社會?
從傳統社會哲學的角度來說,如果我們向前去追尋在現象學中,從胡塞爾到舍勒以及舒茨諸人對於主體間性乃至主體性的討論,會發現他們的線索在基督教哲學,政治哲學以至盧梭從自然人到社會人的探討中隱隱浮現。儘管這可以作爲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方向,但是我們仍需注意,由此進入共同體乃至現代性的問題並非如此簡單,除去大量細緻的工作以外,就共同體的問題而言,考慮到讓呂克·南希以知識考古學的方式對共同體神話的解構,共同體這一概念本身是否也值得我們去思考?
文字编辑:王文彬、卢海瞳
推送编辑:苟钟月、毛美琦
审核:许方毅
文字节选自《社會理論學報》 第八卷第一期(2005): 93-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