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立瑋:社會共同體與社會團結——帕森斯探討現代社會整合問題的路徑(下)
趙立瑋
(中閾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摘要:帕森斯在1960年代中期明確地提出了社會共同體概念以及以之爲核心的理論分析圖式,從而構成了他中後期探討現代社會中的社會整合或團結問題的主要範式。雖然該範式是帕森斯對社會理論中的社會整合或團結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但在西方帕森斯研究中該分析卻長期受到忽視。本文試圖在闡明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觀念的基礎上,緊扣社會共同體與社會團結的關係這一核心問題,溯及它與塗爾幹、韋伯等古典社會理論家的智識根源,並結合近期的一些相關研究指出它與公民社會以及全球化這些當下的重要論題相結合的可能性及其意義。
.png)
通過前面幾節的簡要闡述,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帕森斯對社會學的研究主題的界定,對社會共同體這個範疇的涵義的確定及其在社會或社會系統中的功能性定位,抑或是從比較—進化視角對人類歷史上的“社會共同體”的考察,始終圍繞著社會整合或團結這個核心問題;因爲就其實質而言,“社會共同體”就是一個社會整合系統。不過,帕森斯所闡述的這個社會的整合子系統是如何履行其社會整合或團結的功能的呢?下麵結合帕森斯的相關論述,僅就其中的幾個要點予以簡要闡述。
首先,作爲一種“共同體”,帕森斯強調了共同體成員對於集體的“忠誠”:
“在我們看來,社會共同體這種(社會的)整合性子系統的基本功能在於確定人們對於社會集體的忠誠的義務,不論是對於社會內部作爲一個整體的全體成員還是對於分化性的地位和角色的各種範疇來説皆如此。……忠誠就是對於那些以集體或公共利益或需要之名恰當地‘證明了是正當的’訴求的欣然應允。規範性問題是當這樣一種回應構成了一種義務時對時機(occasions)的確定。一般而言,任何集體都要求忠誠,但是對於社會共同體來説,忠誠具有某種特別的重要性。政府機構一般是籲求社會忠誠的代理人,它們也是履行相關規範的代理人。”
在現代高度分化和多元化的社會中,這種“忠誠”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特別重要的是亞群體和個體對社會共同體的忠誠和他們對作爲其成員的其他集體的忠誠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多重角色(role-pluralism),即同一個人關涉幾個集體,是所有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徵。總的説來,多重角色的某種不斷增長是那些導致現代的社會類型的分化過程的一個主要特徵。因此,對於某種社會共同體來説,對於人們對該共同體本身的忠誠和對其他各種集體的忠誠(之關係)的調節就成爲一個主要問題。”現代社會中的這種“多重角色”與其多元主義特徵密切相關,現代高度分化的多元社會的整合或團結問題因此構成了帕森斯“社會共同體”理論的一個核心關注點。
另一方面,共同體的成員總會面臨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係問題。帕森斯認爲,社會共同體的團結實質上是一個程度問題,其中,“無論在什麽情況下,當其成員的單位利益與集體利益兩者之間出現衝突時,我們都可以期望集體利益超越單位利益。”不過,帕森斯認爲可以通過“相互尊重”而與集體中被制度化的價值和規範保持一致:“總的來説,個體的自利性動機通過各種與成員身份和對於諸集體的忠誠而被有效地導入社會系統之中。對於大多數個體來説,最爲直接的問題就是萬一在各種競爭性的忠誠義務之間出現衝突而進行調整。”
不過,共同體成員對於集體的忠誠雖然重要,但根據帕森斯的“控制論等級”思想,在共同體之上還存在著一個更高的價值領域:“對於社會共同體的忠誠在任何穩定的忠誠等級中都必須佔據一個很高的位置,並因此成爲社會關注的一個主要焦點。然而,這種忠誠在忠誠等級中並不佔據最高的位置。”根據前文對於“社會共同體”的界定,社會共同體中存在著某種“規範秩序”,因此,“規範系統支配著(成員對共同體的)忠誠,它必須不僅要將各種集體及其成員的權利和義務相互整合起來,而且要與作爲整體的秩序的合法性基礎相整合。”在共同體中,存在著一個明確的分層系統:“在其等級方面,借助成員資格對社會共同體進行的規範性秩序化包括其分層標準,這是被人們所接受的關於諸亞集體、地位和角色以及作爲社會成員的個人的聲望標準(而且,這是就價值和規範是整合性的和合法的情形而言的)。它必須與支配成員身份之地位的普遍規範以及在亞集體、地位和角色的功能(它們並非如此指涉某種等級)之間的分化的諸要素相協調。因此,具體的分層系統是所有這些要素的一個複雜功能。”總之,“一個社會共同體就是一個相互滲透的集體和集體忠誠的複雜網絡,一個以功能分化和分割爲特徵的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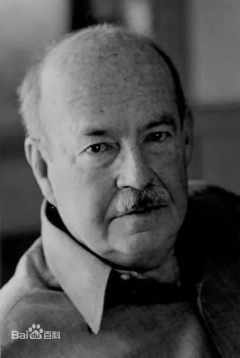
帕森斯。圖源:百度。
其次,帕森斯對現代社會中社會共同體所關涉的整合機制進行了探討。前文指出,帕森斯將社會和社會共同體界定爲一種“系統”的主要標準是其“自足性”,這種自足性體現在兩個方面,即內部整合和對外部環境的控制能力;同時,這種“自足性”實際上表現爲一個程度的問題,也就是説,社會和社會共同體的“自足性”體現爲一個進化的過程:“關於自足性,……我所指的是該系統的能力,這種能力既通過其內部組織和資源,也通過它對於來自其環境的輸入的使用來獲得的,其功能是自主地實現其規範文化,尤其是其價值,不過也包括其規範和集體目標。自足性顯然是生物理論意義上的一般化適應能力的某種程度(問題)。”
我們在上一節通過對人類歷史中的“社會共同體”的演化過程的簡要考察,揭示出“社會共同體”或者説帕森斯意義上的“社會”是一個不斷分化的進化過程;只有在現代社會,社會或社會共同體的自主性才達到了某種(相對而言的)“最高”程度。作爲一種“進化”過程,社會和社會共同體在其分化過程中不斷地遇到整合的問題。以“三次革命”爲例,“革命”必然帶來新、舊之間的衝突和鬥爭、帶來社會結構的分化和整個社會範圍內的動蕩,社會整合因此顯得迫切和必要:“民主革命和産業革命共同産生了現代社會尖銳的整合問題;前者幾乎完全集中在下述問題上,即,這樣一個(現代)社會的“成員”,亦即“公民”是什麽構成的;後者則更爲直接地集中在如下問題上:人力資源在經濟生産中的分配對於‘勞動力’地位的其他方面而言意味著什麽。這兩個功能性的問題複合體顯然支配著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裏人們的社會性‘關注’,並延續至今。”
不過,根據帕森斯社會—文化進化理論範式,社會進化的總趨勢或後果是社會的“適應能力的提升”(adaptive capacity upgrading),這種“提升”實際上體現的是“社會”層面上的“自由”:社會或社會系統對其環境的控制能力日益增長;社會共同體的“包容性”(inclusion)不斷增強;社會的價值觀更爲“一般化”:
三次革命(産業革命、民主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概念與漸進性變遷範式是相適合的,因爲所有這三種革命都涉及與現代社會的以前狀態相關的主要分化過程。另外,所有這三種革命都是通過一般化的和流動的資源的內在增長(而實現適應能力)提升的主要能動者(agencies)。所有這三種革命也都清晰地提出了它們在其中産生的社會之主要的整合問題,並使得我們所謂的價值一般化的主要轉變成爲必然。
因此,在一個高度分化和多元化的現代複雜社會中,社會整合成爲一個核心問題:社會共同體在履行其整合功能時既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同時也發展出一些較爲有效的整合機制。帕森斯提及的整合機制大致有:(1)現代“法律系統”;(2)社會共同體中的成員資格;(3)市場系統;(4)官僚制組織;(5)聯合性組織。
帕森斯雖然對現代法律系統的直接論述不多,但(在某種意義上)卻將法律系統視爲現代社會中最主要的整合機制。”他將法律視爲某種“一般性的規範性規則(normative code)”系統,它將約束力(bindingness)、可實施性(enforceability)、共識性要素等整合爲一個單一系統;現代法律系統並包含著“憲法成分”,這種憲法成分既非宗教的,也非“純然道德性的”:“憲法規範與社會共同體聯結在一起,並關涉存在於受人重視的聯合體形式中的社會忠誠;法律關注公民資格的道德性,但是並非必然都是道德性。”社會共同體的整合機制還與“市場系統”以及“科層制組織”有關:“在社會團結從宗教、種族以及地域的那些較爲原始的基礎中解放出來的地方,它就會趨向於培育出其他類型的內在分化和多元化。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建立在經濟的、政治的和聯合的(或整合的)功能之基礎上的團結。”因此,現代市場系統和官僚制組織也構成了現代社會的主要整合機制,這一點顯然與産業革命和民主革命等對西方社會及社會共同體的分化過程的推進密切相關。
帕森斯特別強調了“聯合組織”的重要性,指出某種“聯合體的原型”也許就是社會共同體本身。現代社會中的聯合體表現出三種主要趨勢:一是朝某種“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邁進,最明顯地體現在現代公民權的發展中(見下節);二是邁向“自願性”(voluntariness);第三是“程式制度”的重要性,尤其明確地適用於社會集體和政府機構之中。帕森斯認爲,在大規模的商業部門的“信託”機構(fiduciary boards)和現代職業這兩種規範性的背景中,現代社會那些具有高度重要性的操作性功能幾乎完全是通過聯合性結構來實現的。總之,帕森斯認爲在高度分化的現代社會,社會共同體已經與經濟體、政治體以及信任系統這些社會子系統分化開來,它們之間形成既相互獨立又相互滲透的複雜關係;正是這種分化使得社會共同體的“自足性”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現代社會複雜的整合機制也因此而形成。
第三,帕森斯對於現代“公民權”(citizenship)的發展對於現代社會中的團結問題的重要意義給予了特別的強調;“公民團結”構成了現代社會團結的一個核心維度。上文提及的“社會共同體中的成員資格(membership)”這種整合機制也與此密切相關。
帕森斯認爲,社會共同體內部的兩個基本方面,即規範性(秩序)方面和集體(組織)方面構成了兩極:“在一端,可以將規範秩序的主要內容視爲對於所有成員或多或少是普遍的。然而,這提出了如下尖銳的問題,即在如此廣泛的一個共同體的實際運作中,這種高度普遍主義的規範能夠被有效地制度化到什麽程度。在另一端,政府和規範秩序可能僅僅適用於某種特別小的共同體。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廣泛變動範圍之內,現代社會共同體一般採取某種建立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的形式。這種形式的發展既涉及社會共同體和政府之間的某種分化過程,也關涉社會共同體的性質、尤其是與成員資格相關的方面的改革。”帕森斯指出,在歐洲社會共同體的發展過程中,在社會成員資格方面出現了一個“公民模式”取代“臣民(subject)模式”的變革;並借助於T.H.馬歇爾(T.H.Marshall)關於西方“公民權”發展的三維模型(三要素或三階段)的著名論述,闡述了“公民權”或“公民團結”對於現代社會共同體之發展的重要意義。
帕森斯指出,“公民權複合體”的發展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在第一個階段産生了“一種法律的或公民的框架”(a legal or civic framework),該框架“對於社會共同體和政府或國家之間的邊界關係重新給予了根本性的確定。新邊界的關鍵方面是對於公民的‘權利’的確定,對公民權利的保護成爲政府的一項重要義務”;第二個階段關注的是人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主要關涉公民的選舉權問題;第三個階段或公民權的第三個主要要素是“對於公民的‘福利’的‘社會性’關注,並視之爲一種公共責任”,他特別強調這個階段教育的普及問題。因此,
現代公民權制度的發展使得作爲社會共同體團結的某種基礎的民族(性)模式中的廣泛變化成爲可能。在早期現代社會,(社會)團結的最強大基礎存在於同民族(性)相一致的宗教、種族和地域這三種要素之中。然而,在完全的現代社會中,在宗教、種族和地域的每一種基礎上,我們都能夠發現差異或多樣性的存在,因爲公民身份的共同地位爲民族團結提供了一個充分的基礎。
不過,帕森斯進一步指出:“如果(現代社會的)多元主義基礎惡化到尖銳的結構分裂的地步,公民權和民族性的制度也會給社會共同體造成傷害。”正是對高度分化的現代社會的“多元主義”和“公民團結”的討論中,帕森斯援引了塗爾幹關於“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的思想,並對其給予了新的闡述。帕森斯認爲,塗爾幹所提出的兩種類型的團結都是通過“共同價值和制度化的規範”來描述的,但是這兩者所指涉的一般化層次是不同的。塗爾幹的“機械團結”原本描述的是一種未分化社會的團結狀態,強烈的“集體良知”(conscience collective)在一般性的層次上爲社會團結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高度分化的現代社會中,團結的這種普遍性維度仍是不可缺少的,不過帕森斯認爲“在分化性社會的社會共同體層次上,機械團結的系統之核心存在於公民權利的諸模式之中。”他沿用馬歇爾對於公民權利的三分法,以分化程度最高的美國爲例,認爲《權利法案》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憲政結構(如“第十四修正案”)爲這種普遍化的公民權利提供了最爲直接的制度性保障。
另一方面,帕森斯承續了塗爾幹對於社會分工所導致的“有機團結”的論述,並在“社會共同體”中予以了充實和發展。他認爲有機團結關涉“社會系統的各種角色、亞集體以及在功能基礎上分化了的規範這些方面”;在這種團結中,雖然共同價值模式在相關的價值具體化層次上仍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但是行動者在行動中的期待所依據的則是不同的角色(要求)和亞文化。因此,有機團結所針對的問題就是“將那些關涉可比較的功能過程的各種各樣的基礎的期望整合起來。”帕森斯進而將現代分化社會(尤其是美國)的“有機團結”問題與現代社會的“多元主義”問題關聯起來;他強調在經濟分工、政治分化以及社會與其文化指涉的關係這三個結構性背景中,有機團結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這三個領域分別産生了經濟多元主義、政治多元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尤其是宗教多元主義);而“倫理多元主義”趨勢似乎背離了機械團結所描述的那種特殊的道德一律(moral uniformality),但他認爲此處的“實質性關注點”是“共同的道德標準所位於的一般性層次”,也就是説,“如果一個多元主義的社會要將其各種類型的單位整合到一種團結性的社會共同體之中,就不能通過對於每一種地位都是具體的方式,而必須憑藉那種能夠充分普遍地適用於諸分化性單位類型的廣泛範圍的方式來界定道德義務。”

塗爾幹《社會分工論》。圖源:必應。
帕森斯此處所強調的實際上和塗爾幹晚期的一個主要努力是一致的,即不是將“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主要或完全視爲歷史序列中的兩種社會形態中的團結類型,而是視爲社會團結的兩種要素或模式,它們共存於現代社會之中;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解釋和解決現代複雜社會的團結問題。對於帕森斯來説,高度分化的現代多元主義社會仍然需要某種普遍性的共同價值基礎,現代“公民權”的普遍化發展提供的就是這種基礎,它體現的是現代社會“機械團結”的一面;另一方面,有機團結則與現代社會的多元主義相對應,體現了在普遍價值基礎(如民族認同)之上的多元亞團結類型。這兩個方面在現代社會共同體中的有機結合爲現代社會提供了主要的團結機制。
最後,尤其是在分析的意義上,帕森斯的“一般性交換媒介”理論對於他關於社會共同體及其團結功能或整合功能的闡述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前文曾經指出,對於不同層次上的“一般化交換媒介”的闡述是帕森斯中後期行動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創新和有機組成部分;這種理論圖式實際上構成了帕森斯對於不同層次的系統內部以及它們與其環境之間的交換關係的主要分析範式。
帕森斯指出:“對於一般化媒介的需要是社會結構的分化性的一個功能;在這種意義上,它們全都是部分性的整合機制。”在社會系統或社會中,與社會共同體相對應的一般化媒介是“影響(力)”;帕森斯將其界定爲“一種説服(persuasion)的手段”。在十分專門的意義上,它指的是“通過説服與某種團結群體的其他成員達成‘共識’的能力,這種説服並不需要給出充分的理由(在這種意義上,某種充分的理由就是某人爲了他本人做出一個理性的決定而給予接受者充分的資訊,或者對接受者來説至少是能夠完全理解的理由)。”也就是説,這種“説服”主要是建立在説服者的地位或者聲望的基礎上,而非通常意義上的“説服”。帕森斯認爲,對於“影響力”的功能需要關涉“在接受‘建議’(advice)(在既不存在情境性誘惑也不存在強制性懲罰的情況下試圖説服這種意義上而言的)的基礎和接受這種建議的本質上是令人信服的‘理由’之間的裂隙中搭建橋樑。”因爲在複雜的共同體中,對於所有承諾的可取性(advisability)不可能等待“完全理性的證明”,所以,它們必須依賴於影響力或者聲望。
前文曾經指出,帕森斯在其理論發展的中後期著力論述的“一般化交換媒介”圖式因其自身的複雜性以及帕森斯的意外去世而具有明顯的未完成性和不充分性,雖然這個理論圖式對於包括社會共同體在內的諸系統的闡述在分析的意義上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我們在此也只能對這個複雜問題留待另文專論。
.png)
帕森斯提出的“社會共同體”範疇並非他突發奇想的産物,這種觀念在西方社會理論傳統中具有其深厚的智識根源。不過,帕森斯對於這些智識傳統並非簡單的承續,而是將它們綜合到他所建構的一般理論框架之中。我們擬在本節對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理論受其影響較大的幾種思想進行一個簡要的類似於帕森斯所謂的“彙通性”的分析。
首先,也是最明顯的,帕森斯關於社會共同體與社會團結的論述主要稟承的是塗爾幹的社會整合理論傳統。帕森斯在爲塗爾幹百年誕辰而寫的一篇長文中,集中闡述了後者關於“社會系統的整合理論”;他認爲“塗爾幹在其學術生涯中最持之以恆地集中貫注的就是社會系統的整合,亦即是什麽將諸社會結合在一起的問題。”塗爾幹社會理論中的一些核心概念,諸如“集體良知”(conscience collective)、“集體表現”(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機械團結”、“有機團結”、“職業群體”(occupational groups)、“失範”(anomie)等莫不與其社會整合理論相關聯。正如我們在前文指出的,帕森斯特別借用和拓展了塗爾幹圍繞著“集體良知”和“機械—有機團結”概念而闡發的社會團結理論。帕森斯雖然強調了塗爾幹對於現代社會整合理論做出的重要的和基礎性的貢獻,但也認爲塗爾幹的社會整合理論存在著諸多含糊性和問題,未能提出一個明晰的分析框架(例如他在上文中就運用他所謂的社會系統的四個結構性變量圖示對塗爾幹的整合理論進行了批評和修正)。
不過,考慮到社會共同體在其社會整合理論中的重要意義,帕森斯在其關於塗爾幹理論的闡述中對後者的“職業群體”概念及相關論述的相對忽視這一事實就顯得有些令人不解,畢竟塗爾幹圍繞“職業群體”概念所闡發的現代社會團結方案和他圍繞著“社會共同體”概念闡述的現代社會整合方案頗爲相似,儘管兩者之間也存在著重要不同。
塗爾幹在其《社會分工論》的著名的〈第二版序言〉中指出,“職業群體”或“法團”(corporation)這種具有悠久歷史的團體的核心是公共精神,它能夠對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進行協調,並通過某種犧牲和克制的精神來凸現其道德屬性:“在職業群體裏,我們尤其能夠看到一種道德力量,它遏制了個人利己主義的膨脹,培植了勞動者對團體互助的極大熱情,防止了工業和商業關係中強權法則的肆意橫行。”換言之,法人團體中的生活實質上是“一種共同的道德生活”。在這個意義上講,“職業群體”似乎具有“機械團結”的功能。不過,另一方面,實際上也是更爲重要的,伴隨著社會的分工和分化的發展,職業群體及其社會團結功能面臨著諸多挑戰,它在現代分化和多元化的社會中的整合功能因此主要體現在“有機團結”方面。
.png)
塗爾幹像。圖源:必應。
職業群體的這種作用進一步體現在現代社會結構之中。塗爾幹指出,隨著社會的分化,“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遠……國家已經無法切入到個人的意識深處,無法把他們結合在一起。……如果在政府與個人之間沒有一系列次級群體的存在,那麽國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這些次級群體與個人的關係非常緊密,那麽它就會強勁地把個人吸收進群體活動裏,並以此把個人納入到社會生活的主流之中。”因此,職業群體在現代社會的一個主要問題實際上是其“重建”問題。例如,我們可以將塗爾幹的《職業倫理與公民道德》視爲這種重建的某種嘗試;正如該書標題所示:塗爾幹實際上想通過“職業倫理”(professional ethics)和“公民道德”(civic morals)這兩個不同層次的社會團結紐帶來解決現代社會中的團結與失範問題。塗爾幹指出,在現代社會中,“任何人要想生存,就必須成爲國家的公民。不過,顯而易見的是,有一類規範卻是多樣化的:它們共同組成了職業倫理。”他認爲,“職業倫理越發達,它們的作用越先進,職業群體自身的組織就越穩定、越合理。”因此,在現代工業社會中,“治療邪惡的真正辦法就是爲經濟秩序中的職業群體賦予一種它們從未得到過的穩定性”。
另一方面,塗爾幹將現代“國家”的性質確定爲“政治社會”:“‘國家’尤其是指統治權威的代理機構,而‘政治社會’指的是(由各種次級群體構成的)複合群體,國家是其最高結構。這樣一來,公民道德所規定的主要義務,顯然就是公民對國家應該履行的義務,反過來說,還有國家賦予個體的義務。”塗爾幹指出現代社會面對著這樣一對矛盾:“一方面,我們確認國家在不斷發展;另一方面,個人積極對抗國家權力的權利也同樣獲得了發展”。正是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塗爾幹提出了其著名的“道德個體主義”(moral individualism)的思想:
我們能夠理解,在國家職能逐步拓展的同時,個人並沒有消弭。我們也看到,個人的發展也不會使國家走向衰落,因爲他本身在某些方面就是國家的産物,因爲國家的活動從根本上就是要解放個人。就事實來説,歷史給出了最權威的證明,這種因果關係就是道德個體主義的進程與國家的進步之間的關係。除了我們下文將要提到的反常情況以外,國家越強大,個人就會越受到尊重。
因此,正如許多論者(包括帕森斯在內)所指出的,塗爾幹實際上充分認識到現代社會的整合或團結問題的複雜性,並試圖構建一個關涉從國家到個人、從普遍到特殊的多層次的團結或整合機制;如上文所述,帕森斯關於現代社會的整合問題的探討和塗爾幹的這個研究進路總體上是一致的。
其次,在帕森斯關於社會共同體和社會團結的論述中,他對韋伯社會理論傳統的稟承雖然不像對塗爾幹的社會整合理論的接續那麽直接和明顯,但是韋伯社會理論傳統顯然給他的相關論述提供了別樣的支持。按照人們對韋伯思想的一個常規理解,韋伯對現代性或現代社會的態度是典型的“文化悲觀主義”,他對“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過程以及“官僚制化”(bureaucratization)的分析,給人們造成現代社會就是一個“鐵籠”(iron cage)的印象。這自然是對韋伯複雜而充滿張力的理論的一種片面的理解,或者説反映的只不過是韋伯社會理論的一個方面而已。
.png)
馬克斯·韋伯。圖源:百度。
前文曾經強調,帕森斯對“社會共同體”的界定突出地強調了它的兩個方面,即“規範秩序”和“集體組織”;而在古典社會理論傳統中,無論是就其廣度還是深度而言,我們都可以説幾乎沒有人能夠超越韋伯在這兩個方面的卓越研究。不過,韋伯並沒有像塗爾幹那樣非常直接和鮮明地探討現代社會的整合或團結問題;但是這並不等於説韋伯的相關研究所要解決的不是現代社會的整合或團結問題。正如我們在本文開始論及的,帕森斯之所以將“霍布斯秩序問題”設定爲現代社會理論的主題,就是因爲這個問題指涉現代性的最實質性的問題。
不同理論家的理論視角可能會不同,表述也可能會不一樣,但在最實質的層面上,他們關注的問題是一致的。帕森斯曾經對韋伯有過這樣的評價:“對我來説,韋伯似乎是站在西方文明的整個發展的一個非常緊要的關頭。他的同時代人幾乎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理解那比較古老的系統的崩潰這種事實及其性質;而且,他對於一種新的智識取向—在對那個正在産生的社會世界的情境進行確定的過程中,這種取向很可能具有建設性的意義——的概貌的貢獻要比其他任何個人都要大。”
因此,在帕森斯對於韋伯思想的闡述中,他始終強調“規範秩序”(normative order)在韋伯理論中的核心地位。例如,前文曾經提及帕森斯對韋伯社會理論的一個重要評判,即韋伯社會學的核心關注點在於法律社會學,他對經濟和政治現象的旨趣位於這個中心點的一側,另一側則是他對宗教社會學的旨趣。
我們也曾經論及,帕森斯將“法律系統”視爲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整合機制。他認爲,“韋伯關於諸社會的分析的參照點在於合法秩序(legitimate order)的概念中。他將合法性概念本身的基礎置入行動者的信念或構念(conception)之中。”他雖然認爲韋伯的法律社會學探討也存在著某些缺陷,但是他對韋伯的法律社會學思想的贊同似乎要比任何一位法學家都多得多。同樣,他認爲韋伯的宗教社會學關注的焦點是“宗教觀念及承諾與人類行動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一個社會內部的人類行動的經濟特徵之間的關係”。換言之,韋伯關於宗教社會學的研究是他對人類社會的“規範秩序”探討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更爲重要的是,帕森斯認爲構成韋伯思想之內核的“意義問題”(problem of meaning)就植根於宗教領域。
帕森斯指出,“意義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即“在規範秩序中被制度化的期望系統與人們所遭受的實際經歷這兩者之間的整合與差異”是“韋伯整個思想的一條主要線索”。此問題的旨趣在於“人們將什麽解釋爲對他們而言以及對於他們所依附的人類境況的諸方面來説的諸後果,以及與某種已經確立的規範秩序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問題”。上述等等,包括韋伯對經濟和政治問題的研究,無不體現出他對現代社會的整合問題的獨特探討。
至於韋伯對人類社會中的諸組織形態的研究,更是後來者很難超越的成就。韋伯在其經濟史以及宏大的歷史—比較研究中對人類歷史上包括官僚制組織在內的複雜組織形態進行了卓著的探討。韋伯這些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遠非本文所能澄清,我們下麵僅僅提及他的相關研究中與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概念具有密切關聯的兩個方面。前文曾經論及帕森斯通過其社會共同體範疇而展開的對現代社會的整合或團結問題的論述中,“公民權”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恰恰在這個方面,韋伯對西方的公民和公民權的歷史産生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彌補塗爾幹的社會整合理論在這個方面的相對缺失(至少是一個明顯的薄弱環節),另一方面也可以爲帕森斯對現代社會中“公民團結”論述提供廣泛而堅實的社會史基礎。
韋伯認爲,現代西方的“公民”和“公民權”實際上産生於中世紀的“城市自治體”(city-commune),而這種作爲一種大量或普遍出現的現象的“城市自治體”只存在於西方。現代西方的“公民”實際上是中世紀“城市自治體”中的“市民”(burgher)演化而來。韋伯指出:“按照社會史中的用法,公民權(Burgertum,citizenship)這個概念與下麵三種不同的指涉密切相關:第一,公民身份,可能包括某些具有某種特殊的共同利益或經濟利益的社會類型或社會階級。……第二,在政治的意義上,公民資格意味著國家中的成員資格,它蘊涵有這種成員作爲某些政治權利的持有者這樣的含義。最後,在階級的意義上,公民指的是那些不同於官僚階級或無産階級以及在他們的圈子之外的階級的階層,我們可以將它們理解爲‘擁有財産和具有文化的人’,亦即企業家、食利者以及大體上所有那些具有學術文化、某種特定的生活標準和一定的社會聲望的人。”當然,韋伯強調只有在西方才會發展出上述citizenship的概念。
另外一個方面是韋伯對於基督教“教會”(church)和“教派”(sect)的論述。韋伯於1904年借參加美國聖路易斯世界博覽會期間舉行的“世界兿術與科學大會”之機對這個“新世界”進行了爲期三個月的旅遊和考察,作爲這次訪美的一個成果,韋伯在1906年發表了名爲〈北美的“教會”和“教派”〉的文章,韋伯在去世前將該文予以改寫和擴充,並以〈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名置於其《宗教社會學文集》第一卷。韋伯對“教會”和“教派”這對概念進行了區分:“教會將其自身視爲一種‘制度’(Anstalt),是那些一出生就加入其中並成爲它努力的對象(大體説來,這必定成爲它的‘職責’)的那些個體之靈魂拯救的某種神聖的捐贈基金會(divine endowed foundation)。相反,一個‘教派’(此處所使用的這個術語是特別創造出來的,而且不會被我們正在討論的那些教派所使用)是一個純然建立在個體的宗教資格的基礎上的個體的自願性共同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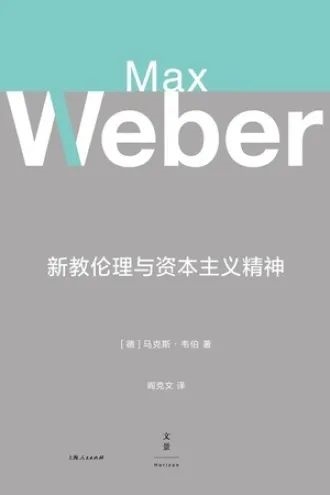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圖源:豆瓣。
韋伯後來更加明確地指出:“實際上,教會是一種法團(corporation),它就像一個捐贈基金會,組織恩典和管理宗教性的恩賜之物。一般而言,人們加入教會是強制性的,因此不能證明與成員資格相關的任何東西。然而,一個教派則是一種自願聯合體,加入這個聯合體的人僅僅是那些依據原則在宗教和道德上合格的人。如果某人發現通過宗教性的查驗(probation)後他的成員資格得到人們自願地認可,他就會自願地加入教派。”也就是説,“教會”具有明顯的“先賦”色彩,而“教派”顯然是一個“成就性”或“自致性”組織。韋伯在其美國之行中親身體會到“教派”以及它的各種世俗化形式(俱樂部、各種自願聯合組織等)在美國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另外,韋伯在1910年德國社會學學會上的演講的後半部分特別強調了“自願聯合生活”(Vereinswesen/voluntary associational life)的重要意義,這種強調依然來自美國的經驗;其主旨同樣是強調美國的各種自願聯合組織在國家、社會和個人生活中的關鍵作用。
韋伯的這幾個文本所強調的一些要素,諸如聯合性、自願性和自致性以及道德性等特徵,和帕森斯對社會共同體的相關論述極爲一致;而且,從“教派”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例如,信任作用)來看,這種共同體顯然是一種整合性的共同體。韋伯在這些文本(在西方韋伯研究中,這些文本相對被忽視)中表達了一種和他對理性化及官僚制化的論述迥然不同的思想,這對於我們全面、準確地理解韋伯關於現代性的論述極爲重要;限於篇幅,不再展開論述。而作爲一個典型的清教徒,帕森斯在其早期就已經關注到韋伯和特洛爾奇(Ernst Troeltsch)等人對基督教組織的特徵及其在西方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意義的論述,我們完全可以説這種智識傳統早已融到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理論之中。
因此,韋伯的理論傳統和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理論具有非常廣泛和密切的關聯;不過,因爲種種原因,帕森斯並未能將韋伯理論中的諸多相關論述充分的融入他對社會共同體的分析圖式之中。就其理論的廣度和深度而言,韋伯的相關研究對於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理論的潛在的重要性事實上要比塗爾幹的相關論述更爲重要,而且是後者的重要補充。
第四,從古典社會理論的另外一種主要傳統,即馬克思傳統中開闢出來的關於社會整合或團結的論述與帕森斯所承續的塗爾幹(乃至韋伯)傳統形成了鮮明對照。帕森斯顯然明白其中的差異,不過(和西方諸多理論家一樣),他對馬克思社會理論的理解和定位或多或少是成問題的。
衆所周知,馬克思社會理論的一個主要方面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二元階級結構的分析和強調,而這種結構又根植於資本主義或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之中。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馬克思是不會相信資産階級社會理論家(如塗爾幹)所闡述的那一套社會整合或團結的機制的;相反,他對社會團結的論述以他所謂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階級結構爲基礎,也就是説,馬克思的相關論述是一種“階級團結”(class solidarity)。但是,這種團結並不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它首先需要培育明確的、普遍性的“階級意識”;不過,這種階級意識不是要與現存的秩序相協調,而是要“再造一種新秩序,即馬克思所説的一種新型的生産關係;而這樣一種徹底翻新的生産關係,則必須籍由階級意識所造就的具有組織性和團結性的社會行動來實現,即通過社會革命來實現。因此,從根本上説,這樣的團結實際上是一種否定性的團結形態(negative solidarity),團結是作爲社會進步的否定性環節而得到規定的,而且是爲特定的社會階級規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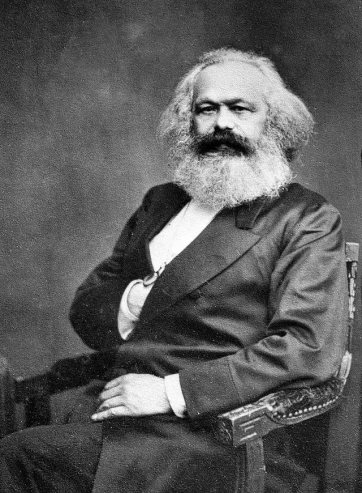
馬克思像。圖源:搜狐。
在上述“革命性”的視角下,馬克思對現代社會諸多重要問題的論述和西方主流的社會理論傳統(如塗爾幹和韋伯)都判然有別。他對“公民權”的論述就是顯著的一例。例如馬克思在其早期重要文章〈論猶太人問題〉中對一般性的“人權”(rights of man)與政治權利或“公民權”(rights of citizen)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他指出:“不同於droits du citoyen(公民權)的所謂人權(droits de l’homme)無非是市民社會的成員的權力,即脫離了人的本質和共同體的利己主義的人的權力。”諸如法國1793年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所宣稱的平等、自由、安全、財産等權利。政治權的“內容就是參加這個共同體,而且是參加政治共同體,參加國家。這些權利屬於政治自由的範疇,屬於公民權利的範疇”。這樣一來,就産生了:“尤其使人不解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公民生活、政治共同體甚至都被致力政治解放的人變成了維護這些所謂人權的一種手段;這樣一來,citoyen(公民)就成了自私homme(人)的奴僕;人作爲社會存在物所處的領域還要低於他作局私人個體所處的領域;最後,不是身爲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爲bourgeois(市民社會的一分子)的人,才是本來的人,真正的人。”因爲在馬克思看來,作爲公民的人所體現的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類存在”,而作爲市民社會成員所體現的則是一種具有特殊性的自私自利的個人性存在。
現在,特殊性淩駕於普遍性之上!馬克思認爲這是一個“謎”:“爲什麽致力政治解放的人本末倒置,把目的當成手段,把手段當成目的?”馬克思對現代“人權”和“公民權”的批判雖然帶有明顯的古希臘色彩,但他絕非一個懷舊者,他的批判是面向未來的:“只有當現實的人同時也是抽象的公民,並且作爲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人勞動、自己的個人關係中間,成爲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當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
因此,馬克思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和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雖然在某些方面頗爲相似,但是其理論取向完全不同:一個是未來的目標,另一個則是歷史進化的産物;不過,就其規範性特徵而言,兩者顯然是一致的。
最後,塗爾幹、韋伯、帕森斯分別圍繞“職業群體”、“教派”(更廣義上講,自願聯合組織)和“社會共同體”概念展開的論述以及針對現代社會整合問題提出的方案,實際上是對藤尼斯關於“共同體”(Gemeinschaft)和“社會”(Gesellschaft)的二分法的超越。

滕尼斯像。圖源:新浪網。
藤尼斯的“共同體—社會”二分法基本上屬於一對關於社會關係、社會形態或社會類型的“理想類型”概念。作爲霍布斯研究專家,藤尼斯深受霍布斯思想的影響,他的這種二分法類似於“自然”和“人爲”的區分:“共同體”是一種建立在自然基礎上的群體,“社會”則是一個“人造物”(artifact);“共同體”是自然的、有機的、古老的,而“社會”則是人造的、機械的、新近的。另外,這種二分法與他對“人類意志”的區分,即“自然/本質意志”(natural or essential will)和“理性/任意意志”(rational or arbitrary will)相對應,前者是“人的身體的心理上的對等物;它是生命的統一原則”,後者則是“思想本身的産物”。
藤尼斯認爲人類意志的相互作用形成複雜的社會關係,從而形成諸社會形態:人類意志處於相互關係之中,“就關係本身(社會聯結[social bond]就源自於它)而言,人們可以將其設想爲要麽是具有真實的有機生命,這就是共同體的本質;要麽是存在於人們心智中的一種純粹的機械構造物,這就我們所認爲的社會的本質。”在某種(甚至更爲實質性的)意義上,藤尼斯的這一對範疇指涉的就是兩種社會團結的類型。
不過,藤尼斯的論述和塗爾幹的社會團結類型在理論取向上恰恰相反:“在共同體中,成員的相互依賴關係非常緊密,社會關係形成一個極其稠密的網絡,家庭是組織的基本形態。現代社會的關係,實際上是通過契約關係和交換關係確立起來的,因此,社會團結的基礎必定會被範圍越來越大的地域流動、城市的興起以及大規模的産業結構所削弱。著意味著,隨著文明化進程的展開,個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反而抽象性越強、越疏遠,實際上陷入一種霍布斯意義上的社會敵對狀態,即藤尼斯所謂的‘無條件的自我確認’(unconditional self-affrmation)及‘無限制的經濟競爭’(unfettered economic competition)。”因此,藤尼斯和馬克思對現代“社會”都持批判的態度;不過,“藤尼斯不同意馬克思所説的通過無産階級確立新型的團結而創造出一個新型社會的見解,他認爲由團結形成的階級鬥爭實際上只能破壞社會本身,唯有復興共同體的組織結構,才是現代組織的真正出路。”
衆所周知,藤尼斯的這種二分法對現代社會(學)理論影響深遠。韋伯、塗爾幹和帕森斯對藤尼斯的論述都十分熟悉,並依據各自的理論圖式對這種二分法提出過不同的評價。不過,雖然存在著評價上的差異,但是他們在對藤尼斯思想中對於現代性或現代社會的一種較爲明顯的價值判斷——人們稱這種價值判斷或態度乃至情緒爲對於過去的“懷舊”或“鄉愁”(nostalagie)情結,帕森斯稱之爲“共同體浪漫主義”(Gemeinschaft romanticism)——都持鮮明地不贊同立場。真正的“現代性的理論家”,既不會對過去懷抱著某種懷舊、感傷的浪漫主義情懷,也不會對人類社會的未來持盲目的樂觀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講,將“文化悲觀主義”和“新進化論樂觀主義”(neo-evolutionary optimism)這樣的標籤分別貼在韋伯和帕森斯這樣的理論家的身上,顯然是某種獨斷或片面的做法。直面現在和當下,力求準確診斷現代社會的問題並積極尋求解決方案,這也許是真正的現代性理論家共同的立場;馬克思、塗爾幹、韋伯和帕森斯(儘管馬克思和其他三人的理論取向具有明顯的不同)這些社會理論家的理論探索也許就是對上述立場的真實注解。
.png)
前文指出,對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理論的忽視是在西方帕森斯研究中一個非常明顯的缺陷;不過,也有一些帕森斯理論的研究者認識到社會共同體理論對於帕森斯整體理論的重要意義,而且他們的相關闡述不僅僅限於對帕森斯的相關論述本身,而且試圖闡明這種理論圖式對於當代社會學的研究主題的意義以及與之相結合的可能性。
大體上講,這些論者對待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理論的研究態度或取向可分爲兩種類型:一種可稱爲建設性的,即以帕森斯本人的相關論述爲基礎,在澄清帕森斯本人的相關論述和指出其不足的同時對其予以補充、修正或推進,維克多·利茲、烏塔·格哈特以及朱塞佩·肖蒂諾等人的相關研究就屬於這種類型;另外一種可稱爲批判性的,即認爲帕森斯關於社會共同體的概念及相關論述是成問題的,而且不適合當前的社會學分析,因而需要以某種新的範式取代帕森斯的理論圖式,這方面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傑弗裏·C·亞歷山大。就目前的研究狀況而言,前者處於主流地位,而且顯然更爲重要。本節不擬對這些相關研究進行細緻討論,而主要關注這些論者指出的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理論與當今社會理論研究中的兩個重要主題,即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關聯。
就帕森斯關於社會共同體的論述而言,它與“公民社會”的關聯性似乎頗爲明顯;如前文所述,在帕森斯對社會共同體的論述中,“公民權”和“民主”等構成了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而這也恰恰是公民社會話語中的核心內容。不過,考慮到“公民社會”範疇在西方思想史和社會史中的複雜關聯以及它在當今的相關研究中的複雜背景和意涵,要確立兩者明確的關聯性也並非易事。
首先,許多論者都注意到1980年代後期以來人們圍繞“公民社會”進行的爭論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背景(如東歐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潰敗)。例如,卡維拉傑(Sudipta Kaviraj)和基爾納尼(Sunil Khilnani)指出,當代關於“公民社會”的討論至少存在著三個可以確定的方面:第一個方面涉及“後共産主義社會中的社會組織以及它與國家的關係應當是什麽”的問題;二是某些激進理論家在對社會主義觀念幻滅之後,期望“通過重新籲求公民社會的觀念對民主觀念予以激進化”,他們批評“福利國家”制度、援引“英國多元主義傳統”、要求復興“公民社會中非國家組織的聯合性的主動精神(associative initiatives)”;三是“對(西方)新的社會運動的理論論證”。其中的前兩個方面分別針對“共産主義中央集權制(statism)的肆無忌憚”和“資本主義的原子化”。
其次,civil society這個概念在西方思想史—社會史上的演變及其涵義也是頗爲複雜的問題,或者説是至今也未達成相對共識的問題,不同論者在援引這個概念時依然缺乏較爲明確和統一的標準。例如,泰勒(Charles Taylor)依據西方政治理論史提出了關於“公民社會”的三種觀念:(1)在最起碼的意義上,公民社會存在於有自由社團之處,而不是處於國家權力的監護之下;(2)在較強的意義上,公民社會只有在作爲整體的社會能夠通過獨立於國家監護之外的社團來組織自身並協調自身行爲這樣的地方才存在;(3)作爲第2點的替代或補充,只要各種社團的整體能夠舉足輕重地決定或者轉變國家政策的進程,我們就能夠談論公民社會。
席爾斯(Edward Shils)則較爲明確地指出,civil society的觀念具有三種主要成分:一是“一個包含著一套區別於家庭、氏族、地域和國家的經濟的、宗教的、智識的和政治的自主制度的社會”;二是“一個擁有在國家和一組獨特的制度之間的某種特殊的關係複合體的社會,這組制度捍衛著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分離並維持著兩者之間的有效紐帶”;三是“一個具有有教養的或文明的風尚的社會”。席爾斯認爲,第一種要素一直被視爲公民社會;人們有時也把具有上述特徵的“整個包容性的社會”視爲公民社會。當今的某些相關研究中,civil society則被等同於和政府、市場相並列的“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
相反,如上文所述,帕森斯明確地將“社會共同體”界定爲“社會”或“社會系統”的一個整合子系統,對其內部結構、外部環境等都做了明確論述,並且提出了一個明確的分析框架。因此,無論是就其歷史演變、概念內涵還是其當下應用等方面,“公民社會”都不能與“社會共同體”相等同。不過,考慮到這兩個概念在諸多指涉上都有明顯的關聯,因此,某些研究者試圖在兩者之間建立某種聯結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例如,格哈特在其專論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理論的文章中,對帕森斯關於公民權的論述與當今某些研究者對於“公民社會”的研究進行了比較,並指出帕森斯的相關論述對於當今的“公民社會”研究的意義。公民社會也是傑弗裏·亞歷山大在1990年後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他的研究因其具有明顯的帕森斯式理論色彩而與諸多相關研究不同。例如他在其關於civil sphere的最新論著中提出了他所謂的“公民社會”的三種類型(civil society I,civil society II和civil society III)的觀點;其中的前兩者分別來自西方政治理論史中的英國傳統和德國傳統,並將第三種類型“設想爲一種團結的領域,其中,某種類型的普遍化的共同體是通過文化來確定的,並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制度而強化”;他雖然沒有注明這種界定的智識根源,但這種論述顯然源自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概念。
帕森斯顯然熟知“公民社會”這個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但他並未明確地使用該範疇,反而創造出“社會共同體”這個概念;這也許和我們剛剛論及的原因有關,也許兩者本來就是不同的範疇。不管怎樣,相對於當今的公民社會研究的混亂狀況,帕森斯關於社會共同體的分析應當是一種極爲重要的參照系。不過,帕森斯顯然不熟悉他去世近十餘年之後才盛行的“全球化”話語;但格哈特認爲,帕森斯在1960年代關於“國際秩序”或“全球性的社會共同體類型”(worldwide type of societal community)的論述不僅和當今的全球化研究密切相關,而且頗具意義。
格哈特指出,與全球化的非預期後果和民族主義相關涉的當今全球化研究的這兩個極爲重要的視角,都能夠與帕森斯的相關論述聯繫起來。帕森斯的相關論述的背景是“二戰”後愈演愈烈的兩大政治陣營之間的“冷戰”。前文曾經指出,帕森斯早期將蘇俄共産主義/社會主義視爲(和法西斯主義相類似的)對西方現代性的一種威脅;但是在1960年代,他似乎將其著名的“彙通性”分析運用到“冷戰”背景中的國際關係領域,尋求“國際秩序”或國際整合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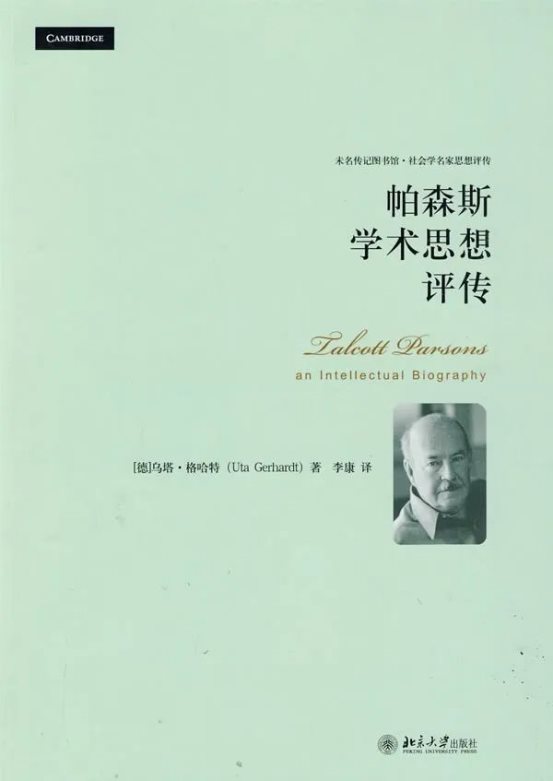
格哈特《帕森斯學術思想評傳》。圖源:百度。
例如,他在如下四個領域中發現,在這“兩極分化的巨型系統”(polarized megasystems)之間隱約可見“初步的共通性(communality)”,這四個領域是:包括經濟繁榮和政治自由在內的“一組共同價值”、國際法中已確立的“規範”、(不論是通過“龐大的控制等級”還是“多元主義的[子]系統的多重性”的)“利益的表達”以及“意識形態”。換言之,帕森斯認爲東、西兩大集團的長期對抗實際上也是一個分化和整合的過程。
格哈特指出,帕森斯在相關論述中實際上提出了兩個假定:一是“在當時兩極分化的東—西格局中的國際化(聯合國爲其提供了一個論壇),能夠促使世界分化爲比以往更加多元化的諸領域”;二是“與此同時,共産主義的和西方的體制都對珍愛諸如普遍的自由和平等這樣的價值的多元主義給予高度的尊重,這種多元主義能夠在所有國家強化對於人權的規範性承諾,從而將全世界聯結在一起。”帕森斯以社會共同體爲核心的社會整合機制實質上是一種“不同而和”的機制;換言之,它是一種建基於分化之上的整合機制。這樣的機制既可以適用於微觀層次上的群體,也可適用於宏觀層次上的國家之間以及國際組織之間的整合。
鑒於此,格哈特認爲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理論範式“可以極佳地用來理解”1990年代以來(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化和公民社會這些當代最重要的論題(這些論題恰恰是社會學必須應對的並應當有所貢獻的領域),而且可以將這兩個論題融入同一個理論之中。因此,
只有在今天,在關於普遍存在的民主制度的“一個世界”的全球性熱望中,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觀念才顯示出其真正的價值。帕森斯在世期間,他關於社會共同體的概念化中存在著的某些表面上看起來不必要的複雜原則,可能曾經表現出過分的“學究氣”。然而,在今天,帕森斯對社會共同體的分析對於在一個多元主義的、多元文化的社會中的整合問題提供了某種答案,這是一種涉及同當今世界相一致的理論的解答。
.png)
在帕森斯的整個理論系統(或一般意義上的四功能範式)中,主要履行整合功能的(子)系統實際上處於核心地位:在人類境況系統中,(人類)行動系統居於核心地位;在一般行動系統中,社會系統居於核心地位;在社會系統中,社會共同體則居於核心地位。因此,帕森斯關於(尤其現代社會中的)整合問題(並非僅限於社會層次)的論述實質上構成了其整個理論探討的重心。整合功能雖然在“控制論等級”中並不居於(資訊維度的)最高層次,但是一般性價值必須具體化爲規範層次才能夠被“制度化”,並因此才能夠實現其潛在的模式維持功能。另一方面,個體人格層次上的社會化或內化也必須與規範、組織、制度這一層次相關聯並通過它們而與更高的價值層次相連接來實現;換言之,個體是在社會共同體的生活中來完成其社會化、塑造其人格的。
因此,諸如前文指出的,“制度化”和“內化”構成了帕森斯的行動系統理論中的兩個基點;也正因如此,帕森斯一直將源自塗爾幹的“制度化個體主義”作爲其基本的理論立場,而制度化個體主義的實質意涵就是將制度化與內化統一起來,將個體(人格)、制度(規範)以及一般(或普遍)價值三個層次統一起來,將強調個體自由或自主的個體主義與強調社會整合或團結的制度化機制統一起來。他所提出的社會共同體概念及相關論述就是其“制度化個體主義”立場的典型而集中的體現;而社會共同體理論圖式所要解決的實質性問題的理路就蘊涵在這種立場之中。
另一方面,帕森斯關於整合問題的論述是建立在分化的前提之上的,而非衝突論者或激進理論家們所指責的那樣是一種對均衡的靜態研究。換言之,沒有分化就不會有整合問題。同時,伴隨著社會演化過程的不僅有分化過程,也存在著反分化或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過程,因此,“某個社會共同體發揮作用的過程不是一種既定的而是不確定的實現(過程)”。正如帕森斯將“規範秩序”確定爲一種動態的“問題”而非靜態的“理想”一樣,這背後指涉的就是帕森斯意義上的“意志論的行動”。
在帕森斯的整個著述中,始終洋溢著一種積極、能動的樂觀情懷,這也許就是“作爲最後的清教徒的社會學家”的帕森斯想要向世人表達的一種精神。正是這種情懷或精神使得帕森斯的著作及其闡述的理論在現代社會理論中獨樹一幟。肖蒂諾在論及帕森斯關於現代社會中的多元主義的論述時,認爲他的理論立場一方面與“保守主義思想的懷舊眼界”明顯不同,另一方面又與“批判理論的悲歎”判然有別:
在其他人看到某種共同文化傳統瓦解爲具有高度專業化的、狹隘地發展起來的趣味的諸碎片(fragments)的地方,帕森斯強調的是某種複雜精深的規範秩序的發展,其中,對於共同成員資格的要求與特殊主義的諸傳統所施加的遵從壓力區別開來。在其他人將部門性的(segmental)忠誠確定爲對於“民族性的”社會共同體的統一性的一種危險的地方,帕森斯強調的是這些網絡(一旦被嵌入普遍主義的個體權利之中)是如何成爲民主社會中的力量和靈活性的一種根源的。在其他人哀歎“公益(common good)的終結”的地方,帕森斯卻識別出關於“從先賦性和強制性的效忠中解放出來的自由”的具有高度制度性的前提。在其他人看到道德秩序最終敗壞的地方,帕森斯看到的卻是某種多元主義的社會共同體的浮現,這種共同體與經濟控制、政治權力以及文化強制共同存在著,但是在分析的意義上與它們相獨立。
文字编辑:高雅馨、张歆泽、吕灵
推送编辑:李金瑶、罗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