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立瑋:社會共同體與社會團結——帕森斯探討現代社會整合問題的路徑(上)
趙立瑋
(中閾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摘要:帕森斯在1960年代中期明確地提出了社會共同體概念以及以之爲核心的理論分析圖式,從而構成了他中後期探討現代社會中的社會整合或團結問題的主要範式。雖然該範式是帕森斯對社會理論中的社會整合或團結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但在西方帕森斯研究中該分析卻長期受到忽視。本文試圖在闡明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觀念的基礎上,緊扣社會共同體與社會團結的關係這一核心問題,溯及它與塗爾幹、韋伯等古典社會理論家的智識根源,並結合近期的一些相關研究指出它與公民社會以及全球化這些當下的重要論題相結合的可能性及其意義。
.png)
“社會共同體”(societal community)是帕森斯中後期理論發展中的一個具有關鍵意義的範疇。和帕森斯社會理論的其他許多重要概念一樣,“社會共同體”觀念一方面具有其理論(尤其是古典社會理論)淵源,另一方面又和他在其長達半個世紀的理論生涯中所建構的“一般理論”(框架),即“一般行動理論”(general theory of action)的諸多方面具有複雜和密切的關聯,構成了這個分析框架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將這兩個方面統一起來的是它(們)共同面對的現代性問題。肖蒂諾(Giuseppe Sciortino)指出:“帕森斯對社會共同體的分析是他對當代社會結構之分析的努力的基石,也是他對歷史進化的闡釋的基石。這個概念對於他的社會整合理論而言是至關重要的,自《社會行動的結構》以來,帕森斯就將後者確定爲社會學的研究範圉。我們也可以將他後期努力發展的社會共同體觀念視爲對他自1930年代晚期以來一直從事的經驗研究——諸如宗教及種族多元主義的重要意義、聯合性團體的結構特性、與現代化過程相關涉的諸極化(polarizing)趨勢(以及能夠防止它們的那些具有破壤性的外在性(externalities)不斷增加的機制類型)和教育革命的範圍與影響力——的諸方面予以綜合(以及改進)的一種途徑。”
實際上,“社會共同體”範疇在帕森斯“一般行動理論”(以及更爲一般的,“人類境況”[human condition]範式)中的關聯要比肖蒂諾指出的情形更爲複雜。不過,帕森斯生前雖然對“社會共同體”的概念有過明確而系統的闡述,但它關涉的某些重要方面因帕森斯的意外去世而不夠充分和有待發展。雖然如此,對“社會共同體”及相關思想的忽略依然是西方帕森斯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缺陷。”本文試圖在聞明帕森斯的“社會共同體”觀念的基礎上,緊扣社會共同體與社會團結(或社會整合)的關係這一核心問題,溯及它與塗爾幹、韋伯等古典社會理論家的相關思想的關聯性,並結合近期的一些相關研究指出它與公民社會以及全球化這些當下的重要論題相結合的可能性及其意義。
帕森斯社會理論的奠基之作《社會行動的結構》(以下簡稱《結構》)的開篇頗富意味。他將全書“導論”的第一小節稱之爲“問題”,而“問題”出在哪兒呢?全書開篇引用的英國學者布林頓(Crane Brinton)的一段話已開宗明義:問題與英國19世紀最知名的社會理論家赫伯特·斯賓塞有關。爲什麽是斯賓塞而不是其他人?而“斯賓塞的理論已經過時了”,那麽是“誰摧毀和怎樣摧毀他的理論的?”帕森斯認爲這就是問題之所在。帕森斯接下來對此問題進行了簡要而深入的分析。準確地講,問題的根子還不在斯賓塞的身上,真正成問題的是他作爲其晚近發展階段的一個典型代表的“實證主義—功利主義傅統”。這個傳統主宰了西方(尤其是歐洲)社會思想數個世紀,但隨著這種理論傳統在斯賓塞時代發展到“頂峰”,對其表示置疑和批判的人也越來越多。
在醖釀和寫作《結構》的近十年的時間裏,帕森斯對於其《結構》一書的主角和作爲他日後理論發展中最主要的對話者的馬克斯·韋伯和埃米爾·塗爾幹的思想已經是非常熟悉,而這兩人都將對於上述傳統的批判作爲其理論發展的起點。帕森斯認爲韋伯和塗爾幹就是屬於那些認爲“當代社會正處於或者接近轉捩點”的少數社會理論家之一。換言之,西方社會思想傅統正處於“危機”之中:“在對某些最重要的社會問題的經驗性解釋領域裏,一場根本性的變革正在進行中。線性進化論已被人們遺忘,各種循環論則嶄露頭角;各種各樣的個人主義正受到越來越猛烈的抨擊,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和有機的理論。作爲一種行動要素的理性的作用和科學知識的地位則一再地受到抨擊;我們再次被不同種類的關於人性和人類行爲的反智主義的(anti-intellectualistic)理論浪潮所淹沒。除非追溯到16世紀,否則很難在一代人這麽短暫的問隙裏發現關於人類社會的那些流行的經驗性解釋發生了一場如此重大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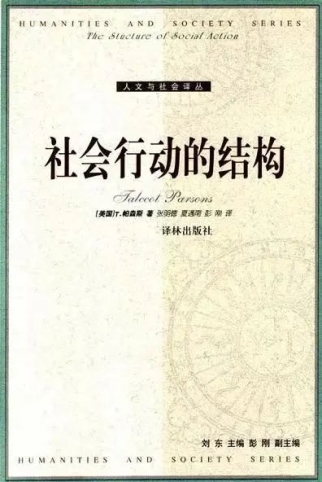
《社會行動的結構》。圖源:百度百科。
危機不僅表現在思想或智識的層面,而且在社會層面上更爲顯著和更加劇烈地呈現出來。帕森斯後來在回顧其理論發展時談到他寫作《結構》時的社會狀況:“(當時)西方社會的狀況也許既不能稱爲資本主義,也不能稱之爲自由企業(free enterprise);而在政治方面也不能稱其屬民主制度;因此,它雖然處於某種危機狀態之中。自我的大學時代以來,俄國革命以及被共産黨控制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突現對於我的思考一直具有關鍵性的意義。法西斯主義運動對(我)在德國的友誼産生了影響:《結構》這部著作出版不到兩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最後,是大蕭條及其在整個世界的蔓延(對我的思想産生的影響)。”換言之,《結構》誕生於一個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帕森斯視爲西方文明之威脅的)蘇俄社會主義、大蕭條、法西斯主義以及迫在眉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等“災難性事件”爲標誌的西方社會陷入全面危機的時代。不過,面對西方文明遭遇的這雙重危機,帕森斯並不是像斯賓格勒那樣哀歎“西方的沒落”,而是在“危機”中尋找“轉機”的可能性。
自其學術生涯伊始,西方現代性的命運就成爲帕森斯關注的核心問題。例如他在其博士論文中通過對馬克思、韋伯和桑巴特的相關論述的考察而對“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問題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在《結構》中,他通過對馬歇爾、帕雷托、塗爾幹以及韋伯的思想的著名的“彙通性”(convergence)分析,澄清和發展了他自己關於“西方社會的狀況的諸問題”(這也是這些理論家論述的問題)的思考。帕森斯後來在闡述塗爾幹的“社會系統的整合理論”時指出,塗爾幹最初的理論取向有兩個“實質性的參照點”:一個是肯定性的,即“把孔德式的“共識”(consensus)概念作爲諸社會中的統一性的焦點;另一個是否定性的,即功利主義關於“互不關聯的個人利益的相互作用”(interplay of discrete individual interest)的概念,這是斯賓塞首次提出的,他將工業社會設想爲某種“契約關係”的網絡。這種説法也大致適用於帕森斯本人;所不同的是,帕森斯的“否定性參照點”不僅僅包括實證主義——功利主義傳統,而且(較爲次要的)包括德國的觀念論傳統,而他的“肯定性參照點”也要廣泛得多,即他在“四位歐洲理論家”的思想中發現的“彙通性”。
具體來説,以“功利主義”爲例,他認爲這種思想體系自其開創者霍布斯以來,就一直未能令人滿意地解決“社會秩序問題”;而這個問題恰恰是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當社會思想大約在17世紀變得世俗化時,它的中心問題就是社會中的秩序基礎(問題),並特別通過下述形式表現出來,即個體自由領域從與國家的強制性權威相關聯的專制控制下解放出來。”由於實證主義和功利主義在西方社會思想傳統中長期佔據支配性地位,從而導致(當然不是唯一因素)上文提及的西方文明在思想和社會兩個層面上的雙重危機。而他通過“𢑥通性”分析而得出的“意志論的行動理論”(volu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則爲解決他所謂的“霍布斯秩序問題”奠定了比較堅實的理論基礎——當然,在更具實質性的層面上,帕森斯意圖通過《結構》中的探討爲重建西方文明奠定理論基礎。因此,帕森斯在《結構》中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在西方諸(社會)行動理論傳統中將“秩序問題”(因此凖確地説是“行動和秩序”)確立爲現代社會理論的主題。他在此後數十年的理論生涯中所建構的“一般理論”框架(包括分析圖式和實質理論)就是圍繞著這個主題展開的。本文所要討論的帕森斯的(最後)以“社會共同體”爲核心的社會整合理論就是他關於現代社會中的“秩序問題”探討的核心部分,”當然也必須將它置於這個問題域中才能把握其真意之所在。
.png)
自早期開始,帕森斯就試圖確立社會學的研究範圍及其學科地位,而這個問題顯然與他對現代社會的整合問題的思考密切相關。因此之故,帕森斯在其前期的兩部重要著作(也是他最具影響力的兩部著作)《社會行動的結構》和《社會系統》(以下簡稱《系統》)的結尾部分,討論的都是行動科學(sciences of action)的分類問題,不過其著眼點顯然在於社會學的學科地位問題。雖然主題相同,但是這兩種相隔十餘年的論述之間卻存在著某些差異,體現了帕森斯理論思考和理論建構的若干進展和變化。
帕森斯在《結構》最後一章的最後兩節近20頁的篇幅裏討論了行動科學的分類問題。他首先將“歷史科學”和“分析科學”區分開來,前者以理解具體的“歷史個體”爲要務,後者的目的則在於“發展出邏輯一致的一般分析理論體系”;並進一步將分析科學劃分爲三大類理論系統,即自然、行動和文化系統,其中的前兩類系統可歸爲“經驗科學”,因爲它們關涉的是“時問中的諸過程”,而文化系統則既非空間性的也非時間性的;他再進一步將“經驗性的分析科學”分屬“自然科學”和“行動科學”兩大類。帕森斯在《結構》中對單位行動(unitact)的分析屬於最基礎性的分析,亦即對行動系統的諸基本要素的分析;但是,“就其本身而言,單位行動的諸基本特性並不構成一門獨立的分析科學的(研究)主題。毋寜説,它們構成了所有行動科學共同的方法論基礎。”也就是説,對單位行動的分析構成了所有行動科學的一個共同的參照框架,亦即“行動參照框架”(action frame of reference)。行動科學或行動理論的主要任務在於利用這個參照框架去分析行動系統的諸“突生特性”(emergent properties)。 這樣,行動科學的分類原則就是依據“一般化的行動系統的何種結構性要素或要素群構成所要探討的(行動)科學的關注焦點”來予以分類。換言之,行動系統的不同要素或要素群總是與行動系統的某些“突生特性”相關聯,這些“突生特性”正是諸行動科學研究的主題。
因此,“經濟合理性”、“權力關係”、“共同價值整合”(common-value integration)以及“人格”這些行動系統的“突生特性”就分別成爲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研究主題。另外,帕森斯還提及與行動中的手段——目的關係相關的一組“技術學”(technologies),作爲行動科學的第五個分支。帕森斯特別強調了社會學的學科定位問題。他將社會學界定爲“一門試圖發展出某種關於諸社會行動系統——就這些系統能夠借助於共同價值整合的特性來予以理解而言——的分析理論的科學。”在上述行動科學分類體系中,社會學是“一門與經濟學處於相同層次的特殊的分析科學”。因此,帕森斯反對過去(如韋伯)將社會學界定爲一門(相對的)歷史科學或綜合性的分析科學(將經濟學、政治學等包括其內)的觀點。
帕森斯在《系統》一書最後作結的一章再次以20頁的篇幅專論了上述問題,並以“社會學理論在諸分析性的行動科學中的地位問題”作爲該章的標題。雖然論及的依然是“行動科學”,但是帕森斯的看法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變。帕森斯在《系統》的“前言”中指出,應當將他與席爾斯(Edward Shils)合著的長篇專論“價值、動機和行動系統”和《系統》視爲他當時“關於行動理論的系統論述”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就兩者的內容來看,前者側重闡述的是“人格—社會—文化系統”模型,後者著力論述的是社會系統(以及它與人格、文化系統的關係)。換言之,三系統模型構成了帕森斯行動理論發展的這個階段的一般參照框架。這種框架也主導著帕森斯在《系統》的最後一章關於行動科學分類的論述。該章第一節已經將這一點說得很清楚。在具體論述“行動科學的分類”的第三節,帕森斯對《結構》中的相關分類進行了修改,現在的行動科學主要研究的是上述三個行動子系統,因此其分類也就圍繞著這三個系統而展開。心理學的研究領域是“作爲一種行動系統的人格”,這是《結構》中相關論述的進一步發展。他對“社會系統”的論述則較爲複雜,《結構》中提出的行動科學的五種分枝學科似乎是屬於同一層次的,而在《系統》中,“社會系統”似乎並非某一門學科(如社會學)的研究主題,經濟學、政治科學和社會學分別研究社會系統的某個方面。
另外,在《結構》中與行動科學處於同一層次的“文化科學”現在則被納入“行動科學”之中,與文化系統相對應的是人類學及其文化理論。這樣一來,心理學和人類學似乎處於相同的系統層次,而經濟學、政治科學和社會學則處於較低一級的系統層次。其他如《結構》中的“技術學”在《系統》中只是在論及“合理性假定”時簡單提及,且未被作爲與經濟學等平行的一個行動科學的分支;歷史學也被提及,只是現在被視爲一門“綜合性的經驗科學”而非《結構》中與“行動科學”相對的那種“歷史科學”。帕森斯現在將“社會學理論”(而非社會學)界定爲“關於諸社會系統的理論的某個方面,它關注的是社會系統的價值取向模式的制度化現象、這種制度化的諸條件、各種(價值取向)模式中的變化、和一組這樣的模式相一致以及相背離的諸條件、與上述所有這些相關涉的諸動機過程。”心理學、經濟學、政治科學、社會學和人類學似乎取代了《結構》中的行動科學的五個分支學科,但作爲它們研究主題的諸系統似乎又處於不同的層次。
不論是在《結構》還是在《系統》中,帕森斯的學科分類都僅僅是某種探索,都存在著某些含糊性和問題,兩種論述間也存在著若干相矛盾的地方。《結構》是以對行動的基本要素(單位行動)的研究爲基礎,將從中産生的若干“突生特性”作爲不同學科的研究主題來進行行動科學的分類的;《系統》則完全是在系統的層次上,尤其是在“三系統模型”的基礎上對行動科學予以分類的。正如帕森斯1951年的“主要闡述”只不過是其理論發展的一個階段而具有過渡性特徵一樣,他在《系統》中的分類隨後因“四功能範式”的提出和發展而很快發生了變化;只是帕森斯可能也意識到上述局限於學科分類的做法的不便,他此後幾乎不再進行類似的科學分類,而是借助“四功能範式”著力發展其“社會系統理論”和“一般行動理論”。
不過,自1950年代晚期以降,隨著帕森斯對“社會系統”和“一般行動系統”的理論建構日趨清晰和成熟,他對社會學的研究主題及其學科地位問題的看法也越來越明晰。他在1966年出版的一部論述社會進化的著作中首次對“社會系統”、“社會”以及“社會共同體”這些概念及其關係進行了澄清,並將社會學的研究主題確定爲“社會共同體”,與之相關涉的社會團結或社會整合問題因此成爲社會學理論的核心問題。帕森斯的學生及晚期的主要合作者之一利茲很明確地指出:“帕森斯在其理論生涯中始終對下述問題給予特別的關注,即在更大的、多學科性的行動理論體之內確定社會學理論的位置。他特別爲了給社會學思想定位而力圖在更大的理論之內來確立核心概念和假設。”利茲認爲,帕森斯在其理論生涯的不同時期對此問題進行了“三次獨特而又不同的探討”:帕森斯在《結構》中“給社會學分派的任務是發展出一種對於社會行動系統是如何通過共同價值而整合起來的廣泛理解”,他此時主要關注的是證明“這種提議將塗酮幹和韋伯所確立的比較的宏觀制度分析予以系統化(codified)”;在《系統》中,社會學集中關注的則是“規範秩序是如何被制度化的”,他所要論證的是“這種提議將對於互動和人縻開係的動態研究和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強調的宏觀社會學的和制度性的分析統一起來”;在第三個階段的研究中,“社會學等同於對社會系統的整合維度(包括它與其他三個維度的相互依賴性)的研究,社會學研究應當關注影響(或被影響)團結或社會一致(coherence)的社會生活的所有結構與過程。”
.png)
帕森斯對“社會共同體”的論述和他對“社會”範疇的探討以及對“社會系統”的分析密切相關。作爲社會理論家,帕森斯很早就關注對社會學研究而言具有基礎性的“社會”範疇。他在早期爲《社會科學百科全書》撰寫的〈社會〉條目中指出:“可以將社會視爲指涉人及其同伴的整個關係複合體的最一般性的術語。”在主要從思想史的角度對西方歷史中從古希臘的“城邦”(polis)到現代的“國家”(state)的諸“社會”形態進行了簡要考察之後,帕森斯明確地將“社會”界定爲“人類關係的總體性複合體”;不過,這些關係是“從行動中産生出來的”,而這種行動又是通過“(內在的或符號性的)手段—目的關係”來説明的。帕森斯進而指出:“如此界定的社會只不過是具體的人類生活整體的一個要素,它也受到遺傳和環境的影響,還同樣會受到文化因素(科學知識和技術,宗教、形而上學和倫理的觀念系統以及諸藝術表達形式)的影響。社會不可能脫離這些事物而存在;這些因素在其所有的具體體現中都起著作用,但它們並非社會,社會所包含的僅僅是這樣的社會關係。”“社會”範疇在此時的帕森斯心目中似乎很清楚,但他尚無法明確地對其予以闡明,更缺乏一個明確的分析框架。
在1937年的“第一次主要綜合”中,帕森斯雖然在討論塗爾幹、韋伯、藤尼斯等人的社會理論時論及“社會”範疇,但他在《結構》中所關注的核心範疇是“社會行動”而非“社會”。他雖然在《結構》中提出了一個“行動參照框架”,但這個框架尚不足以來分析系統層面上的“行動”和“社會”。在1951年的“主要闡述”中,帕森斯提出了一個系統層次上的“行動理論參照框架”,並對“社會系統”的“結構”與“過程”進行了較爲詳細的闡述,第一次較爲系統地(雖然還很不完善)提出了他關於“社會系統”的分析框架。借助於他在1950年代前期提出並在後來不斷完善的“四功能圖式”、後來提出的“一般化交換(符號)媒介”和“控制論等級”(cybernetic hierarchy)等分析圖式以及在1950年代晚期較爲明確地將其系統分析從“社會系統”擴展到“一般行動系統”等一系列的理論創新和建構,帕森斯在1960年代之後對“社會系統”的分析日趨成熟和完善;到1960年代中期,他開始在這個理論分析框架中對“社會”範疇進行較爲明確和系統的闡述。
在1951年的“主要闡述”中,帕森斯將社會系統一般地界定爲一種“互動系統”。他在這個時期對“社會系統”的闡述都是以“人格—社會—文化”三行動系統模型爲理論參照框架。帕森斯指出,社會系統和人格系統、文化系統一道構成了“行動諸要素的三種組織模式”。其中,社會系統和人格系統被構想爲“動機性行動(motivated action)的組織模式:社會系統是圍繞行動者相互關係而組織起來的動機性行動系統;人格系統是圍繞著生命有機體組織起來的動機性行動系統”;文化系統則是“符號性模式系統:這些模式是由行動者創造或表現出來的,並通過傳播在諸社會系統之中進行傳遞、通過學習在諸人格之中進行傳遞。”作爲“互動系統”的社會系統是一種具有如下特徵的行動系統:(1)它涉及兩個或更多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過程;這樣的過程是觀察者的一個關注點。(2)行動者的取向情境包括其他行動者;這些其他行動者(他人)是行動者的宣洩(cathectic)對象;他人的行動被行動者認知性地解釋爲資料(data);他人的各種取向可能要麽是行動者將要追求的目標,要麽是實現目標的手段;他人的取向因此可能是行動者評斷的對象。(3)在一個社會系統中存在著相互依賴的和部分一致性的行動,其中,這種一致性是集體目標取向或共同價值以及規範性和認知性期望的某種共識的一個功能。在《社會系統》中,帕森斯對“社會系統”的定義是:
社會系統是由在某種情境中進行互動的衆多個體行動者所組成的(行動系統),其中的情境至少具有一個物理的或環境的方面,行動者以某種“滿足最大化”傾向爲其(行動)動機,而且行動者與其(行動)情境、包括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都是通過某種文化結構性的和共用的符號系統來界定的和以之爲仲介的。
帕森斯1951年對“社會系統”的第一次系統闡述和分析構成了其社會系統理論後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例如,他確立的“角色”概念或者“地位—角色”概念作爲社會系統基本的“概念單位”、“角色期待”作爲角色的“首要成分”的觀點;他對社會系統中的集體、邊界、團結/整合、共同價值、制度化、資源分配問題、個體動機與系統動力、變遷過程等概念和問題的闡述對於人們研究社會系統具有基礎性和開拓性的意義。其中,尤其是他對於社會系統的“功能先決條件”(functional prerequisites)的強調和分析構成了其行動理論發展的一個核心。帕森斯認爲,對於任何一個行動系統來説,若要“構成某種持久穩固的秩序”或“經歷某種有序的發展性變遷過程”,個體行動者的“充足動機問題”或“秩序的動機問題”以及最低限度的共用價值問題(或可稱之爲秩序的文化價值問題)是兩個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秩序問題,以及社會互動的穩定系統的整合(亦即社會結構)的性質問題,因此關注的焦點就是行動者的動機和那些將行動系統整合起來的規範性的文化標準之間的整合。”帕森斯以“內化/社會化”和“制度化”分別表徵社會系統的“功能先決條件”的兩個方面。
帕森斯在1960年代初爲他主持編寫的《社會的理論》撰寫了一個長達50頁的名爲〈社會系統大網〉的一般導言,在“四功能範式”的基礎上對其1950年代關於“社會系統”的論述進行了較爲充分的補充和擴展。不同於1950年代初期的“三系統模型”,他在這篇導言中以“四功能圖式”爲參照框架提出了一個關於“社會系統”的分析範式,並對社會結構的諸範疇、社會系統的結構及功能分化、社會系統的結構變遷等問題進行了較爲詳細的闡述,可以視爲對《社會系統》的“主要闡述”的一個較爲系統的發展。不過,帕森斯關於“社會系統”的分析範式依然處於發展過程中,其中的一些概念和分析還不明確。
到1960年代中期,隨著他對“一般行動系統”的系統分析的展開以及對於權力及影響力等一般化交換媒介的深入論述,帕森斯現在能夠更加明確地對“社會系統”的內部結構及外在環境進行系統闡述。例如他對社會系統進行了這樣一種描述性的界定:“社會系統是由人類個體的互動組成的,(這些進行互動的)每一個成員既是一個行動者(具有目標、觀念、態度等等),又是其他行動者和他自己的取向對象。因此,這種互動系統是一個可以從其(互動)參與者的總體行動過程中抽象出來的一個分析方面。與此同時,這些‘個體’也是有機體、人格以及文化系統的參與者。”這種描述和他1951年對社會系統的闡述並無實質性的變化;不過,借助於“四功能圖式”,他現在可以將社會系統置於一個系統性層次更高的系統之中:“用我們的範式的功能性術語來説,社會系統是一般意義上的行動(系統)的整合性子系統。行動(系統)的其他三個子系統構成了與之相關的主要環境。”同時,借助於“四功能圖式”和“一般行動系統”,可以對社會系統內部的諸子系統及其開係以及社會系統與作屬其環境的其他行動系統之間的關係進行詳細地闡述。
正是在這種對社會系統的內部結構的分析過程中,帕森斯對“社會系統”和“社會”這一對概念的關係進行了澄清。實際上,帕森斯在1951年對社會系統進行首次系統闡述的時候就涉及到這個問題。他當時認爲:“作爲一個系統,它具有確定的內部組織和確定的結構變遷模式。此外,作爲一個系統,它還具有各種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機制。這些機制的功能産生了一個系統的重要特性之一,即維持邊界的傾向。就特殊目的而言,我們可以將一個總體性的社會系統視爲自立自存的(self-subsistent);換言之,它在由其成員所確定的近似的界限之內包含了維持一個系統所需要的所有功能性機制,我們在此稱之爲一個社會。一個社會只不過是一種子系統。”在《社會系統大網》中,帕森斯已經明確地將“社會”界定爲“一種集體”,亦即,“一個由進行具體的互動的人類個體構成的系統,它是某種獨特的制度化的文化的首要載體,但不能説它是針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大部分功能性需求的較高等級的集體的一個分化的子系統。”到1960年代中期,帕森斯非常明確地將社會確定爲社會系統的一種類型,並指出:“作爲一個系統,它在與其環境的關係中達到了自足性(self-sufficiency)的最高層次。”或者如他後來所説的:“我們將社會界定爲具有如下特徵的社會系統類型,即具有相對於其環境(包括其他社會系統)的最高層次的自足性。”因此,不同於人們關於“社會”的常識觀念,即認爲社會是由具體的人類個體所組成的(社會成員的有機體和人格因此是內在於社會的而非其環境的組成部分);這種定義所指涉的“社會”是“一個抽象系統”,行動系統的其他同樣是抽象的子系統構成了其基本環境。
這種對於“社會”的界定的要點在於“自足性”。作爲一種社會系統的“社會”的“自足性”主要是相對於其環境而言的:“就其作爲一個系統的持續性而言,任何社會都要依賴於通過與其環境性系統(environing systems)的交換而獲得的輸入。因此,與環境相關涉的自足性就意味著(系統與其環境之間的)交換關係的穩定性以及爲了社會的功能發揮而對這些交換進行控制的能力。”帕森斯指出,可以將“自足性標準”劃分屬五個亞標凖,分別與社會系統的五種環境(終極實在、文化系統、人格系統、行爲有機體、物理—有機環境)相對應:“一個社會的自足性是它對其與五個環境之間的關係的控制和它自己的內部整合狀態之間的穩定結合(balanced combination)的一個函數。”另外,“社會”的“自足性”還體現了其“進化”意涵:“自足性顯然是生物理論意義上的一般化適應能力的某種程度(問題)。”這後一點與帕森斯對社會—文化進化的論述密切相關,下文將論及。
同時,帕森斯對作爲社會系統的一種類型的“社會”的內部結構也給予了分析。“ 這種分析一方面體現在運用價值、規範、集體和角色四種“獨立的變量類型”來分析諸社會系統的結構,”另一方面是確定“社會”這種社會系統的諸功能性子系統——正是在這種分析中,帕森斯第一次提出了作爲“社會”的整合性子系統的“社會共同體”概念。另外,帕森斯運用他在此期間開始系統提出的“社會—文化進化”的理論範式對“社會”和“社會共同體”進行歷史—比較分析。上述諸方面綜合反映在圖1中。
.png)
圖1:社會(或更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系統)
因此,“社會共同體”的概念是作爲“社會”這種社會系統類型的一個子系統而提出的:“一個社會必須構成一個具有某種充分的整合或團結層次和一種獨特的成員身份地位的社會共同體。”關於“社會共同體”,帕森斯指出:
作爲一個系統的社會的核心是模式化的規範秩序(pattened normative order),通過這種秩序,某個人群的生活被集體性地組織起來。作爲一種秩序,它包括價值以及分化的和被詳細闡述的(pariculatized)規範和規則,而所有這些要變得有意義和具有合法性,都需要有文化指涉。作爲一個集體,它顯示出某種模式化的成員資格(membership)概念,這種概念將那些屬於該集體和不屬於該集艘的個體區分開來。……我們將社會的這樣一種實體(entity)(就其集體方面而言)稱爲社會共同體。如此説來,社會共同體是由一種規範性的秩序系統和那些可能因共同體內部的亞群體而變化的、與成員資格相關的地位、權利和義務來構成。爲了生存和發展,社會共同體必須保持某種共同的文化取向的完整性,作爲其社會認同之基礎的這種文化取向是共同體的成員所廣泛(儘管並非必然是全體一律地或全體一致地)共用的。”
從帕森斯對“社會共同體”的上述界定來看,它的內部要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規範秩序”,二是“集體”(或“集體性地組織起來的人群”)。帕森斯認爲這“兩個要素之間的相互關聯性”是“社會共同體”關注的焦點。前面提及的分析社會系統和社會的四種“獨立的變數成分類型”同樣適用於對“社會共同體”的內部結構的分析:價值和規範與“規範秩序”相關涉;集體和角色則與“集體性地組織起來的人群”相關涉。
作爲“社會”的一種子系統,“社會共同體”和“社會”一樣具有其“自主性”;不過,這種自主性所面對的環境和“社會”有所不同,“社會”的另外三個子系統“經濟體”(economy)、“政治體”(polity)和“信任系統”(fiduciary system)構成了“社會共同體”的“內在一社會環境”;而行動系統的其他三個子系統,即文化系統、人格系統和行爲有機體則構成了其“外在—社會環境”:“社會共同體依賴於某種高級的文化取向系統,這種系統首先是其規範秩序的合法性的首要根源。因此,對於政治和經濟子系統(它們各自與人格和有機—物理環境具有最爲直接的關聯性)而言,這種(規範)秩序構成了基本的較高等級的指涉。”帕森斯對“社會共同體”與其環境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分析;關於社會共同體及其環境的關係,可參見圖2。帕森斯後來對社會系統(社會)及其包括社會共同體在內的子系統的內部結構及其關係有較爲明確的圖式説明;關於“社會共同體”的內部結構,可參見圖3。限於篇幅,本文不再對這些問題一一闡明。
.png)
圖2:社會共同體及其環境
因此,到1960年代中後期,帕森斯對於社會系統的分析圖式、社會系統及其諸功能性子系統的內部結構、外部環境以及它們之間的複雜關係等等問題都越來越清晰了,聯繋本文第一部分論及的帕森斯關於社會學的研究範圍及學科地位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在分析的意義上,社會學的研究主題並非整個社會系統或者作爲社會系統的一種類型的社會,而是(和經濟學、政治(科)學等社會科學學科一樣)集中關注其中的某一個方面,即社會共同體以及它所關涉的社會整合或社會團結問題。不過,作爲西方智識傳統的現代産物的社會學的研究主題,“社會共同體”在人類社會歷史中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分化或進化過程;對這種過程的論述構成了帕森斯社會—文化進化理論的核心內容。
.png)
圖3:社會共同體的結構
.png)
前文在論及“社會”和“社會共同體”的“自足性”問題時曾提及帕森斯的另外一個視角,即“社會—文化進化視角”;某種意義上講,帕森斯對社會系統、社會以及社會共同體這些概念的分析就是在其“社會—文化進化”理論框架中展開的。按照帕森斯的“社會—文化進化理論”,人類“社會”是處於分化和進化的過程之中的;換言之,“社會”是一個歷史範疇。而作爲“社會的核心結構” 並同樣具有其“自足性”的“社會共同體”同樣是一個歷史範疇:“較爲具體地講,在進化的不同層次上,社會共同體被人們稱爲部落或者‘民族’(people);或者,對古希臘來説,它是‘城邦’(polis);而在現代社會,人們稱之爲‘國家’(nation)。”
簡而言之,帕森斯認爲社會或社會共同體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經歷著一個不斷分化和進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系統和文化系統分化開來,社會系統或社會內部也隨著歷史進程而不斷分化;人類社會從最初的整體性社會發展爲當今高度分化的社會。帕森斯提出了一個較爲完整的“社會—文化進化”理論圖式,“限於篇幅,本文不擬對此過多涉及,僅就社會和社會共同體的演進中的若干要點進行簡要論述。
帕森斯將人類社會的演進大致上分爲三個階段:初民社會(primitive society)、中級社會(intermediate societies)和現代社會。其中,初民社會又分爲以澳洲土著社會爲代表的最初階段和後來出現的“高級(advanced)初民(社會)類型”兩個階段;中級社會也可劃分“古代社會”(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帝國)和“歷史帝國”(中國、印度、穆斯林帝國和羅馬帝國)兩個階段;他對現代社會的論述主要集中於西方社會, 並對西方“現代系統的首次成形”(17世紀歐洲西北部的英國、荷蘭和法國)、18及19世紀“革命年代”的歐洲系統內部複雜的分化與整合關係、作爲20世紀西方“主導社會”(lead society)的美國社會等進行了簡要考察。
以作爲“初民社會”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代表的澳洲土著社會爲例,帕森斯指出:“在這些原始的系統中,整個社會是由一個單一的姻親集體(affinal collectivity)構成的,或者是血緣群體通過其成員的婚姻聯合起來的聯盟。”在這種社會中,“作爲一個整體的社會共同體的核心結構是通過約定俗成的婚姻規則來調節的姻親系統。……這種規範複合體將部分性的世系和氏族聯結爲一個社會,儘管不是一個具有鮮明邊界的社會。”也就是説,澳洲土著社會的“社會共同體”是一個單一的血緣—姻親共同體。但是,當這種社會向“高級的”(advanced)初民社會轉變時,由於分化過程中新的因素,即地域(territory)因素的導入,“必須重新對共同體的基礎予以基本的確定,以便包括‘階級’模式和優先婚姻(preferential marriage)。社會共同體開始被視爲一種種族一地域群體(ethnic-territorial group)。”在初民社會的這個“高級階段”,“社會集體變成了一個部落(tribe),一種對某一地域保持管轄權的種族群體。”因此,“在最原初的社會中,社會共同體完全建立在姻親圈結的基礎上。(社會)分化的一般過程將第二個軸心導入了共同體的結構之中,只有通過更爲複雜的整合機制才能控制這種新的因素。地域性將外部的共同體與內部的同地域位置(亦即土地財産)相關的財産制度的基礎聯結在一起。因此,居住場所和對階級資源的控制開始獨立於親屬群體;就其在系統中的位置而言,(社會的)運行單位(某種意義上的一種世系)就具有了兩種主要的獨立基礎:親屬關係和財産。”
在“古代社會”階段,作屬其代表的兩種“帝國”類型形成了某種有趣的對照。一方面,“古埃及是更具等級制的古代社會類型的典範,在宗教和世俗兩個方面,一系列有序的等級被結構化,從法老以降直達各種層次。”帕森斯因此認爲“可以將金字塔作爲這種社會本身結構的一個象徵。”另一方面,美索不逵米亞諸帝國則是另外“一種基本模式的典範”,即“相對自主的城市共同體的早期發展”,它以各種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遍及該區域的整個地區。帕森斯指出:“從相當早期開始,這種社會結構顯然探取了多元的城市國家,或者……相對自主的城市共同體的形式,這些城市國家或共同體控制著圍繞著它們的農業區域。”
到了“中級社會”階段,歷史上的諸相關的文化運動發展起一種具有根本意義的區分,即“表徵終極實在的秩序”(the order of representations of ultimate reality)和“表徵人類境況的秩序”(the order of representations of the human condition)之間出現了分化,這種分化實際上指涉的是文化系統和社會系統之間的分化,並構成了人類社會共同體在此階段發展的一個共同基礎。帕森斯指出,較之於任何一種古代系統,在這個時期的中國、印度、伊斯蔭和羅馬這些“歷史上的帝國”中的“文化系統的諸模式都更深地滲透到社會結構之中。”不過,在前兩種帝國中,“對於那些明確的上層階級群體來説,文化系統成爲地位的焦點,這些上層群體集體性地爲其社會確定了最重要的基調,儘管沒有合作性組織的存在。”後面兩種帝國則“包括一個更爲深遠的、‘現世取向的’社會共同體概念;一般而言,這種概念延伸到所有能夠進入該文化—社會共同體的人之中,而且不確定先賦性的障礙。”
帕森斯以比較—進化的視角來考察人類歷史上的“社會”或“社會共同體”的演進,這種考察的關注點或者目的並非其整體演進過程或不同類型之問的比較,毋寜説這種考察的著眼點在於探究現代西方所獨有的那種“社會”或“社會共同體”是如何産生和形成的。因此,他對第三個階段,即“現代社會”的考察,就基本上局限於“西方社會”。
帕森斯對西方“社會共同體”的演進的考察大致上有這樣幾個要點。首先,他特別強調“現代諸社會的前現代基礎”。他在專論其“社會—文化進化”理論的兩部著作的第一部的最後對他所謂的兩個“溫床”社會(seed-bed societies),即以色列和古希臘給予了特別強調,將它們視爲“文化創新的能動者(agents)”,認爲它們爲後來西方現代社會共同體的發展提供了諸多基本要素。
其中,以色列是“耶和華宗教(或猶太教)的原創者”,希臘是“一種著名的、大體上是世俗的文化的原創者”。就以色列而言,它最初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部落聯盟”而已,但是卻産生了一種偉大的宗教。這種宗教的許多要素對後來的西方社會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關於以色列人,“最獨特的事物是關於耶和華的觀念以及這個民族和他的關係。這種關係植根於聖約(covenant)概念之中。”超驗—神諭、對上帝律法(如“摩西十戒”)的絕對信仰(區別於儀式性的宗教崇拜)、此世取向(chis worldly)以及作爲一個社會共同體的以色列民族等要素構成了這種宗教的實質性內容。另外,雖然“上帝的選民”(the Chosen People)這種觀念具有其“特殊主義”的意涵,但它是“依據某種被神聖賦予的、而非它自己的內在事務的規範秩序來調節它自身和確定其同一性”;換言之,以色列民族是根據一個超驗的上帝所賦予的規範秩序來指導其民族事務、確定民族同一性的。而耶和華“並非僅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而是“普世之神”(the universal God),這就導致了“支配人類事務的道德秩序概念,由於是被一位超驗的上帝控制的因而獨立於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或政治組織。”也就是説,指導以色列民族的規範秩序具有普世性或普遍主義的特徵。
總之,以色列是個“特殊的文化複合體:首先(存在著)一個超驗的‘立法者’上帝;其次,這個上帝所規定的一種道德秩序;第三,一個執行上帝的指令的神聖共同體的觀念,這種共同體不僅能夠在以色列的政治獨立終結時倖存下來,而且最終會成爲獨立於以色列人的共同體的散佈單位並遷移到非以色列的社會和集體之中。”帕森斯認爲上述這些就是以色列對於社會進化的偉大貢獻。而在古希臘,小小“城邦”是主要的社會單位;使希臘諸“城邦—國家”(city-state)連接起來並保持一致性的是希臘的文化模式。
和以色列不同,希臘盛行的是多神論或多元主義;不過,希臘的文化和以色列文化一樣,也“超越了任何單一的政治上組織起來的共同體”:“以色列人具有一個超驗的規範性權威,他們必須順應耶和華的意志。希臘人不是將這種權威設想爲任何特殊神祗的意志,而是將其設想爲一種神聖存在的並對他們施加影響的秩序,這種秩序最終被系統地闡述爲自然秩序(the order of nature)。……這種一般性的秩序概念是獨特的希臘社會組織模式的一個本質性的條件。它比以前的任何文化模式都更加深入地實現了城邦—國家的構成性要素的基本平等。”他還對古希臘的公民以及作爲“公民團體”的城邦給予了強調;並同時強調了存在於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及斯多葛派的哲學思想中的普遍主義特徵。
因此,“和以色列民族一樣,希臘通過一種關涉整個社會單位從其他社會類型中分化出來的過程發展出一種極爲獨特的文化系統。最爲重要的是,城邦發展爲一種公民共同體(corporate body of citizens),這種團體(尤其是在具有主導性和典範性的雅典)成爲一個平等者(equals)的團體,儘管非公民的居民被排除在外並保持著一種‘下等階級’(的地位)。”基督教是對這兩個“溫床社會”的綜合和延續,也是現代西方社會發展的最重要基礎。另外,羅馬的“制度性遺産”,尤其是“羅馬法”對現代西方社會的形成也具有基礎性的意義。他同時對“中世紀社會”、“歐洲系統的分化”、“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這些顯然對於現代西方社會的形成都做出了某種貢獻的因素給予了簡要考察。
其次,帕森斯對他所謂的“現代系統的首次成形(crystallization)”進行了獨特的論述。他認爲西方現代社會形成於17世紀左右,發端於(歐洲)“西北角”的他稱之爲“早期現代的‘標兵’”的英國、荷蘭和法國。帕森斯指出:它們“最重要的發展發生在其社會共同體之中。這三種社會共同體之中的變更是巨大的,但是其中的每一種都爲民族團結(national solidarity)貢獻了主要的創新。特別是英國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概念,它爲某種具有比較明顯分化的社會共同體提供了一個基礎。這種分化朝著三個方面推進,即宗教、政治和經濟,每一個方面都關涉規範性考慮。法律創新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尤其是對於那些贊同社會共同體的結構的聯合性而非科層制的潛在能力的國家。它們與議會制政體和更爲發達的市場經濟的産生密切相關。”帕森斯特別強調英國“社會共同體”的發展:“到17世紀結束時,英國已經變成了歐洲系統中最具分化性的社會,比此前的任何一個社會在這個方向上都進展得更遠。”
第三,帕森斯對於他所謂的西方歷史上的“三次革命”對現代西方社會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所具有的關鍵作用給予了特別強調。首先是發端於18、19世紀歐洲的“産業革命”和“民主革命”對於現代社會共同體的發展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宗教改革之後的主要發展趨勢所強調的是,在某種能動主義的(activist)價值系統的指導下的社會的適應和整合能力,這關涉新的分化秩序以及不斷增長的(塗爾幹意義上的)有機團結。産業革命之所以是這種趨勢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在於經濟生産率的極大增長引致了社會意義上的分工的巨大擴展。正如我們所強調的,這種分化中的擴展産生了對於新的整合結構和機制的需要。民主革命主要關涉社會的整合方面;它關注的焦點是社會共同體中成員資格的政治意義以及由此對於財富和更爲重要的,政治權威和社會特權領域的不平等機制的關注。
帕森斯明確指出,“産業革命”和“民主革命”導致了現代西方社會系統內部的進一步分化:經濟體和政治體分別與社會共同體分離開來。這樣,經過幾個世紀的“大轉變”之後,高度分化的現代歐洲系統已經大致完備:一方面,“‘充分’現代性的出現因此削弱了(包括)君主制、貴族制、英國國教以及受親屬關係和地方主義所限制的經濟在內的先賦框架,使得它不再發揮決定性的影響”;另一方面,普遍主義的法律系統、世俗文化、聯合原則、民族主義、公民權、代議制政府、分化的市場、職業性服務、有效組織的具體功能的新模式等等現代性要素大都發展起來。
不過,在歐洲之外,西方現代性的另外一種新力量産生了:美國在18世紀末獨立後,在19世紀即獲得了迅速的發展,這種發展先是與歐洲“相平行”,但是很快就超越它而成爲“新的主導社會”,它在19世紀中期以後在西方現代性的發展中所佔據的位置類似於英國在17世紀現代歐洲系統形成中的地位。帕森斯所謂的“三次革命”的第三次革命,即“教育革命”雖然始於19世紀中葉的歐洲,但是它的最典型和最充分的展現卻發生在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社會中。“教育革命”給美國帶來了不同於歐洲社會的結構和特徵:“這個社會主要的獨特特性可歸諸於某種聯合性的、多元主義的側重點,既非其階級歧視的尖銳性和僵化性,也不是其官僚制化那特別高度的發展。除了分權化的治理民主(decentralized governmental democracy)(聯邦制和分權是其範例),政教分離的宗教慣例、教派多元主義以及通通對於較大的遷入的宗教及種族群體之包容的在整合意義上的吸納能力,儘管這種吸納遠非徹底。”因此,帕森斯認爲現代西方社會共同體雎然發端和奠基於歐洲,但卻是在美閾得到最充分和成熟的發展。
通過以上極爲簡略的勾勒,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帕森斯所謂的“社會共同體”的歷史發展軌跡;這種發展也説明帕森斯提出作爲其理論發展晚期的核心概念的“社會共同體”並非空想和臆造,而是具有其堅實的歷史依據和理論依據。
文字编辑:高雅馨、张歆泽、吕灵
推送编辑:谷诗洁、罗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