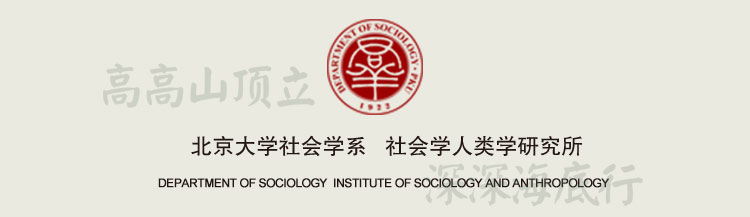(2024第1辑)刘诗予:情感与空间:重寻戈夫曼理论中的神圣个体
刘诗予
提要:本文将戈夫曼早期的互动理论置于涂尔干以降神圣性理论的脉络中,围绕情感和空间两条线索,重新梳理戈夫曼理论中的自我观。情感和空间的分析视角揭示出个体所面临的两层张力,即个体与外部情境的张力和个体内部多重自我之间的张力,身处其中的个体因而始终处于圣俗二分的交界之地。本文认为,戈夫曼理论中的个体具有情感和空间的属性,这些属性使得自我在情境互动中与情境结构形成定义与再定义的循环,本文因此也从情感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涂尔干学派的神圣性理论作出了推进。
戈夫曼从正面情感转为负面情感,探究现代人进入互动仪式的出发点;在空间上,戈夫曼继承了莫斯的理论原型,并在几何空间的概念上扩充了社会空间的意涵。这两个方面的理论构造使得戈夫曼的互动论重返了涂尔干经典的人性二重性学说。本文认为,情感和空间所揭示的互动悖论实际上反映出现代个体最根本的生存状态,个体将始终处于神圣与凡俗的交界之处,在被撕裂的张力中通过能动的行为维持裂缝的存在,成了现代社会新的神圣之物。
关键词:神圣个体;情感;空间;紧张管理;人性二重性
.png)
长期以来,欧文·戈夫曼因其拟剧论和对微观人际互动的敏锐观察被视作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然而,即使被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称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戈夫曼却很难在社会学界的各个流派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Erving Goffman,(1922-1982)。
在学界,欧文·戈夫曼的理论生涯通常被划分为两个阶段,1969 年之前的早期文本主要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情境互动与印象管理策略,探讨个体在互动中的行为、动机以及策略,其主要作品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1959)、《交遇》(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1961)、《收容所》(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1961)、《污名》(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1963)和《互动仪式》(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 to Face Behaviour,1967)。1969 年后的文本如《互动策略》(Strategic Interaction,1969)、《框架分析》(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1974),则转向对框架和谈话仪式的分析。
正是上述理论和著作史的分野使戈夫曼的理论极易被二元论的分析路径理解。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致力于从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立场分别挖掘戈夫曼的理论。罗宾·威廉姆斯将戈夫曼不同文本中的自我区分为作为表演者的自我、作为社会情境结果的自我和作为社会过程的变动自我,三者分别强调个体与他人的互动、个体受组织制度安排的影响以及个体的流动变化。对多重自我的各种解读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个体所具有的能动性,认为这种能动的、展演的自我特性在行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沿着这一框架,克里安强调个体主义在戈夫曼理论中的决定性地位,指出不同于涂尔干对集体意识和社会团结的强调,戈夫曼文本中个体主义的向度完全压倒了社会性。
另一方面,情境本身的结构特点也提供了一种对戈夫曼的结构功能主义式解读。虽然戈夫曼的论述基础是琐碎微观的日常生活,但制度形式本就蕴含于个体的日常接触之中,制度形式的固定性不会脱离日常生活的行动而单独存在。柯林斯也指出,戈夫曼强调的是情境之于个体的外在性、先在性、强制性和结构性。因而,与符号互动论者的视角恰恰相反,情境不再是随着互动过程一同发生的,而是一种位于个体之外的预设和框架。作为框架和结构的情境对身处其中的个体施加着制度性的要求和约束,从而规范和限制着个体的行为。
在这样的理论视阈下,戈夫曼的互动论常被理解为一种非道德性的行动指南:个体在互动中计算得失并以利益为原则指导行动,或受外部力量的影响被塑造出矛盾的多重自我。然而,本文认为,戈夫曼眼中的面对面互动实则具有一层不易察觉的道德色彩,这种道德性从始至终贯穿着戈夫曼的作品,引导我们从个体内部的张力来检视互动论中多重自我矛盾的真正来源,打破二元对立的视角。在 1969 年后,戈夫曼的理论关注点转向谈话分析等深层意义之中,但其理论关切仍然在日常互动研究中留下了一以贯之的线索。因此,本文将主要聚焦于戈夫曼 1969 年以前的早期作品,通过重新检讨其互动论中的个体张力问题,揭示戈夫曼理论中没有得到重视的道德性脉络。
“道德”这一关键词将我们重新带回涂尔干的理论脉络中。戈夫曼所探讨的自我实际上是一种怎样的个体?在学术生涯的一开始,他就曾在博士论文中引入涂尔干关于神圣性的概念来解释个体的互动行为: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考虑的对象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圣的偶像、形象或神。我们对人所呈现出的东西,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给了这些神圣之物。我们感到这些东西具有某种神圣的价值……人,除非他们身居高位,否则并不像偶像那样拥有神圣之力或玛纳(mana),因此不需要用那么多的仪式来对待。偶像之于人,就像仪式之于礼仪。
戈夫曼视个体为“神圣之物”。而在二元论视角下分析戈夫曼的多重自我观时,个体被抽离了人性与道德的属性,也不再具有神圣的意涵。情感与空间的概念将我们重新带回涂尔干学派的神圣性脉络之中。涂尔干在学术生涯的末期曾经发问:宗教正在衰落,维持社会之力的激情已经不在,在这个“道德平庸的时代”,旧神已死,新神未生,我们应该到哪里重新寻回神圣性?他的答案落回到个体身上。个体作为新神的降临成为涂尔干思想的终点,也成为戈夫曼问题意识的起点。在互动秩序的框架之下,戈夫曼对个体自我的关注,实际上呼应的是涂尔干理论中关注的“神圣性”问题,在戈夫曼与涂尔干学派的交汇处,“情感”与“空间”两个核心意涵浮现出来。
情感首先是涂尔干笔下神圣性的起点。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中,涂尔干通过考察古式社会的宗教仪式发现,宗教思想的本质属性在于将世界分为截然对立的神圣与凡俗两部分。在各种宗教活动中,个体感到一种绝不会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高潮。这种强烈的激情和集体欢腾,使个体体会到一种更高的,围绕着灵魂产生的社会力(social force),从而使其进入了另一个神圣的世界。

涂尔干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在仪式活动中,不同的个体所具有的情感融合成了一种共同的情操。在这种同质性中,热情迅速上升成一种超常的兴奋,当人们以集体的形式开始疯狂地喊叫、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时,这些共同的行动反过来增加了活动的强度,像雪崩一样把这股冲动继续推进。剥开这层激情的外壳,涂尔干描绘的集体情感的底层仍然是一种道德情操。原始人在仪式活动中感受到的不仅是纯粹无意义的狂喜,而是一种“我正在和集体共同完成一件正确的事”的价值感。社会之力所带来的情感能量赋予个体勇气、信心、大胆、高尚,这些正面情感让个体享受身处集体之内的美妙,渴望继续不断地体验到这种感受。正因如此,凡俗的个体开始渴望摆脱凡俗,走向非凡。
与集体欢腾相关的是,空间成为个体分得神圣性的必要条件,并与情感体验紧密相连。仪式活动的产生首先要求所有参与仪式的个体在身体上共在,只有聚集在同一地点时集体欢腾才有可能发生。除此之外,当个体借助情感感受来对整个世界进行分类、把握社会整体的时候,涂尔干也将空间的范畴纳入进来。空间对于涂尔干来说并不是先验的,在《原始分类》(Primitive Classification)中,涂尔干指出:“很多民族认为,区域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别。这是因为每个区域都有它自身的情感价值。在各种不同的情感的影响下,每个区域都与一种特定的宗教本原联系起来,因而也就赋有了区别于其他所有区域的独具一格的品性。”当原始人以情感为基础来把握社会时,群体共同的情感也被附着到其所共处的空间之上,相同的情感强化了所属空间的联系。
另一方面,不同部族所感受到不同的情感价值也带来了空间上的区隔,“空间本没有左右、上下、南北之分。很显然,所有这些区别都来源于这个事实,即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情感价值”。空间的区隔源自对共同情感价值的把握,引入空间的范畴将个体行动的价值从有限的仪式活动区域拓展到完整的社会生活领域。对空间的分类看似是从整体中切分出独立的个体,实际上是在个体的差异性中感知整体的融合。
如果说涂尔干通过宗教仪式开辟了圣俗二分的入口,那么莫斯则希望证明,比宗教更强调个体意义的巫术在本质上同样是社会的。在《巫术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Magic)中,莫斯提出,巫术的效力在于在巫术环境中使人感受到自己与玛纳之间的联系,强调个体在即刻环境中的情感体验,由这种直观感受构成对社会的理解。除了社会之力,莫斯不断要求我们去想象一个特定的巫术环境,这一环境包含了完成巫术所需要的所有条件,禁忌的边界为这个环境设立了界限,仪式参与者因等级和职能不同而在这一环境中处于不同的圈层,个体所能分得的神圣性也随着圈层而变化。在这里,莫斯提出的是一种力量—环境(Force and Milieu)的观念,力量与环境密不可分,仪式的形式力图制造出巫术力量,也同时制造出某种特殊的环境。
在涂尔干笔下,群体所共有的情感被附着到他们共处的空间之上,情感强化了所属空间的联系,不同的情感价值造成了不同空间的差异。莫斯进一步指出,空间是仪式得以发挥作用的要素和前提。实现巫术的特定环境中必须包含完成巫术所需要的所有条件,只有在这个空间之内,巫术的感应仪式才有可能发生。力量与环境是一体两面的,只有通过制造某种特殊的环境,巫术的力量才能透过仪式的形式展现在个体面前。
涂尔干和莫斯对神圣性的考察揭示了内在于个体和社会、身体与灵魂、个性感官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张力问题。涂尔干指出,人性天然具有内在的二重性,神圣与凡俗的二分也始终存在于个体内部。个体为了接近普遍性的道德基础必须压抑作为个人的本能,走出自我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撕裂和痛苦,这种张力也恰恰说明了人类生存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紧张。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将神圣性作为理解这种内在紧张的进路。个体对社会的感知都不可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必然需要基于某种对自身和周遭事物具体的情感体验和空间前提来获得。
个体是神圣的,但个体并不能天然意识到神圣性的存在,也并不独占神圣性的力量。个体必须要在和他人的共在关系中,借助集体的力量来感知社会之力,触摸神圣之物。“我与所有同我一样共同属于同一社会群体的人共同分享这种观念……无疑,当人们琢磨那些他从共同体中得到的概念时,就会把这些概念个体化,给它们贴上他个人的印记。”因而,神圣个体的观念实际上超越了感受—道德/个人—社会的简单二分,表明个体性正是从群体共同的观念和情感中分得而出,群体性又建立在每个个体的共同感受之上。
然而,虽然涂尔干承认了人性的二重性及背后永恒存在的个体—社会的张力,他仍然没有给出如何“走出自我”的真正解答。在现代社会构成人们生命基础的日常体验中,我们应该如何重新把握自身在宇宙中的分类和位置,捕捉社会曾经赋予我们的神圣力量?情感和空间的概念指引我们重新回顾古式社会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在宗教仪式中,情感是仪式激发集体同一性、感受普遍性的基础,空间则是产生仪式与情感的前提条件,以及对世界进行分类的依据。通过情感和空间的机制,凡俗的个体才能够分得神圣性。通过追溯宗教的神圣之力,涂尔干实现了神圣个体对道德个体的第一次超越。
而借助情感和空间的具体机制,个体实现了第二次超越,即个体并不是毫无能动性地等待神圣性流溢到自身之上,而是能够通过对情感的感受、理解、把握、调节,对空间的运用、适应、调整,从自我内部孕育出新的力量。这正是戈夫曼的洞见之所在。戈夫曼对日常生活中互动行为的观察,实际上是将涂尔干笔下的宗教仪式转变为现代社会中蕴含互动情境中的世俗仪式。他继承了涂尔干关于神圣性的判断,继而沿着涂尔干笔下神圣性产生作用的机制推进了对现代个体之神圣性的理解。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在涂尔干笔下,仪式活动里的情绪是单纯的欢腾与狂喜,社会行动的规则通常是制约性的,是“强制”“约束”“义务”。莫斯对涂尔干的神圣情感已然发生了一次概念上的转向。在礼物交换中,莫斯明确指出赠礼是强制与自发参半的,个体对这一互动规则的把握依靠的不是外部强加的社会控制,而是布迪厄所说的“非明示性图示”。礼物交换所依靠的核心情感是一种期待(expectation),接受了礼物意味着承担了对方的期待,如果不履行回礼的义务,没有恰当地满足对方的愿望,“那将是不公正的”“会令人难受”。莫斯认为这种期待的背后是“一种模糊的焦虑”。在夸富宴中,引导个体行动的情感动力既包含对被认可的渴望,也包含对被剥夺、被排斥的焦虑和恐惧。
在一般社会学领域,莫斯以国家与国家间互动产生的外交紧张为例,指出期待承载的是各种“紧张状态”,以及在现代社会中伴随技术劳动而出现的普遍焦虑。这种焦虑在心理学和生理学上被人们理解为“癫狂”,与之相关的忧虑则来源于“被取代”和“被压抑”以及由此产生的“剧烈的冲动”。和涂尔干所描述的一样,这种强烈的情感状态“在我们幸福的、世俗的市民生活中是罕见的”,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法国,战争已经让人们痛苦地感受到这种情感体验,在战后的整个现代社会中,这种情感还将“无止境地、更频繁地出现在人类生活中”。
不同于涂尔干对仪式活动中正面情感的强调,也不同于莫斯在礼物互惠中发现的“期望”及其落空,戈夫曼的创造性首先体现在,他是从尴尬(embarrassment)、羞耻(shame)、紧张(tension)等负面情感切入神圣性,从而呈现出内在于互动情境中的张力。在互动情境中,包括尴尬、羞耻、紧张在内的负面情感恰恰反映出个体为维持互动秩序所做出的努力,成为我们理解个体内在张力的关键点。戈夫曼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独特的带着焦虑不安的情感,并带着这一线索直面现代社会中个体的日常生活。宗教仪式能够通过赋予个体情感能量,让个体感受到群体,恢复社会的活力,但这种情感是强烈却短暂的,仪式需要被周期性地重复,但只能是反复性的而不能是永恒持久的。
在涂尔干的基础之上,戈夫曼对互动仪式的研究正是为了考察仪式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能够长久地维持,并让情感持续地发挥作用。戈夫曼以及其后加芬克尔的常人研究让我们认识到,在宗教仪式的激情之外,平淡无奇的情感是渗透在社会生活中的持久的、潜在的氛围或情感状态,它们酝酿出成员在社会中的身份感和自我感。尴尬、羞耻都是长期持久的情感类型,它们弥漫在互动中,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性表达。于是,现代个体在最普通的互动中展现出绝对伟大又绝对悲惨的一面:他们在互动中游刃有余,正是出于内心深处对孤独的恐惧。
.png)
在其理论的中早期,戈夫曼对情感倾向的考察集中体现在羞耻和尴尬的概念之上,这两种情感实际上是互动情境中无处不在的紧张的外在表达。通过分析个体进行紧张管理的诸种方式,戈夫曼揭露了互动情境内的根本悖论,即无论个体如何努力,互动中的紧张永远不会消失。因此,紧张这一情感视角得以带领我们走入个体内部,探究多重自我的根本矛盾。
在戈夫曼看来,正是“造成尴尬的事件和人们回避尴尬的方式,为社会分析提供了一种跨文化的框架”。 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戈夫曼就使用了大量与情感有关的词汇,其中尴尬(36 次)与羞耻(22 次)的使用频率最高:“出于对表演者的敬畏,观众才不去追究的那些事情,通常是那些泄露之后会让表演者感到羞愧的事情。……我们就像是一枚社会硬币,一面是敬畏,一面是羞愧。”在戈夫曼这里,现代个体身上的神圣和羞耻是一体两面的,借由羞耻,个体才能意识到圣与俗在日常生活中的分界,反过来体察到神圣性的存在。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在互动中,羞耻的产生首先源于未被满足的期待。个体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行动并给他人造成某种印象,其目的是使对方做出符合自身期待的回应,与这种期待的任何偏离都会导致尴尬和羞耻的产生。与期待不符的行为一旦出现,首先会打破互动中的信任,暴露出与当前情境定义不符的另一种自我。互动中持续存在的期待导致暴露多重自我的威胁时刻存在,这种威胁会成为互动情境中的紧张(tension)。所以,即使在尴尬尚未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必须竭尽全力地隐匿我们的情感与品行之间所有的不一致”。
在失当行为发生后,个体必须进行紧张管理(tension management),隐藏自己的慌乱、强作镇定或用其他方式进行补救,以向其他互动者证明自己没有真的破坏互动的秩序,仍然值得信任。而其他互动者即使看出个体在隐藏自己的羞耻,也会装作不知情,隐藏自己对他人羞耻的知晓。自我受到威胁的个体和威胁到他人的个体为他们所造成的失态有一种共同的羞耻,每个人都感觉自己飘若浮萍,惶惶不安,这就是为什么尴尬具有感染性和传播性,一旦发生就会处于永远的扩散中的原因。因此,羞耻这一负面情感构成了互动情境的底色,又成为推动互动循环下去的动力。
如果放在神圣个体的视角下,不难发现,戈夫曼早期的所有作品实质上都在讨论紧张管理如何实现的问题,而这正是他选择的继承涂尔干神圣个体的进路。借助羞耻、紧张和紧张管理这一情感路径,戈夫曼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圣俗二分的日常表达。情感这一看似最个体、最私人的感受,实际上是从情境整体中流溢而出,每个个体通过对自我的紧张管理,默契地完成一种对集体的承诺,实现对结构的维护。于是,从个体性之上生发出的是涂尔干所说的共同性,在最凡俗之处,现代个体却找到了最神圣的归处。
(一)表演崩溃:情境化自我初现
在用表演理解日常互动时,戈夫曼区分了作为演员的行动者所完成的两种互动模式:角色内活动和角色外活动。理想情况下,行动者只需要完成角色内活动,表演者呈现的自我形象和观众所期待的角色形象保持一致。它要求表演者严格遵循社会公认准则或客观社会期望,外部社会属性被置入互动情境内部,个体所传递出的自我信息不仅需要与情境适配,也需要符合社会的客观要求。然而,每个个体都不可能只存在唯一的社会属性,因而外部社会的渗透必然导致同一个体的多个不同角色同时存在于情境之中。不同的角色之间并不总能协调一致,因此,表演者需要区分前台和后台。
当不合时宜的闯入、失礼和当众吵闹等现象发生时,表演者所感受到的“不可避免的窘迫”正是因为这些行为打破了前台与后台、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空间区隔,换言之,暴露了本应只有一个角色的个体实际上具有多重角色的事实。这个秘密的揭穿会导致表演的崩溃,空间的破坏带来情感的后果,于是,“通常会出现令人尴尬的结果”,崩溃的舞台成为“尴尬和不协调的来源”,表演者本人则“感到所谓的羞耻感”。换句话说,紧张出现了。个体开始慌乱,不安,尴尬,而当这些窘态被其他互动者察觉到时,互动秩序便会遭到更进一步的削弱。
为了避免崩溃的出现,戈夫曼提出了针对表演者的防卫措施和针对观众的保护措施。处于日常舞台中的表演者也会通过角色外活动来进行一种 “普遍而不外显的沟通”,包括缺席对待、上演闲谈、剧班共谋和再合作行为四类。角色外的活动显示出,表演并不是构成表演者自我的全部事实。在不影响舞台呈现的情形下,作为表演者的个体发展出了各种与表演活动无关甚至相反的行动,显示出自己并非完全等同于舞台上的那个人。这些活动说明,舞台框架所规定的那种表演性自我并不是紧紧扣合在个体身上。
拟剧论视角揭示了“情境化自我”的第一个侧面,即个体有能力随着情境的变化发展出生动可变的自我,并“将个体人格-互动-社会整合进一个框架中”。但在这里,个体对互动规则的把握和调整停留在相当初级的阶段,表演者调整自己的状态仍然是在为表演本身服务,在后台的能动是为了更好地进入前台,在角色外的活动是为了更好地进入下一次的角色表演。个体的自我只是从角色中来,到角色中去。在后续对角色距离的讨论中,戈夫曼将进一步分析具备空间属性的情境化自我,如何借助紧张管理的维度打破角色-表演者在形式上的二分,从而作为一个整体性自我在不同的世界间游走。
(二)角色距离:自我对情境的再定义
角色外活动是个体与角色拉开距离的初级形式,在《角色距离》中,这种类似“反抗”的行为被戈夫曼进一步放大:个体表露出对角色的不满、做出与角色信息不一致的行动也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目的,而是因为身处情境之中,受其在情境中所处位置的影响,带有情境的固有属性。在这里,情境展开了作为社会空间的维度。
.png)
角色距离图式。来源:bing。
齐美尔在《社会学》第九章中援引康德的说法,将空间理解为聚集在一起的可能性,而空间的三个基本要素则是位置、主体和两者之间的联结关系。与物理空间不同,只有互动才能把人与人之间的空白填补和装满,才能赋予空间社会学意义。通过强调个体在情境中的位置和情境在系统中的位置,戈夫曼勾画出自我的一幅整体图景。自我不是孤立地进入互动,而是带着其背景意涵一起进入。因此,个体的互动行为与空间不可分割,自我与情境相互建构。
与传统的角色理论不同,戈夫曼在《角色距离》中强调,角色分析的重点在于将角色放置在具有空间位置属性的情境中,考察在不同的位置中,角色如何发生变化。个体所面对的不是单一的位置或孤立的角色,位置的概念包含着一个人在生活中的选择和处境,他的关系、倾向与行为,以及围绕着他的各种义务和期望,正是它们指导着他与他人进行互动。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他在情境中的一幅整体图景,这幅图景成为个体自我的背景,自我不会孤立地、单独地存在,而是带有环境的注脚,作为整体进入到情境之中。
围绕“行动即存在”(doing is being)的概念,戈夫曼指出当个体进入系统中的某个位置时,实际上已经有一个自我在等待着他。这个自我已经内在地具有被系统赋予的角色特性,个体必须努力使自己在情境中的行动呈现出与这些特性相符的印象,传达出与角色一致的自我形象。戈夫曼所描绘的“被情境定义的自我”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情境化自我”。前者所指的实际上是角色,无论个体进入情境与否,它都稳定地居于情境内部。
而情境化自我指的是随着个体在互动中依附、适应甚至破坏的行为而不断摸索发展、流动变化的特质本身。无论在各种情境中自我以多少种不同的样貌出现,真正反映自我的都不是其所化出的角色,而是能够变化调整的能力。个体看似是在维持情境定义,实际上是在维持他的情境化自我。自我的变化和不稳定性成为情境内唯一“稳定”存在的东西,它始终根植于作为空间的情境内部。
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流露出对角色不满或抵触的行为就是戈夫曼所指的角色距离。必须接受上司命令的下属也常常通过愤怒、抱怨、冷嘲热讽、戏谑、心不在焉等方式和自己作为下属的角色拉开距离,暗示自己并不满意工作安排;实习医师会通过有意怠慢和心不在焉的态度表达对自己在手术室里低下地位的抗拒。在这些例子当中,个体仍然进入了情境之中,但是是以一种并不归属于情境、可以随时抽离情境之外的方式进入的。角色距离并不意味着个体直接彻底抛弃了这一角色,而是为了表现出他有维持任何角色的能力。角色距离的概念帮助我们剖开角色的外壳,展现出个体在互动中与情境相互塑造、相互生成的可能性。
角色距离实际上破除了“角色”的概念,个体并不是紧紧蜷缩在某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主要角色躯壳内,不管他所身处的情境本身多么狭窄、多么具体,人们总能在其中看到不同身份的交织(a dance of identification)。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就像“守卫着帐篷门”一样尽职尽责地扮演着这一舞台所要求的角色,但与此同时,他也会“打开门让他的亲友们偷偷溜进来”。个体在他的自我周围构筑起帐篷门划定了自我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实际上也重新定义了情境的空间形状。情境的弹性被扩大了,自我反过来缔造了一个总能承载其变化的空间,这一空间起初限制了自我的范围,最终却成为它行动的安全网。
正因为系统内的规则秩序明确存在着,个体反而能够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来表达出自我之间的不一致,表达出对情境和秩序的不满。这些行动看似对秩序形成了挑战,实际上却是对作为互动者的自我以及对情境系统的保护。戈夫曼的“角色距离”概念不是强调个体具体的抗争行为,而是情境化自我总会做出抗争行为这一事实本身传递出的信息。个体有能力在既保护自我又不破坏情境的情况下,游走于互动世界和外部社会世界的缝隙之间,对情境进行再定义,为他的自我挣得一丝自由的空间。角色距离使得情境成了自我的缓冲之地。即使发生了意外,角色距离也能够发挥出情境化自我的弹性,事件能够得到缓冲,个体的自我也不会被置于彻底破坏的绝望境地。
因此,自我的特性由其所内在具有的情感和空间属性共同塑造,行动者所身处的情境恰恰也是其能在情境中进行改造的原因。作为空间的情境是“被互动所充满”的空间,它丰富了互动者的内涵,也被互动塑造出新的形状,而并非抽象和坚硬的实体。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情境内外的裂痕原本是导致紧张和角色不一致出现的原因,现在却成为个体可以利用的缓冲之地。自我作为角色的第一层含义是情境赋予的,个体则透过角色距离在它的基础上对自我进行重新定义,这一能动过程最终反过来重新定义了情境本身。自我与情境之间构成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紧密关联,位置、主体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情境和自我的相互塑造中不断加深,形成一种变化中的和谐统一。
(三)次级调适:自我的新生与空间的再造
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可以通过角色距离对情境进行再定义,从而激发空间的弹性,重塑情境的形状。而在《精神病院》中,戈夫曼描绘了以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形象出现的情境的极端状况:情境的空间属性被大大削弱甚至完全抽离,成了真正僵硬断裂的外在框架,将个体与外部世界隔绝。但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戈夫曼表明,情境化的自我(situated self)开始利用情境中的规则和秩序,通过运作系统(working the system)的方式在僵硬的空间内部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空间,在对制度的反抗中,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情境化自我诞生了。
在戈夫曼定义的全控机构里,“一群面临着相似处境的个体在此生活和工作,他们长时间与外部世界隔离,共同过着一种封闭的、被正式管理的生活”。全控机构的系统首先会通过一套奖励与惩罚的制度一步步剥夺个体的能动性,通过羞辱的方式迫使被收容者做出与自己原本认同的自我观念截然相反的行动,个体所处的空间领域被不断压缩,属于个人的物品被剥夺。被收容的个体只能在机构人员的密集管理下生活,机构以一套制度化的方式运作,而个体之间的互动则被批量化、形式化地对待,个体的能动性被剥夺,情境的独特性和弹性也被抽离。
同时,机构还会污染个体的互动关系,也破坏了被收容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依赖和能够支持的互动基础。在全控机构内,被收容者所生活的不同场景和空间之间也失去了区隔,在某个情境中特定的行为也会作用于另一情境中,不同情境中行为不符的现象则会直接暴露出来,造成被收容者的羞耻。于是,个体失去了对自我的认同,也失去了对所处空间的理解和把控。一言以蔽之,机构就会压制情境化自我能够诞生的根基。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然而,自我的内在生命力即使被机构深深压制,却并没有完全消失。戈夫曼论述了一种比角色距离更进一步的次级调适行为(secondary adjustment)。机构要求被收容者对系统秩序完全服从,但自我内部的情感属性仍然在发挥作用。个体的第一步尝试仍然是设法与“精神病人”这一角色保持距离。通过定向地、有选择地在活动中投入自己的精力,个体暗中表明了对机构的反抗态度。系统总是试图将成员塑造成某种特定的自我,而成员则通过不按照被制定的存在方式行动(而不是不从事活动本身)来表达出自我调适,将自己从一个机构官方版本的自我中抽离出来。
病患的这种 “社会化”也被戈夫曼称为自我的“去道德化”。个体会开始配合医院的治疗,并学习如何在机构内部的严苛条件和等级体系下生活。自我能够被剥夺和重塑,也能够在全控机构内不断地弹性变化,去迎合和适应机构的各种要求,来为个体争取一个相对能够维持下去的生活空间。建构自我和摧毁自我变成一种游戏,自我是向外开放的,随着外界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而不是稳定和一成不变的。这种尝试虽然没有完全恢复个体在外部社会生活中曾具有的丰富内涵,但仍然将他从被机构压抑和封闭的状态中释放而出,不满与反抗的情感动力使得个体重新将自我向外敞开,为次级调适和运作系统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第二步,被收容的个体发展出了一套运用未经授权的手段,达到未经授权的目的,从而规避组织的要求和期望的行为,即次级调适。运作系统(working the system)是进行次级调适的典型方式,被收容者会利用机构中的现存的资源为自己谋利,或在了解系统运作机制的基础之上利用系统的漏洞来确保自己能够获得更好的资源。
被收容者为自己谋取的利益或资源包括一些基础的个人需要、额外的个人享受,例如利用被安排打扫卫生的时间在储物间享受短暂的休息。同时,个体会进行打架、斗殴、酗酒、自杀、赌博、违抗、同性性行为、集体骚乱、逃脱等被明确禁止的活动。与此同时,机构本身的复杂面向也在次级调适中展现出来。机构人员与被收容者之间可能会达成默契,前者默许某种形式的捣乱,以使后者在合理的限度内发泄对不公正处境的不满。作为一种次级调适的捣乱更像是机构的安全阀,赋予刚性、严苛的机构情境以某种柔韧性。
次级调适行为的原初动力是个体内部情感属性所激发的反抗。这一情感并不单一存在于某一个体身上,而是机构内不同个体所具有的一种普遍的人性道德基础。个体与个体之间各自独立的调适行为在互动的结点相遇了,他们发展出互相给予、沟通、分享的合作系统,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形式,它是一种包含着社会理解的交换。双方用来交换的不是物品,而是关心、恩惠等社交关系。机构内部社会交换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基础——组织中团结的纽带关系(bonds of solidarity),个体发展出一套与他人建立关联、保持连接的行动循环系统。
正如莫斯的礼物之灵一样,个体在次级调适中建立的纽带关系也是给出自身的一部分,拿取他人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个体再一次将自己置入与所有人共同构建的普遍连接之中。在机构的压迫和剥夺中,个体却依靠自己的能动性,实现了人与人之间最原初的混融,将自己整合进秩序内部,通过自我的新生,在情境内部创造新的空间形式,并反过来为自我赢得自由的余地。它是机构情境内部个体行动的起点和终点,以这种方式,人与他人的灵魂终于再一次在互动中流通了起来。即使其自我正处于最极端的处境中,个体仍然无法抑制这种走出自我、走向他人的渴望。
紧张管理正是戈夫曼对涂尔干和莫斯关于神圣个体概念的推进。紧张的出现正源自涂尔干和莫斯未能解决的问题——圣俗二分在个体内部永恒的撕裂。在古式社会中,个体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集体仪式中感到兴奋和狂热,也不能言说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回礼。但是,现代个体却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羞耻的存在,以及羞耻在互动中对自己和他人产生的作用。
由此,能动性成为戈夫曼的重要概念,他注意到陷入互动困境的个体发展出了一套紧张管理的方法,依靠能动性不断调适自己在互动中的行为,这种调适同时也依赖着个体对他人情感的体察,通过走入他人的行动世界来重新拓宽自我的意涵,催生出一套以礼物交换为原型的新交换系统。流动在这一循环系统中的情感成为了新的玛纳,指引着个体去创造、触摸、分有专属于他们的神圣力量。至此,通过表演崩溃、角色距离、次级调适,戈夫曼笔下的现代个体从情感维度上一步步展露出其神圣属性。
在这里,戈夫曼从情感的角度在现代社会中延续了涂尔干的神圣个体,但将个体与他人普遍连接的不再是涂尔干笔下的激情与欢愉,而是内在的痛苦、不满与反抗的本能。不同于原始社会中的社会之力,个体和情境之间的张力带来了现代自我最底层的焦虑。自我的焦虑在情境中弥漫,并引导个体进行能动的反抗,通过与紧张的对抗,自我才得以从被压抑的状态中重新浮现生机。在不断对抗的过程中,自我不断被加深和重塑,并最终激发出人之为人最深处的创造力与生命力。
紧张状态实际上是现代性个体最基本的情感状态,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氤氲在常人互动结构最底层的焦虑不安在污名者身上被极端放大了。污名者不得不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将他已经受损的自我暴露在尴尬的情境之中。然而,无论污名者如何努力,他们的情境化自我都无法像常人一样与情境进入相互建构的良性循环。污名者在情境中的恶性循环过程从反面指出,缺失了神圣性的个体不再能发挥自我的情感与空间属性,便再也无法将自己整合进情境系统之中。我们亦可以说,《污名》从反面论证了情感的神圣属性。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借由污名者的绝境,戈夫曼点出了互动的真正困难:似乎无论个体如何努力,弥漫在互动情境中的威胁因素都不会消散。尴尬总会出现,羞耻始终处于个体心中,甚至越是试图通过行为来避免羞耻的发生,羞耻就越有可能发生。戈夫曼在《污名》的结尾告诉我们:“是情境而不是人变得岌岌可危。”当我们沿着情感的脉络一层层剥开互动的外壳后,戈夫曼向我们揭示出互动本身的悖论:困境和风险总是内在于情境之中,不存在永远和谐统一的互动系统,但情境和情境中的互动者却必须为维持互动秩序的稳定付出永恒的努力。悖谬的是,这种努力本身又会给情境系统带来新的威胁。
个体与情境内在的张力指向的是个体多重自我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体、情境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张力仍然需要放在自我的空间属性下进行理解。下文将从空间的第二层视角——边界——出发,继续完善空间属性在互动中的作用,通过互动膜的概念,探究作为“边界”的空间对个体自我施加着怎样的影响。互动膜的分析将帮助我们理解内在于互动情境中的悖论,以及张力背后的原因与现代个体的根本处境。
.png)
紧张管理从情感的维度切入,指出自我内在具有情感和空间的属性,这种属性反过来将情境扩展为具有弹性的可变空间。戈夫曼接下来在“边界”这一空间的另一维度上指出这种弹性所需要依赖的前提,即情境外部包裹着一层互动膜。它划定了情境内与外的边界。与其说互动膜所保护的是情境本身,不如说它保护的是这内外区分的存在。通过无关性规则和转换性规则,互动膜将可能威胁情境的因素排除出情境之外,又将能够帮助维持情境秩序的外部因素引入情境内部。这层位于边界的滤网使得情境得以不断变化,并将能动的个体自我安全地包裹其中。
正如涂尔干用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的概念来理解现代社会分工中个体与集体如何重新相连一样,戈夫曼在他的互动理论中也引入了有机体的比喻。作为构成生物有机体的基本单元,细胞的外层会有一层薄膜,即细胞壁。这层薄膜能够把细胞与其所处的外在环境隔离开,确保外部环境中的所有成分只能有选择地进入细胞内部,正是这种选择的功能决定了细胞的弹性和健康。戈夫曼认为日常互动的周围也存在这样一层细胞膜,即互动膜,正是这一概念帮助我们走入了互动的核心问题。
在引入互动膜的视角后,我们可以看到,与其说互动者维持的是互动情境本身,不如说是在维持这层弹性薄膜所代表的界限。真正重要的不是互动世界或外部世界,而是两个世界的交界之处。正是这一界限的存在带来了紧张,开启了互动行为的流动与循环。互动膜标记出两个世界之间的交界处,作为一张滤网,它对内部和外部属性的筛选遵循无关性规则和转换性规则。无关性规则(rules of irrelevance)确保了情境中的互动者与和与当下情境无关的属性、人员、事件保持距离。情境活动本身是互动的焦点,它在互动者周围设置了互动膜这一屏障,把互动者同外部世界的许多潜在意义隔离开。假如没有互动膜,互动者就会因为活动目标过于广泛、漫无边际而不知道如何恰当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而据转换性规则(transformation rules),互动膜会根据情境互动的需要进行筛选,允许一部分外部属性渗透进情境中,其目的是维持情境活动的良好运转。当外部社会中的属性穿过互动膜这层滤网进入到情境中时,这些属性也会因为互动的特点而发生改变。转换性规则指向的是外部属性在情境中所发生的变化,它既告诉了互动者哪些行为不能做,同时指导互动者按照被情境认可的标准行动。
戈夫曼以游戏这一互动情境作为例子,向我们指出当良好的互动秩序得以维持时,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实际上有哪些因素已经由互动膜帮我们过滤出来,排除在互动之外。无关性规则(rules of irrelevance)指的是在游戏情境中,通过排除与游戏无关的外在因素,互动双方得以从同一位置进入情境,同等地投入到游戏中,享受游戏的乐趣。无关性规则首先排除了游戏中物质材料所带有的外部特性。游戏在一系列事件和情境的周围设置了一种框架,这一框架决定了处于游戏内的个体应该如何看待情境内发生的事件,而将互动者与游戏外部的普遍定义隔离开,例如在监狱的围墙游戏中,围墙被视作游戏的棋盘而不再是它本身。
参与游戏的互动者身上的外部属性也会被无关性规则排除在外。为了保证互动者之间的平等,首先需要排除个体身上的社会属性,例如财富、地位、名望等。正如齐美尔指出的那样,社交是一种更加纯粹的真空中的游戏,与外部社会的复杂生活脱节,人们在社交情境中假装彼此能够平起平坐。无关性规则是禁止性的,转换性规则既是禁止性的又是促进性的,它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向我们表明外部属性在经过互动膜之后,在外形上受到了怎样的整饬。
如果说在紧张管理中,自我和情境的相互建构是从自我内部开启的,那么互动膜的存在则意味着在自我外部情境施加影响的机制和前提。在走出自我的过程中,除了自身的能动性之外,个体也依赖着被互动膜这一边界所包裹的情境结构。自我带着一幅包含情感和空间的完整图景走入互动中,但内部的能动性并不足以完全激发情感和空间属性的作用。在情境化自我与情境空间相互定义、不断循环的过程中,赋予情境弹性的并不仅仅是自我本身,空间的边界也通过筛选、转换和流动对情境进行了改造,最终使得情境如同有机体一样生发和成长,与情境中的自我一起碰撞出新的生命力。
通过梳理互动膜的作用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戈夫曼所描绘的情境空间与莫斯笔下的巫术空间高度相似。首先,在地资源(realized resources)是巫术环境与情境空间得以成立的共同前提。在莫斯看来,巫术环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它需要从普遍、世俗的日常环境中被单独划分出,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一环境现有的构成要素组成了巫术所需的所有条件,直接成为巫术实施的基础。禁忌的边界也是为了守护巫术环境的特殊性才产生,人们甚至为此专门形成了进入仪式和结束仪式,以对这一空间进行严密的保护与区分。

《巫术的一般理论》
在分析互动的形式化过程(formalization)时,戈夫曼同样强调了互动情境中现有资源的重要性。互动仪式的产生必须依赖情境中早已广泛存在的物品、设备等在地资源(realized resources)。互动者只能通过手头现有的材料,在情境现有的条件下完成情境的要求。互动空间里的在地资源限制和影响着个体的行动,正因如此,转换性规则才凸显其必要性,通过引入外部属性,转换性规则引导着互动空间内部对有限在地资源的分配,从而影响着互动仪式的实现方式。
其次,巫术环境和情境空间的概念在形式上遵循两种相同的规则:一是在内部与外部世界之间划分清晰的边界,二是在内部世界之中也再度细分出新的多重空间。一方面,正如各种禁忌的规则在四周把守着巫术空间一样,互动膜也在互动情境的四周设立了屏障,无关性规则如同禁忌一样,将与互动仪式无关的要素和人员严格排除在外,再由转换性规则筛选出有资格进入的要素。
另一方面,不同的人根据其职能在巫术环境内部处于不同的位置,从而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力。在巫术仪式中,不同的参与者通常以祭坛为中心形成一个同心圆,巫师离中心最近,祭祀者在其后,普通群众则处于最外围。互动仪式也同样如此,必然有人处于情境内焦点活动的中心,引导活动的发生与持续,也总有人会被嘲讽和打趣。在其他人用破坏性嘲讽等方式进行紧张管理、施展互动膜弹性的魔力时,少数人则“不得不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在这两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将戈夫曼的互动情景理解成现代社会的一种巫术空间。在作为巫术空间的互动情境内,具有特定意义的事件和使事件得以发生的角色,共同将互动构筑成一架意义引擎,创造出一个独立的世界。穿过禁忌的边界进入巫术环境的事物“要么禀赋中便带有感应仪式的性质,要么就被赋予了这种性质。这种性质也影响到所有的姿势和语言的一般基调”;同样,通过互动膜渗透进互动情境的因素也会在进入互动的意义体系后改变自身的特点,呈现出与互动整体一致的情感色彩,使自己的姿态和语言适合当下的语境。在互动的空间里,自我与情境世界不断作用与反作用,这一空间于是在日常生活的连续活动中建造出一个封闭的、自我补偿的、可以自我终止但又相互依赖的内部循环系统。
在戈夫曼对不同互动情境的具体分析中,互动作为空间的属性在文本中一直有明确的线索。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为我们所熟知的前台和后台的区分意味着后台成为个体生活世界中的巫术空间,它显然带有禁忌性:除了个体自己之外,他人被严格限制入内,在后台这一空间里,作为表演者的个体能够进行与表演的印象不相符的行为。角色外活动也必须在后台完成,个体在这里为其自我松绑。不同剧班和后台之间的来回穿梭表明,情境内部并不是一个空旷单一的房间,不同的细分空间随着自我辗转腾挪的过程填满了整个情境,多重空间被嵌套在情境内部,随着个体位置的变化、个体与他人关系的变化、个体自我属性的不断膨胀或收缩,它们有时重叠勾连,有时逐渐疏远,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塑造着情境的形状。
而在全控机构中,次级调适行为的发生同样必须依赖于边界明确的空间区域,并在机构内进一步划分出不同的空间层级。在机构内部有限的条件下,被收容者依据在地资源的不同条件,在情境内部划分出功能不同的多重空间,个体的独立空间首先帮助个体脱离被机构定义的精神病人的角色形象,重新建立与自我的连接;随处存在的藏宝地(stash)扩展了自我活动的界限,让个体得以将封闭的自我向外敞开。内部的多重空间一步步帮助被压抑的自我走出隔绝孤立的绝境,重新激发出能够担负起反抗行为的活力。
通过边界的划分和内部多重空间的生成,自我被具象为一种空间化的表达,储存私有物的空间成为自我和主体性的延伸。正如涂尔干和莫斯强调情感与仪式发生的空间密切相关一样,戈夫曼也强调全控机构内的个体附加在上述空间中的情感连带。对被收容者来说,被机构剥夺空间就是被剥夺了自我,当他们为自己赢得哪怕最微小的空间时,这些区域本身就承载着他们对自我的依恋(attachment)。
他们将对安全感的期待和渴望注入空间环境中,只有在这种情感的基础上,自我的能动性才能冲破机构的压抑得到发挥。如果脱离了藏宝地这一空间,被收容者运营出的地下运输系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地下生活也无法展开。正是因为首先划分出自我与外部的边界,次级调适的具体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又因为自我内部同样具有多重空间,互动才能在整合了空间内资源和要素的前提之下,一步步重新产生活力。
作为巫术环境的情境空间在两个维度上对互动中的个体施加着影响。一方面,互动膜划分出情境内外的边界,将互动者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互动膜的筛选机制在这层边界之内形塑着自我。同时,个体在情境内部也处于不同位置、不同关系、不同等级中,每一层空间又承载着不同的自我意涵。两种空间维度分别揭示了个体与情境的张力,以及个体内部多重自我的张力。这两层相依共存的张力最终导致了互动的悖论,这正是戈夫曼在现代社会中对人性二重性的重新审视。只有拨开它们的嵌套结构,我们才能理解情境如何在孕育出张力和矛盾的同时,又为个体提供了突破和改变的力量。
.png)
至此,我们已经发现互动情境双层嵌套的空间结构。情境与外部社会边界分明,但它们并不是完全孤立隔绝,而是通过互动膜相互勾连,相互渗透。然而,无论渗入互动情境中的外部社会因素有哪些,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即它们既需要为平静的互动带来挑战,注入活力,甚至引发一些冲突的可能性,但同时又需要被仔细保持在互动膜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能真正造成破坏。互动的这一悖论揭示出个体内部存在的永恒张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戈夫曼成为涂尔干的现代继承者,在宗教消逝的日常生活中重寻人性二重性之所在。
戈夫曼认为,当个体感受到情境中的压力和紧张时,破坏性嘲讽(subversive ironies)是一种最有可能出现的应对方式。在互动中,破坏性嘲讽将一些最无法忍受的、受到正式的转换性规则排斥的事件用一种轻描淡写、冷嘲热讽的方式提出。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原本应当被无关性规则排除在外的属性以婉转弹性的方式被引入了互动中,原本会损害自我和破坏情境的事件以嘲弄的形式被化解了。换言之,“嘲讽”的形式为从整个情境背景中产生的情感开辟了表达的出口,让个体得以“脱口而出”,但同时又把真正想表达之物充分地伪装了起来,以保证互动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
从个体与情境的关系出发,我们最终来到了空间与情感的交汇之处。破坏性嘲讽在情感与空间两个维度上建立了联系,紧张管理实质上正是运用了互动膜的转换性规则。在紧张管理的过程中,看似矛盾的互动方式只有在互动膜的保护下才得以实现。在这层包裹之中,紧张管理与破坏性嘲讽可谓是异曲同工:它们都是以破坏情境的方式维护情境,以攻击自我的方式恢复自我的弹性。无论是表演补救、角色距离还是次级调适,都以看似不符合互动中既定规则的方式重新塑造了互动。由外而内,互动膜以纳入威胁因素的方式维护了互动;由内而外,个体的紧张管理以破坏稳定的方式维护了互动的稳定。在这一层面上,被互动所连接起来的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展现出一种内在一致的矛盾性。
当我们沿着情感和空间的脉络一层层剥开互动的外壳后,我们发现,情境几乎从诞生的一刻起就天然具有“产生紧张”的可能性,互动者不得不发展出专门的紧张管理行为来应对这一必然降临的局面,而紧张管理恰恰是以一种看似在破坏互动秩序的方式来维持互动秩序。于是,戈夫曼捕捉到了情境中始终存在着的“双重主题”(dual theme):情境空间与外部空间、个体自我内部的多重空间都在“情境”的语境下共生,它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必然导致互动的矛盾和悖论,而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必须以看似相反的方式完成。
这种双重主题最终回归到涂尔干所说的人类二重性(homo duplex)之上。 涂尔干已经看到,在个体内部“具有一种类似双重重心的东西。一方面,是我们的个性,特别是它所依赖的我们的身体;另一方面,是我们能够表达超出我们自身以外的东西的一切”。如果说羞耻、紧张等情绪的诞生正是来源于“我们的个性”和“我们的身体”,那么,个体通过其能动性所发展出的紧张管理技术则反映出蕴含在我们自身之中的“自身以外的东西”。
这种内在的二重性也意味着个体内部必然的痛苦与撕裂。它们真正对立,相互矛盾,相互否定。正如涂尔干所说,我们的快乐永远不会是单纯的,其间总有痛苦,这是由于我们无法同时满足体内的两种存在。这种不协调,这种永恒的自我分裂使得我们既伟大又悲惨。 而在这种分裂之上,个体所追寻的更高的道德行为必然意味着牺牲,“我们可以毫不抵制、满怀热情地接受这种牺牲,即使这不过是一阵喜悦,牺牲也同样是真实的”。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个体所追求的这种牺牲,必然导致一种永恒的苦行,苦行所追求的正是痛苦本身——涂尔干认为这种矛盾永远不可能完全解决,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既完全属于自己,又完全属于他人。
互动中的紧张和紧张管理正是这种苦行的现代表现。如同痛苦永远存在于个体内部一样,紧张永远存在于情境内部。个体在情境中的能动行为,实际上仍然是一种牺牲。作为个体与结构的交汇处,互动成为这种二分的连接点。在互动之中,对羞耻的回避既蕴含在我们的个性经验之中,但这种个体情感却在互动过程中不断丰富,重新定义,扩展了自我、行动和情境的边界,共同进入一种彼此联结的情感状态中。
以紧张为基础,戈夫曼对涂尔干神圣性脉络中的情感意涵进行了转向。涂尔干认为,所有的仪式和膜拜都是在歌唱、舞蹈和戏剧表现等活动中进行的,根植其中的是“愉快的信念,而不是恐惧和压抑”。然而,狂喜和激情只能在仪式活动中得到短暂的维持,如果想要持续与神圣性建立连接,原始人只能借助于图腾和对仪式周期性的复现。戈夫曼开辟了现代人把握神圣性新的进路:“在当代社会,为超自然实体的替身举行的仪式到处都在衰败……拥有一小笔神圣的遗产……剩下的……只有人际间的仪式。”

Scalp Dance by the Chualpays Indians, by Paul Kane, 1856
因而,当宗教仪式从特殊的庆典转入日常生活时,激烈但短暂的情感难以维系,继而被强度更低但长期存在的情感状态所取代,而这正是戈夫曼笔下弥漫在日常互动中的负面情感的真正意涵。作为互动的情感基础,羞耻和紧张的出现也与现代社会的特性密不可分。正如涂尔干在1914年所说的那样,“我们还在不断经受着焦虑与忧伤的煎熬。谁未曾感到在社会的深处,一种紧张的生活在滋长”。一百年来,这种紧张和焦虑在现代社会中愈演愈烈,乃至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基本状态。
作为涂尔干的继任者,在人性二重性的划分之上,戈夫曼没有简单停留在神圣与凡俗的断裂之中。在涂尔干那里,神圣与凡俗的二分带来的是个体与社会的断裂,但在戈夫曼笔下,这种断裂所造成的紧张却孕育出新的共性与和谐。涂尔干认为,“我们可以不确定地接近这两种状态,却永远不能完全实现它们”。但戈夫曼却通过对个体内部自我的关照给出新的答案:圣俗二分不仅意味着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也意味着存在两个世界的交界之处。个体不一定要在神圣或凡俗中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也可以在两者的边界之中长久地游走。
作为情感的羞耻绝不是一种非理性的、破坏社会规定的冲动,而恰恰是秩序行为的一部分。自我是这样一种最为违反常识之物,他在最封闭之处才能敞开,在最可能被排斥之时建立连接,在最世俗之地孕育最神圣的存在。个体与他人正是在这一过程创造了神圣之物新的价值,然后又将神圣之力重新认领。
我们不得不带着这种认识,重新回到神圣性的起点来检视“互动”一词更广阔的含义。
互动正因其悖谬和矛盾才成为真正的互动。个体体会过自己的羞耻,也见证着他人的羞耻;个体亏欠着他人,也被他人亏欠。在莫斯笔下,礼物交换实际上是借助礼物与礼物的流动完成人与人的相通,并在普遍的期待和焦虑中不断流转,最终达到人与神的共通。而在戈夫曼这里,面对面互动则是借助自我与自我的碰撞,完成人与他人的连接,依托羞耻和紧张的普遍情感不断开启下一次能动的循环,直至达到人与他者、人与情境、人与空间的混融。
在集体欢腾中,社会作为一种可被共同感知到的普遍之力降临;在礼物交换中,社会在给予与获得的循环中作为灵力流动着;在情境互动中,社会则在个体发挥其能动性,运用各种技巧对他的自我进行辗转腾挪的过程中,在流动变化和不稳定性中展现出真实的面貌。正因为个体没有完全服从外部的社会秩序,在感受到内在张力的同时,他也才真正激发了自身的神圣之力。这种张力在多重空间的嵌套中最终浮现,然而,对戈夫曼来说重要的不是要去探究清楚每一层空间是什么、每一重自我有什么特点,真正重要的是这种重叠和裂隙的存在本身。
正如涂尔干所说,“本质上,我们的感觉是个体化的,但我们越是从感觉中解放出来,我们就越能够从概念上思考和行动,我们也就越成其为人”。只有当情感不再是个人层面的“感受”(sensation)时,个体才打开了神圣性的入口,戈夫曼严格遵循了涂尔干的道路,在他笔下,感受被巫术般的精灵之力变成了内化于互动空间中每个人身上的普遍情感,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联结不再是一种由上至下的统治和集中,而是一种从自我出发、升入更高处的解放(emancipate)。只有在互动仪式为他缔造的巫术般的空间里,他才能从这种解放中获得了自由。这一自由让他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个体(individual),而终于成为有人格、有情感的人(persons)。在每个自我享有自由的同时,自由也连接了互动空间内的所有人。在这一意义上,戈夫曼最终回到了莫斯致力于呈现的“总体的人”(l’homme total)。

Magic Flight or Zamfonia, by Remedios Varo
在这种自由的图景下,个体性与社会性是否实现了统一?显然,戈夫曼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已经和涂尔干不同。对涂尔干来说,人的双重性意味着人的存在同时包含有个体性和社会性。社会性处于个体性之外,个人获得社会化、把握社会性的方式是追寻社会留下的印记,通过图腾和其他介质不断重现社会之力。个人和社会并不具有同一性,即使他们都存在于人之上,却始终是截然不同的两面。
但莫斯在论述“总体的人”时,已经将个体与社会相融的概念包含其中。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个人在时间的流动中所进行的活动最终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因此,社会存在才以一种个人命运的方式被个体所承载。个人与社会的混融难以被剥离或分割,因为这种双重性不再清晰明了地外在于人的外部,而是与生俱来地处于个人自身之内。戈夫曼笔下个体永远无法摆脱的紧张和内在张力正源自于此,既然人成为新的神圣之物,人的双重性便转入了他的内部。
但真正影响着个人的因素既不属于内部,也不属于外部;既不是个体性的,也不是社会性的。它们始终是一种在两个世界的界限之间交织穿插的“中间之物”。中间之物的重要性在于,它以非语言的方式实现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交流,他们借助中间之物这一媒介,在进行仪式活动的同时完成了沟通,通过这种内在的交流与沟通,人与事物、人与神才得以在同一时空范围内作为社会实体被紧密联系起来。
在这一前提下重新检讨“圣俗二分”之说,我们发现其最重要的意义不再是区分何为神圣、何为凡俗,而是两者之间永恒存在的交界处。在莫斯笔下,社会在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相融中才成为了可被观察、可被理解之物,它不再是涂尔干所描绘的那样边界清晰,在两个世界的分界处骤然断裂。相反,交界之处孕育出由多种不同关系所构成的圈,它是礼物的库拉圈,也是巫术或献祭仪式的圈。这些圈在社会实体的内部和外部之间游走交织,它们杂糅着外部的因素,如影子般存在于圈子内部并施加影响;它们也承载着内部的属性,在来回穿插的过程中扩大了外延。
交界之处的圈从涂尔干“有机体”的概念中脱胎而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个人的再次成为社会的。所有个人交织而成的体系相互之间密切关联,又在内部共享社会总体的关系本质。涂尔干笔下个体在这里出现了打开的缺口,以交换和流动为基础的关系体系成为开放社会的力量之源。
个体所面临的不是在互动与社会、内部与外部的两个世界中做出选择,而是那道永恒存在的裂缝本身。他们的困境在于如何把握这道边界、维持这道边界,并在缝隙下自洽地生存。在互动膜所包裹的“中间之地”,个人与社会重新混融在一起。一个有机且整全的互动空间重新衔起本应断裂的圣俗交界之地。在这里,个人与社会相连的方式不再是一种被动的整合。身处其中的所有人都共同面临边界与裂缝的存在,他们共享裂缝所带来的张力(而非断裂本身),也正是在共同维系这种张力的过程中,不同的个体才完成了一种新的整合。
如果说互动空间的存在让个人拥有了施展主体性的可能并从而享有了自由,那么这种无法避免的张力则是个人获得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个人不可能永远只置身于互动情境的内部,无论是为了向内推动互动仪式的完成还是为了向外扩大自身与结构的外延,他都必须在两个世界中不断地游走。从形式上看,进行紧张管理的个人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插在两个世界之间,但实际上,紧张和张力带来的威胁无穷无尽,他没有任何方法真正清楚危险,只能永远处于紧张与紧张管理的循环流动之中。这一困境并不意味着个体被压抑和拘束在互动的监狱里,恰恰相反,它迫使个人去直视那道不可见的裂缝,把握它,维系它,分有它,与它恒久共处。只有当个人承认神圣与凡俗之交界的存在时,人才成为了新的神圣之物。
戈夫曼对涂尔干和莫斯的推进也在于此。戈夫曼的互动论实际上要回答的正是涂尔干以降社会学的根本命题:社会何以可能?但他切断了通过重返古式社会而重现神圣性的理论道路。一方面,他继承了涂尔干对神圣性的思路,指出连接个体和社会的仍然是神圣之力。但戈夫曼没有回到古式社会的宗教体系中,他没有停留在原始宗教、图腾和狂欢的原始情感中,也没有借助后期涂尔干和莫斯都很看重的人类学方式,例如亲属关系、礼物交换或是身体,而是直指人性深处的这些情感在现代社会中借助互动所进行的全新表达。个体的行动不是为了弥合缝隙,也不是为了在两个世界中做出选择,而是通过自身的能动行为,与他人共同维系裂缝的存在。在共同维持裂缝、遭遇张力的过程中,个体从孤岛上的神龛中陨落,然后在相互融合的交界之地作为现代的神祇重新升起。
在互动论中,个体依靠内心深处的牺牲仍然如信仰宗教般维系着整体的互动结构,但不同于原始宗教,这是一种由现代社会孕育出的公民宗教。涂尔干认为个人的情感与普遍的道德之间存在必然的对立,戈夫曼却向我们揭示出,个体的情感也同样是道德的。在现代公民社会中,个体通过紧张管理这一日常生活中的苦行重新成就了神圣性。个体不需要依靠进入纯粹的宗教生活去寻回神圣之物,在现代社会,这种神圣路径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为神圣性不在别处,而在个体的内心之中。因此,最庸常平凡的日常互动却成了孕育神圣性的空间。
戈夫曼的理论洞见成为符号互动论的理论基石之一。符号互动论认为,聚焦互动是因为“社会是个体日常互动的产物”。它帮助我们理解个体如何互动并创造符号世界,以及这些符号世界如何反过来塑造个体行为的参考框架。带着神圣性的视角,我们才能真正看到这一框架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社会是如何通过个体间互动而得以维持和被创造的。符号互动论发扬了戈夫曼对现代神圣性的理解,不仅基于情感,更基于社会日常生活语境中所有行动背后的含义,对它们的共同理解形成了新的共同性,成为社会中的个体行动的新前提。于是凡俗与神圣的二分不再像两条平行线,神圣的光晕同样照射进日常生活之中。
.png)
通过对戈夫曼早期互动论文本的梳理,本文将戈夫曼的互动理论,作为社会理论中神圣性研究的一部分,放到了涂尔干和莫斯开启的脉络当中。在莫斯的礼物交换中,个体有一种被循环排斥在外的焦虑,这种情感底色在戈夫曼笔下被具体为现代个体所普遍感受到的羞耻与紧张。给予他人尊重、维护他人的脸面,实际上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脸面。如果这一互动秩序遭到破坏,尴尬和羞耻就会在情境中不断滋生和蔓延。
在戈夫曼看来,驱使个体做出行动的不是对喜悦、兴奋等正面情感的追逐,而是对尴尬、羞耻等负面情感的回避。负面情感之所以成为日常互动最底层的基础,是因为互动情境中总会出现造成这些情感的紧张。紧张源于互动结构内部所固有的张力,当它被施加到作为互动者的个体身上时,互动者们便发展出一套紧张管理的艺术。个体总是用看似破坏互动秩序的方式来维护互动秩序,而进行紧张管理的行为本身,又总会分散人们对互动中心的关注,为互动注入新的紧张,构成紧张的循环。
互动的悖论向我们展示出互动情境内在的张力。戈夫曼从空间的视角回答了这种张力的来源。莫斯强调力量与环境的密切关联,指出巫术的力量若要真正发挥作用,则必须要求一个特定的巫术空间。借由互动膜的概念,我们看到互动情境本身正是一个这样的巫术空间,它是广阔社会世界中的一个切面,外部社会的属性通过无关性规则被排除在外,又通过转换性规则得以被筛选进入其中,对互动空间内的活动施加必要的影响,帮助个体面对互动内部的张力。
这种空间关系永远存在于个体内部与空间内部,因而互动空间始终处于两个世界交界之处的裂缝之上。这道缝隙既给互动带来威胁和张力,又给予了个体发挥能动性的空间。这种张力放大了个体自我必然具有的多重性,从而导致了互动秩序内在的不一致,同时又要求个体在不一致的背景下寻求一致性,重建个体与他人的普遍关联。因此,以紧张管理为表现形式的能动行为并不能被是个体对结构的反抗,所形成的也不是单薄的“抗争性”自我。
正因互动结构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张力,个体才能享有发挥主体能动性的自由。氤氲在互动空间内部的羞耻的情感底色,其实是因为所有个体都共享着结构性的紧张,共享着裂缝所带来的张力。他们并不寻求消除两个世界之间裂缝的方法,而是有意识地共同维系着裂缝的存在而不破坏互动空间本身。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在感受自我内部的撕裂和阵痛时,才不再是涂尔干所描绘的封闭单子,他们才终于能够向外部敞开,与他人真正地混融。
戈夫曼曾经不断被指责为对人类缺乏真实和具体的理解与同情:“对他来说,人的存在只是无穷无尽的博弈中被操控的木偶。感觉、情感、爱、恨、自我,似乎在任何地方都不曾出现。20世纪60年代,当美国社会越来越狂躁之时,我们越来越难以将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与戈夫曼作品中冷酷的世界联系起来。”戈夫曼的世界真的是冷酷的吗?当涂尔干提出“冰冷的道德解释着各种表象……但让我们感到宽慰的是人们正在寻找出路,并且终将找到”这一论断时,我们无法断言戈夫曼是否已经寻找到现代社会的出路,但毋庸置疑的是,戈夫曼解释世界的方式绝不是一种“冰冷的道德”。恰恰相反,他始终关注缠绕在互动之中的道德纤维。
他笔下的个体在互动世界中将自我腾挪辗转,但他们并不是克里安所指的“道德商人”,而是在面对永恒无法摆脱的张力和困境时,仍旧用能动性去寻找自我突破的边界,生发出新的神圣之力。他们所身处的是行动世界内部张力无休止的循环,因为“互动永远不会停止,就像一场古希腊的悲剧”。但面对这种永恒的悲剧,个体仍然付出着西西弗斯式的努力。他们体会着绝对的孤独,承认断裂与痛苦将永远从内部撕扯自己的肉身和灵魂,但他们没有被这种撕裂所毁灭,而是将撕扯开的裂缝作为向外敞开的出口,寻找新的普遍性和活力。涂尔干承认个体是神圣的,但他们并不天然享有神圣性的力量。而在戈夫曼这里,个体凭借自身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真正具有分得神圣性的资格与能力。
面对涂尔干无法解决的困境,在戈夫曼这里,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松散但具有韧性的耦合关系,不再有清晰的边界,而是在缝隙中混融。个体承受着痛苦,在痛苦中孕育了自由,同时又为自由付出了代价。这种代价正体现在社会对个人所培育的道德情感之中。那么激活社会之力是否只能依靠一种向上的道德情感?即使在古式社会中,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这种单方面培育的局限性。莫斯所描绘的夸富宴已经不再仅仅包含一种单纯向上的情感形态,而是具有内在的竞争性和摧毁性。在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结构中,我们也已经看到与彼此团结同时出现的彼此敌对。这种内在固有的紧张和张力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制度赖以维持的底层基础。

The Potlatch
现代个体一方面体会到伟大的情感和社会之力,另一方面又必然在这种情感中体会着紧张与分裂。在这场表演中,悲剧永远无法被改变,但也正是必然到来的悲剧本身使演出成为杰作,正是紧张和冲突的状态成为激发社会活力的根本方式,构成现代性世界结构的基础。戈夫曼在互动中所勾勒的张力,实际上是西方的社会形态的本质张力。负面情感成为激发社会活力的原因,也构成人之为人的根源和形式。它导向的不是单纯的崩塌或者危机,在这种拉扯中,个体的行动反过来强化和整合了社会的结构与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个体才重新谱写了现代社会的神话。
文字编辑:刘慕齐、曹佳韬、许方毅
推送编辑:周丽敏、毛美琦
文章出处:刘诗予,2024,《北大社会学刊》,第三辑,155-188。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