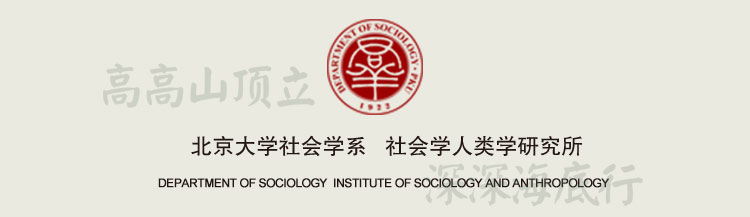明理 | 葉啟政:西方社會學理論思考中的一些“迷思”
西方社會學理論思考中的一些“迷思”
葉啟政
摘要:以“驚奇”與“迸生”作為説明文明源起的特質,佐以強調“人民”(與“大衆”)的概念,使得西方社會學理論論述以概率理論中的常態性來塑造“均質且平等”之“均值人(或平均類型)”的概念、並以之作為形塑具集體性之“結構”概念的基石。同時,強調自由且平等的自由主義思想作為一種信念,卻又促使著西方社會學家普遍相信、且肯定個體或集體施為者(特別個體人)具有自主的主體能動性,因此,構成了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中特有的“結構/行動(施為)”的兩難困境。就此歷史背景來看,此一困境其實是西方人特有之思維模式的歷史產物,本質上,問題是屬於西方人的。
一 前言
絕大部分的人都是生活在人群裏,也就是生活在“社會”裏。這是一件難以否認的經驗事實,在這個一切被高度體系化的時代裏,情形又是特別明顯。因此,僅管人類具有著一些相同的天性,但因身處特定的歷史與文化情境之下,要知道“我們是誰”,就必須注意到我們所賴以生存之整個世界(特別是社會世界)的脈絡。
假如這樣的説法可以接受的話,我們接著有兩個問題必須面對。首先,我們並不能馬上論斷“既然人是社會的動物,他因而必須屈從於社會的結構形式”。在我個人的觀念裏,這樣的説法是有商榷的餘地的,因爲,事實上,人並不只是單純而機械性地對著環境做“反應”,而是有某個程度的能力來操弄著環境。使用中國人慣用的語言來説,人是懂得“造勢”,也懂得借力使力與順勢而焉的,因此,他並不只是在既定的可能範疇下做選擇,而是不斷創造著(包含無中生有的)可能性。
是故,人的自主性並不只是體現於“人有選擇的自由”這個常見的經驗“事實”上面,而是在於因為他有著掌握創造的可能性。其次(也是在這兒我所要討論的主題),既然人的種種行爲是受制於環境的因素,那麼,人們用來解釋現象發生的種種説法的本身,也算得上是一種社會性的行爲了。它如何被呈現出來,一樣地是受制於特殊的文化與社會環境條件的。
換句話説,任何有關人之行爲與社會現象的論述,本身也都是社會産物,因此,它內涵著一些特定的認知與思維模式,尤其是基本的預設命題。以如此的認知架構作爲基礎來審視,顯而易見的,西方社會學的理論論述,可以看成是一種西方特殊文化與歷史背景所塑造的特殊思維産物。它潛藏有特定的“意識形態”,自是可以預期,而這正是在這兒所欲探究的課題。
二 “驚奇”與“迸生”作為理解文明起源的認知基礎
在其膾炙人口的著作《新科學》(Scienza Nuova)一書中,維科(Giambattista Vico)處理人類之本性的問題。對維科而言,人類本性的根本即在於所謂的社會性上面,因爲這是透過天神的許可旨意,人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相對的,自然則是上帝根據自己的旨意而創造出來的,乃與人本身的旨意無關。以類似這樣的兩分方式來肯定社會性與證成人之社會行動內涵自主性,並以之作爲理解世界之存有狀態的優位基礎,一直在西方社會思想的發展史裏據有著重要的地位。
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下,維科有一段循著他自己的假設而衍生的説法,極具想像力,用來表現近代西方人對人類文明之起源的基本認知立場,或許有著一定的意義。他認為,在遠古時代,時間是在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發生洪水之後一百年的某一天,天空終於響著令人驚懼的巨雷,並且閃耀著疾電。維科説,這可能是一種暴烈的壓力首次在空氣中爆發的結果,而所以在這個時候發生,乃因為需要一段這樣長的時間才能讓地球上因洪水造成的潮濕空氣變得乾燥。發出乾燥的氣息,才能使得空氣中有著可以燃燒的物質來産生閃電。
於是,就有少數(一定是最健壯)、且散居在兇猛野獸築巢之高山森林地方的巨人,對這種他們還不知原因的巨大事變深感恐懼和驚惶。他們舉目仰視,才發覺到上面的天空。對此,維科説,基於人心的本性,人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種效果上去。而且,因爲,在這種情況下,按本性言,巨人們是一些體力粗壯的人,通常是用咆哮或呻吟來表達自己暴烈的情欲的,他們於是就把天空想像爲一種像自己一樣有生氣的巨大軀體。對此一爆發雷電的天空,他們叫它烏約夫(Jove,天帝),即所謂頭等部落的第一天帝的意思,而這位天帝有意要用雷轟閃電來向他們説些甚麼話。這樣,他們就開始運用本性中的好奇心了。
維科這樣的説法有一個蘊涵是相當清楚的,那是:驚奇(surprise)乃被用來作為説明當人類處在無知狀態,但卻面臨反常現象時的一種基本心理狀態,並進而用此來闡述文明的起源。維科即提到:“驚奇是無知的女兒,驚奇的對象愈大,驚奇也就變得愈大”、“好奇心是人生而就有的特性,它是蒙昧無知的女兒和知識的母親。當驚奇喚醒我們的心靈時,好奇心總有這樣的習慣,每逢見到自然界有某種反常現象時,例如一顆彗星,一個太陽幻相,一顆正午的星光,就立刻要追問它意味著甚麼”。
於是,“當推理力愈薄弱,想像力也就成比例地愈旺盛”。維科進而提到,驚嘆聲即是在強烈情感衝動之下發出來,而人的文字有些就是由驚嘆詞形成的。譬如,“很可能,最初的雷霆驚醒人們的驚奇感時,天帝約夫的驚嘆聲就引起由人聲發出的驚嘆聲“拍”(Pa!爸);而這個聲音接著又重複成為“pape”(爸爸)!從這個表示驚嘆聲後來派生出天帝約夫這位‘人和神的父親’的稱號,不久凡是天神都叫做父親而女神也都叫做母親;……”
繼而,維科認爲,驚奇帶來的是崇敬感,爾後是火熱的強烈願望。他説:“這三種情感事實上就是天神意旨的三道強光在人們心中所引起的,……”。準此,透過這樣的情感形式,人類的感覺與情欲首先發揮了實際的作用,而“詩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賦予感覺和情欲於本無感覺的事物”。因此,文明的起源狀態是一種具有著詩性的歷史發展狀態。這是歷史性的事實,而這詩性乃由以神爲主,經過英雄轉至以人類爲中心。
職是之故,文明乃起源於人類的心智還完全沈浸於感覺、情愁折磨之時。這個時候,神學詩人就以上述的方式來創造第一個神的故事,而有關天帝約夫的故事就是他們所創造出來之中最偉大的神話故事。人們相信,天帝用一些記號來發號施令,這些記號就是實物文字,而自然界就是天帝的語言。各異教民族普遍相信這種語言的學問即是占卜,希臘人則把這稱為神學,意思就是神的語言的學問。從此,“天帝就獲得了令人畏懼的雷電王國,成為人神之王。他還獲得了兩個頭銜:一個是‘最有權力者’(optimus),意思就是‘最強者’(fortissimus)。另一個頭銜就是‘最大的’(maximus),來自天帝的巨大軀體,即天空本身。……此外,由於使少數巨人們終止了野獸般的浪遊,成了各部落的酋長,天帝又獲得了Stator(即‘支撐者’或‘奠定者’)的稱呼。”
在此,所以引述維科的文明起源説法,不是意圖證成他所提出之論點是絕對經得起經驗事實的考驗,而只是用來凸顯他所指出之“驚奇”心理狀態作爲解説文明起源時所彰顯的特殊文化意義。這使我立刻聯想到柏格夫婦(Peter Berger and Brigitte Berger)在他們倆人合寫的《社會學:一個傳記性的取向》(Sociology : A Biographical Approach)一書中的開始所提出的一些説法。他們説,人類有兩種對“社會”的經驗是基本的:其一是大驚奇(big surprise),另一則是例行事件(routine events),而且前者總是先於後者而呈現著。
對柏格夫婦而言,這也就是説,驚奇是人類到世間來的第一種感覺經驗。他們就這麼説著:“我們可以具信心地假設,當亞當和夏娃的眼神首次相互吸引時,他們是迷亂地震驚著。一個嬰兒的首次微笑仍然有著如此之驚奇新鮮度的特質,一種有如清晨鮮露的經驗。的確,我們早期幼年的經驗,在我們的記憶裏總是保留了一個相當有利的位置,正是因爲世界仍然充滿著那麼多令人震撼的驚奇。”
對照著上面所引述維科的説法,雖説柏格夫婦這樣平鋪直述的敘述,顯得缺乏想像力,內涵更是貧瘠了許多,但是,難道我們不以爲,對人類感應文明(與社會)的基本心理狀態的理解,他們彼此之間是有著明顯的共同文化感應嗎?這個共同的感應即,文明(與社會)乃起源於驚奇的感覺。或許,這樣的雷同相當程度地表示著,在描繪人類經驗(社會)世界的基本感覺時,這樣的文明(社會)起源觀乃西歐人經常呈現的一種典型認知模式。若是,顯然的,這樣的認知模式之所以産生,是有一定的文化背景來支撐著的。只是,這個背景是甚麼,説真的,我説不上。然而,對我個人來説,以這種“驚奇”感作爲理解人類文明(社會)生成的心理起源,其體現在整個西方社會學發展史中的,可以説是有著一定的特殊意義。
就概念內涵的歷史性而言,把強調“驚奇”心理狀態拿來與以“迸生”(emergence)的概念作爲説明事物所以生成的基本狀態相互扣聯在一起思考,將會是具有著一定的特殊文化意義。因此,對迸生的概念是需要做説明的。首先,就語根而言,英文的“emergence”一字乃從拉丁文之“emergere”而來,其中“e”意指"從……而出",而“mergere”的意思則是浸泡在液體(如水)中。因此,“emergence”乃指原有沈在液體中的一樣東西浮現出來。
現在,讓我們假設一個情景:有一天,我們特地到海邊去欣賞海景,看著海水衝擊著海岸帶起了陣陣的浪花。正沈醉在欣賞之際,突然之間瞥到遠遠的海洋裏有一樣東西從水中冒出來。於是,我們把手搭在眉際,仔細一看,原來是一艘潛水艇。此時,試著想想人們的心理反應會是如何呢?或許,最常見的即是,人們以一聲類似“啊!是一艘潛水艇耶!”來反應。此時的心理狀態,基本上是維科以及柏格夫婦所説的“驚奇”感覺了,不是嗎?一旦我們更進一步地發現潛水艇上所插的旗子竟然是敵人的國旗,那麼,“驚奇”之外,添加的恐怕就是一種“驚恐”的感覺了。於是,我們或者趕快報警,或者嚇得拔腿就跑。
總之,準此語根的特質,當“迸生”一詞被用來形容所謂的“社會”的生成樣態時,基本上,它乃意涵著"社會"原本就是在某個“那兒”的地方,但因爲某種原因而被遮蓋、潛藏,使得人們看不到。因而,就認知層面來説,整個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讓它重新浮現出來,就像如何操縱控制浮沈的機關而讓潛艇浮出水面一般。
然而,就情緒感覺層面來説,那將會是甚麼呢?基本上,那或許就是維科以及柏格夫婦所説的“驚奇”感覺了。然而,“大驚奇”之後呢?柏格夫婦説是“例行化”,情形或許就正是如此罷!但是,情形也可能正如前面已提過之維科的説法——驚奇帶來的是崇敬感,爾後是火熱的強烈願望。若是,就人們對“迸生”現象的心理反應而言,與“驚奇”經常相連在一起的,至少是一種意外的強烈情緒感覺。因此,除了譬如驚恐之外,也可能是塗爾幹(Emile Durkheim)所説的迷狂狀態(ecstasy)了。
三 神聖崇拜與神才魅力——驚奇與例行化的體現
雖然塗爾幹與韋伯(Max Weber)這兩位古典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大師,在其論述當中,並沒有如維科或乃至柏格夫婦一般,明顯地把“驚奇”奉焉説明社會(或文明)之起源的心理狀態而進行理論論述,但是,他們在隱約之中卻是分享著類似的文化氛圍,也暗涵有類似的感知模式。底下,讓我們以嘗試的態度來看看維科所説之“驚奇”心理作爲文明的源起狀態,以怎樣的“變形”迸生姿態暗隱在塗爾幹與韋伯的論述裏面。
簡單地來説,在塗爾幹的眼中,社會作為一個存有體,它有著原本的自性,且是獨立於組成它之個體成員之外而自存著。只是,這個自性可能一直被掩遮而潛藏著,有待人們去挖掘而已。在此,姑且不管我們應當以何種方式來挖掘這個被隱藏之“東西”(thing)的自性,這樣的認知模式基本上乃蔚成傳統,並導引著整個西方社會學之主流認知體系的發展。社會學家們總是認爲社會有著一定的結構樣態,而此結構樣態以具動態的“迸生”性質,架設出整個有關社會的本質問題來。
然而,社會以怎樣的“迸生”方式而浮現出來呢?就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而言,塗爾幹認焉,社會所以“迸生”的源起乃在初民社會裏的圖騰主義(totemism)當中看到。他指出:
……在圖騰制度中,圖騰的形象表現被視屬首要的聖物,……各種神聖事物在信仰者的心中都能激起相同的情感,正是這種情感使他們具有了神聖性。而這種情感顯然只能來自於某種共同的本原,某種由圖騰標記、氏族成員和圖騰物種中的每個個體所共同分享的本原。事實上,膜拜所針對的就是這一共同的本原。換言之,圖騰制度不是關於動物、人或者圖象的宗教,而是關於一種匿名的和非人格的力的宗教。……
這種匿名、且非人格化的力是甚麼?它來自何處?對此,塗爾幹舉澳洲土人爲例,並發揮高度的想像來加以説明。他認爲,在平常例行的日子之外,土人們會經歷著類似今天之所謂“嘉年華會”的例外場合。在這樣的場合裏,人們聚在一齊狂舞、高歌,激情的鼓舞往往使得人們變得易於衝動,情緒激昂,亢奮而不能自已。但是,等到聚會結束之後,人們發現自己又是孑然一身,回落到平常的狀態。於是,他常會感覺到自己曾經在某個程度上經驗了超越自身。而所以如此,乃因“他感到體內充溢和泛濫著一種異常的力量,並且試圖奔湧而出。有時候他甚至覺得,他被一種比他本人要偉大得多的道德力量支配著,他只不過是他的代言人”。
尤有進之的是,正如前面所提到之維科説的,塗爾幹認爲,人們的這種感覺,基本上是“一個強烈得讓他震驚(surprise)的新生命在他體內奔流“。不過,人們“並沒有被幻覺所愚弄,因爲這種亢奮是真實的,他確實來自一種外在於個體並且高於個體的力量的作用”。同時,除非這份力量大到足以使得一個人脫離自我,而縱身投入到一種稱之爲迷狂的心理狀態,否則,它就不可能影響人們的心靈。
簡單地來説,在塗爾幹的心目中,這份實在、且足以使人迷狂的力量,就是社會本身。於此,塗爾幹提醒我們,當社會以一種宗教膜拜的氛圍被呈現時,這份膜拜的力量並沒有表現出是一種高高在上、並以其優勢來壓制人類的情形;相反的,它與人很接近,並賦予了人們一些憑藉他們自身根本無法擁有之各種非常有用的力量。總之,根植於圖騰制度的情感表現,本質上是一種愉快的信念,而不是恐懼和壓制。情形所以是如此,乃因爲“原始社會並不像那些龐大的利維坦一樣,用它的權力窮兒惡極地壓制人,把人置於嚴厲的規訓之下;原始人自發地投入到社會中而毫無抵觸”。
於是,很明顯的,在塗爾幹的眼裏,人類文明源起的原型是,人們在自然地感到驚奇而迷狂的冥冥之中,感受到社會的存在,尤其是其所展現的神聖性。這樣的説法無疑地乃與維科分享著相類似的感知模式,對人類文明的源起,更有著異曲同工的哲學人類學預設和期待性的説法。
至於韋伯,基本上,他並沒有像塗爾幹一樣,對人類文明的源起與發展,進行人類學式的細繳探源工作。他所側重的毋寧地是,對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或更廣泛地説,西方的理性文明)所以興起的歷史事件,進行著歷史因果與文化詮釋性的探索。以此背景來看,我們實難期待韋伯會在其浩瀚的著作中像維科(或塗爾幹)一般,具體地論及人類文明(社會)的起源問題,甚至,只是以隱晦而迂回的方式來觸及,也實難以發現的。
因此,底下,有關韋伯涉及社會源起所可能持有或意涵的立場,都必須在其著作中尋找一些蛛絲馬跡來作爲論證的依據。我深知,這樣的討論是欠缺相對穩固而直接的經驗證據基礎,有著一定的危險性,但是,我卻相信,這樣一種近乎“臆測而揣摩”的討論,佐以一些一手直接與二手間接資料作爲支撐的條件,應當可以呈現出一定的社會學意義,值得在此提出來與讀者分享。即使退一步來看,這至少對促使大家去注意這樣的一個問題,有著拋磚引玉的作用。
在韋伯的思想裹面,與文明(社會)之源起問題最有關的,莫過於是環繞著“神才”(charisma)此一概念的諸多討論上面。為了使得整個討論更具有説服力、也更形過延,首先,讓我引用埃森斯塔(Shumel N.Eisenstadt)對西方社會學理論的評論性説法作爲楔子。
埃森斯塔認爲,西方之古典社會學理論所關心的,基本上是啓蒙運動發韌以來有關自由、創造力和個人責任,以及三者彼此之間的關係的問題,而韋伯的論述自然也不例外。準此,固然神才的行止可能有著黑暗一面(如希特勒對猶太人所進行的大屠殺作爲),但是,它(特別是其所內涵之熱情的散發)卻也正是人類精神之潛在創造力得以呈現、發揮、並進而突破與改變既存制度的根本動力。
因此,從神才的概念作爲出發點來討論自由、創造力與個人責任的問題,是有著一定的理路基礎作爲後盾的。何以可以作如此説,那就得從韋伯對神才一概念所賦予的社會學意涵,尤其是形塑現代社會之運行基調——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所具的特殊地位來關照,才可能得到一些端倪。
就韋伯的意思,神才指的是一個個體人格所具有的一種特殊品質,其特點在於:被認爲是非凡的(extraordinary),並秉賦著超自然、超人、或至少相當特殊的異常力量或品質。當把這種人格特質施用於權威(authority)或正當統制(legitimate domination)的塑造上面時,相對於“傳統”(traditional)與“立法-理性”(legal - rational)兩個類型(或形式),則有了神才權威的類型和神才統制的形式。而如何使得神才權威或統制形式予以例行化(或謂理性化),又正是韋伯所關注的基本課題。
根據奚爾斯(Edward Shils)的意見,韋伯有關權威之三種理念類型的説法,其實乃意涵著區分兩類的人(或現象)是必要的。這兩類的人(或現象)分別是:創新或創造(者)(innovator or creator)以及維持(者)(maintainer)。很明顯的,創新或創造者指的是在引動觀念或行止上具神才魅力者,而維持者則是貫徹神才觀念或行止、並予以例行化的安頓者。對此一後者,韋伯認爲,就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進程來審視,大體上可能是訴諸“傳統”的形式,也可能是透過“立法-理性”形式來呈現。
然而,具神才魅力的創新或創造(者)如何搭架具傳統形式與具立法-理性形式的維持(者)呢?或更具體地説,具傳統形式與具立法-理性形式的維持(者)之間到底有著怎樣的可能關係?又,具神才魅力的創新或創造(者)對此一關係的建立,到底扮演著怎樣的角色?這個問題的可能解答關涉到神才所具源起性的社會意義,至爲關鍵,因此,必須予以正視。對此,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的説法頗具啓發性,值得特別在此加以闡述。
施路赫特認爲,非凡性(因此,與其相對應的“平凡性”也一樣地)是一種結構屬性;亦即:二分的“非凡/平凡”涉及的,是一種具超越特定時間與空間向度之普全特質的概念範疇,因此,二者之間的相互轉渡,至少在概念上是具有著必然性(因此,也就稱之為結構性的)。無疑的,這樣賦予“非凡/平凡”之二分範疇以具結構屬性的説法,保證了神才在社會變遷過程中有著具決定性之“過渡”作用的必要樞紐地位。換言之,不管一個社會以何種方式來例行化變遷的樣態,神才形式的出現是確立變遷方向的基本標杆,這是必要的內涵。
至於“傳統”與“立法-理性”的形式作爲例行化的權威形式,施路赫特認為,區分的基準則在於是否具備著“人格化”(即“人格的/非人格的”)(personal/impersonal),而這基本上是一種具發展(亦即歷史)意義的屬性。這也就是説,以所謂“傳統”與“立法﹣理性”(因而,“人格的/非人格的”)的形式來作爲轉換的表徵特質,本質上是受著特殊文化與歷史條件所制約,它將隨著一個社會的特殊條件而有所不同的。在不同的社會裏,因為有著不同的文化與歷史背景,神才所內涵的非凡性作爲一種結構性的力量,可能以異於“人格的/非人格的”的方式來呈現。
總之,準此兩個不同性質之面向作爲考量的基礎,施路赫特認爲,在韋伯的觀念裏,整個西方文明的發展(甚至可以説,整個人類文明也都是如此)正是透過神才權威的非凡性作爲結構性的動源來進行例行化過程。而且,更基於西方世界既有的特定文化和歷史條件的搭配,才使得整個西方世界由具人格化的傳統型社會形態過渡到具非人格化之立法-理性型的特殊“平凡”世界。
從以上奚爾斯與施路赫特所提出的闡述,我們可以發現,以個人人格的神才魅力特質(諸如神跡、預言啓示、或英雄行止等等)來確保權威的運作,基本上是一種以例外的非凡特質來證成社會形式的過程,它本身是不穩定,只具備著過渡性而已。韋伯進而認爲,通常,具神才魅力者被認爲是賦予使命,因而享受著人們的輸誠,也給予權威,但是,此一使命並不必然、也不常是具有著革命性的。只有在最富魅力的形式中,一個神才才有翻轉所有價值階序以及推翻既有習俗、法律與傳統的可能性。
因此,神才的極端形式,證諸於特殊的聖潔、英雄或例證等等特質,乃具備著塗爾幹所説那呈現在澳洲土人之部落社會裏的“曼納”(mana)的力道性質。而根據塗爾幹的意見,此一“曼納”力道恰恰正是使得宗教(因而社會)之原始形式得以産生的源起基礎。
倘若使用奚爾斯的説法,神才的“曼納”特質則又是意味著,它所涉及之人的存在或其所生活之世界具備著中心性(centrality)。而且,正是此一中心性配合了韋伯所説之“極端形式”必然內涵的強度,使得神才性是非凡的。同時,“此一中心性乃由其對引發、駕駁、轉化、維持和破壞人之生命中的致命緊要部分,具有著構作力量而組成,而且,此中心力量常常被看成是‘神’、宇宙的創始者、或其他具超越性的力量”。
因此,神才是一種新“社會秩序”形式的源起創造者;這也就是説,任何的秩序都內涵了神才的成分。無怪乎,韋伯會稱神才是“歷史中一種具特殊創造力的革命力量”,進而使得施洛伊德(Ralph Schroeder)認爲,神才基本上乃被使用來解釋一個新觀念體系的起源。或者,採取默生(Wolfgang Mommsen)較爲持重的説法,這則是:配合著例行化的過程,神才的力量成爲所有社會變遷的基本來源。
於是,我們似乎可以説,一方面,神才的非凡性成就了一種具宗教情操的神聖性,而誠如前引之塗爾幹所説的,這樣的神聖性為人們帶來“驚奇”(繼而崇拜)的新鮮經驗,雖然一開始或許不免令人們會有著突兀的感覺。另一方面,固然此一偉大的力量發現、創造、並維持了秩序,但是,也正是它,秩序可以破壞。 沒錯,在韋伯的論述當中,具理性的法制例行化是形構現代社會最基本、也是最明顯的特色。在此一歷史演進的過程中,神才的使命是愈來愈受知性所控制,而産生了所謂“非人格化”(impersonalization)的情形。其表現於現代社會、且最爲典型的,莫過於是使得理性本身成爲一種神才形式,韋伯稱之局“理性神才”(charisma of reason)的現象。韋伯甚至認爲,此一“非人格化”之理性神才的勝利所代表的,乃是歴史進程中之神才的最後形式,而此一“世俗化”的神才形式依賴的是理念(ideas)的本身,再也不是個人承載著的魔力或遺傳品質了。
然而,對“非人格化”之制度性的理性神才,尤其,其典型形式-科層制(bureaucracy)的運轉,韋伯一直是有所疑慮的。他認爲,科層制本身強調的是規則與權力運作時的技術性效率,它本身並無能力孕生一個“真正”的領袖。然而,一個民主體制(尤其是草創時期)要能夠順利運轉,是需要具神才成分的政治領袖,因爲只有具有類似希臘酒神戴奧西斯(Dionysus)之神才魅力的領袖人物,才可能爲社會創造、並提供一個肯確的價值方向。
於是,理性化的長成乃有賴本身不是理性之非凡、且疏外於所有規則(being foreign to all rules)的神才力量來證成的。無怪乎,在討論韋伯的政治與社會思想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會提出這樣的説法:“……神才作爲乃是歷史中最重要的革命成分,一種新理性形式之最具潛力的來源。”
很明顯的,盡管韋伯並沒有直接碰觸文明的源起問題,但是,當他把“非凡性”賦予神才一概念以作爲其所內涵的結構屬性之際,其實,這已暗含著“驚奇”是人們面對著神才時的一種初始心理狀態。同時,這也等於宣告了神才性是帶動任何社會變遷所必須之具結構必然(而非特殊歷史條件)性的“源起”因子。話説到這兒,我想,可以不用再多寫了。只有一句話:在思想與認知的潛意識裏,與塗爾幹一樣,韋伯多少分享有維科對人類文明起源所持有的基本哲學人類學預設與期待。但願,這樣的説法不會是太過武斷。
四 “人民”與“大眾”二概念的社會學意涵
西方社會學者如尼斯畢(Robert Nisbet)與吉登斯等人指出,發生於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與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乃是形塑西方社會學論述之基本性格的兩個重要歷史事件。單就法國大革命而言,它即成就了兩個相關的重要概念,對爾後之社會學思考也有著莫大的影響:這兩個概念分別是“人民”(people)與“大衆”(mass)。根據麻菲索利(Michel Maffesoli)的意見,打從誕生以來,西方社會學作爲一種逼近社會現象的學問,與哲學、心理學或甚至經濟學相比較,就較少關心個體或個體間的契約與理性集合形式,其所著重的毋寧是大衆和它所呈現的特殊屬性(如集體意識、社會連帶等等)。
於是,社會學探討的是對個體有著強制作用、且具集合性質的外在客存的結構特質,尤其是既無行動性、也非邏輯的“物質”部分(如馬克思所謂的下層結構)。塗爾幹早期強調“社會先於個體人、且對個體人産生制約”的主張,説來只是其中比較徹底的一種説法而已。
.png)
Michel Maffesoli:Ordinary Knowledge: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書影。圖片來源:Amazon
然而,假若我們特別回顧十七世紀以來的西歐社會思想發展史與其對現實社會所産生的影響,我們將不難發現,強調持具個體(possessive individual)的自由主義思想,一直就是西歐人(特指一些思想家)持有的一種理想信念。他們更是進一步地以之(以下簡稱“個人自由”)作爲改造現實社會的“應然”依據。只是,特別是在經歷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洗禮的法國,這樣強調個體的自由主義思想,卻是無法讓人們感覺到完全吻合著社會實際內涵的“本質”。當時法國社會所實際呈現的動蕩不安情形,使得許多思想家(特別是所謂的浪漫保守主義者)開始對來自自由主義傳統的思想有所省思,而重新思考起社會秩序的本質問題。
再者,受到是時流行之生物科學思想的影響,諸多英法社會學者,如斯賓賽(Herbert Spencer)和孔德(Auguste Comte),以及其後之塗爾幹,把人的社會比擬成爲有機體,而且蔚成思想上的潮流。於是,一旦社會被視爲是一個具整合協調狀態的秩序整體,它就獨立於個體之外而有了自性。如此一來,社會一概念所呈現的集體性(collectivity)乃被視爲是反映經驗現實的一種“實然”狀態。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之下,供奉社會爲一具自主性的集體形式,乃成爲“實然”的事實,而這與強調自由之持具個體的個人主義作爲一種“應然”的理想信念,於是出現相互對峙的局面。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格局之下,人民(與大衆)的概念,在某個程度上,可以把因這樣對峙而産生之概念上的空檔彌補過來。
基本上,人民與大衆這兩個概念可以説是因應啓蒙理性精神的召喚,把人類(human beings)此一範疇性的概念做了具體的歷史性轉折而變形生成的,並主要乃施用於政治社會學上面。就字根而言,英文的“people”一詞來自拉丁文“populus”,與“popular”和“public”二字分享著相同的意思。簡單來説,它乃特別就權利與義務(而且特指前者)的立場來泛指涉及公共領域的人們。在近代的民主體制裏,他們則是具備有正當之政治權力的來源,也是權力運作的主體。至於大衆一概念,雖與政治脫不離關係,但是,其內涵指涉的,基本上是一群分享著共同社會情境與感覺的人們,因此,社會心理的意義較重。
就啓蒙理性精神發皇的歷史軌跡來看,當歐洲人擡出了人民(或乃至大衆)的概念時,原有用來彰顯“人是自由、且平等”之理念的意思。説來,這可以看成是當時(特指十八至十九世紀之法國社會)以資産者爲主體之“老百姓”爲確保自身利益,對皇室與貴族等特權階層進行鬥爭的一種理念性工具。在此情況之下,人民一詞可以説是用來作爲在政治社會學上表逹具均質且平等性質之“人類”一概念的同義詞。至於個體性(individuality)一概念,作爲顯示“人類”此一“種屬”(species)之集合性概念的一種歷史形式,則是體現當時之歐洲人在文化與社會關係層次上的特定意義要求。因此,它必須配合著資産者所彰顯之人民(與大衆)的概念來考察,才可以有較爲妥貼的理解。換句話説,個體一概念的內涵是必須仰賴人民(與大衆)這樣一個具集體性質之概念所意涵的歷史屬性來予以成就的。
既然“人乃生而自由且平等”指涉的主體對象是人民,那麼,組成人民(大衆亦然)的成員,本質上自然就得假設是具有著相當均質的特質。或者,更恰確地説,(至少在理想上)人們具有著均質與平等的特質,乃成爲人民和大衆二概念之內涵勢必需要強調的部分。對此,我們必須做更進一步的闡述。
沒錯,在當代西方(特別美國)社會學裏所流行使用的一些概念,如社會階層(stratification),看似指涉、且承認著社會具有不同階序(hierarchy)的意思,但是,誠如杜蒙(Louis Dumont)指出的,這樣的階序概念,事實上並沒有充分認識到階序的本質、功能、和普遍性。所以這麼説,乃是因爲西方社會學家對這個名詞分析到最後,不僅表示採用了平等主義的看法來探討留存在平等主義社會中之階序的殘餘,而且也使用同一個看法來看待非平等主義社會中實際存在的階序。杜蒙甚至認爲,這是因爲西方人的心目中羞於談起階序,或把它潛意識化、並加以壓抑所導致的。
然而,假若我們特別回顧十七世紀以來的西歐社會思想發展史與其對現實社會所産生的影響,我們將不難發現,強調持具個體(possessive individual)的自由主義思想,一直就是西歐人(特指一些思想家)持有的一種理想信念。他們更是進一步地以之(以下簡稱“個人自由”)作爲改造現實社會的“應然”依據。只是,特別是在經歷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洗禮的法國,這樣強調個體的自由主義思想,卻是無法讓人們感覺到完全吻合著社會實際內涵的“本質”。當時法國社會所實際呈現的動蕩不安情形,使得許多思想家(特別是所謂的浪漫保守主義者)開始對來自自由主義傳統的思想有所省思,而重新思考起社會秩序的本質問題。
再者,受到是時流行之生物科學思想的影響,諸多英法社會學者,如斯賓賽(Herbert Spencer)和孔德(Auguste Comte),以及其後之塗爾幹,把人的社會比擬成爲有機體,而且蔚成思想上的潮流。於是,一旦社會被視爲是一個具整合協調狀態的秩序整體,它就獨立於個體之外而有了自性。如此一來,社會一概念所呈現的集體性(collectivity)乃被視爲是反映經驗現實的一種“實然”狀態。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之下,供奉社會爲一具自主性的集體形式,乃成爲“實然”的事實,而這與強調自由之持具個體的個人主義作爲一種“應然”的理想信念,於是出現相互對峙的局面。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格局之下,人民(與大衆)的概念,在某個程度上,可以把因這樣對峙而産生之概念上的空檔彌補過來。
基本上,人民與大衆這兩個概念可以説是因應啓蒙理性精神的召喚,把人類(human beings)此一範疇性的概念做了具體的歷史性轉折而變形生成的,並主要乃施用於政治社會學上面。就字根而言,英文的“people”一詞來自拉丁文“populus”,與“popular”和“public”二字分享著相同的意思。簡單來説,它乃特別就權利與義務(而且特指前者)的立場來泛指涉及公共領域的人們。在近代的民主體制裏,他們則是具備有正當之政治權力的來源,也是權力運作的主體。至於大衆一概念,雖與政治脫不離關係,但是,其內涵指涉的,基本上是一群分享著共同社會情境與感覺的人們,因此,社會心理的意義較重。
就啓蒙理性精神發皇的歷史軌跡來看,當歐洲人擡出了人民(或乃至大衆)的概念時,原有用來彰顯“人是自由、且平等”之理念的意思。説來,這可以看成是當時(特指十八至十九世紀之法國社會)以資産者爲主體之“老百姓”爲確保自身利益,對皇室與貴族等特權階層進行鬥爭的一種理念性工具。在此情況之下,人民一詞可以説是用來作爲在政治社會學上表逹具均質且平等性質之“人類”一概念的同義詞。至於個體性(individuality)一概念,作爲顯示“人類”此一“種屬”(species)之集合性概念的一種歷史形式,則是體現當時之歐洲人在文化與社會關係層次上的特定意義要求。因此,它必須配合著資産者所彰顯之人民(與大衆)的概念來考察,才可以有較爲妥貼的理解。換句話説,個體一概念的內涵是必須仰賴人民(與大衆)這樣一個具集體性質之概念所意涵的歷史屬性來予以成就的。
既然“人乃生而自由且平等”指涉的主體對象是人民,那麼,組成人民(大衆亦然)的成員,本質上自然就得假設是具有著相當均質的特質。或者,更恰確地説,(至少在理想上)人們具有著均質與平等的特質,乃成爲人民和大衆二概念之內涵勢必需要強調的部分。對此,我們必須做更進一步的闡述。
沒錯,在當代西方(特別美國)社會學裏所流行使用的一些概念,如社會階層(stratification),看似指涉、且承認著社會具有不同階序(hierarchy)的意思,但是,誠如杜蒙(Louis Dumont)指出的,這樣的階序概念,事實上並沒有充分認識到階序的本質、功能、和普遍性。所以這麼説,乃是因爲西方社會學家對這個名詞分析到最後,不僅表示採用了平等主義的看法來探討留存在平等主義社會中之階序的殘餘,而且也使用同一個看法來看待非平等主義社會中實際存在的階序。杜蒙甚至認爲,這是因爲西方人的心目中羞於談起階序,或把它潛意識化、並加以壓抑所導致的。
.png)
Louis Dumont:《階序人:卡斯特體系及其衍生現象》書影。圖片來源:豆瓣
更進一步的,杜蒙認爲,西方平等主義的信念乃內涵著平等是根源於人的本性,只因爲罪悪的社會加於否定,人們才享受不到。對此,他即説道:
那麼,既然人與人之間再也無法存在有甚麼條件上或身分上,甚至是種類上分屬正當的差別,人人也就全都大同小異,甚至是等同的,人人也就都平等了。平等與等同的融合已深入常識的層面。我們因而可以瞭解平等主義有一項嚴重而始料所未及的後果。在平等主義的世界裏面,人不再被認爲是分屬於階序格局中地位有別的各種社會性的或文化性的種屬,而被認爲基本上是平等而且等同;在此前提下,人類社群之間在性質上或地位上的差別有時候以一種危害重大的方式被加以重新強調:社群間之差別被認爲是生理特徵所造成——這就是種族主義。
於是,特別在美國人極端重視平等之意識形態的支配下,西方人甚至普遍地認爲,自由競爭代表的是平等與自由的結合。因此,他們同時也接受了因競爭而引起的不平等,而這樣的不平等的體現,恰恰即用來證成社會階層所以存在的正當性。
在此,需要更進一步提示的是,以這樣的認知模式作爲基礎,並就其所指涉的主體對象而言,社會一概念企圖涵蓋的,實際上就是人民(與大衆)這樣的範疇,儘管在絶大部分的時候它是被隱藏住的。尤有進之的是,倘若特別地就西方社會學的實證論述傳統來看,基本上,人民(與大衆)一詞則又必須予以行動表像化而表現在外,整個概念的內涵才得以充分地被證成。換句話説,就概念的實際操作面向,依附在人民(與大衆)概念下之種種可選擇的社會屬性(最常見的,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性質、互動連帶程度等等),則是用來作爲實際界定社會之特質的重要指標。發展至此、且推到端點來看,社會一概念於是乎被“變項化”(尤其計量化),並使得社會學論述與統計學可以接軌。更重要的是,人民(與大衆)的概念乃以深具“中性”色彩的“人口”(population)的姿態被呈現出來。這麼一來,原本只具政治社會學意涵的人民此一概念有了跨越邊界而擴散成爲社會學之一般概念的機會。但是,人口一概念的出現,卻也使得隱藏於背後之原有的人民一概念,在整個社會學論述中本具有的“核心”地位(尤其,其所意涵之特定的西歐文化與歷史色彩),更形隱晦地被掩遮住了。
與人民的概念一樣,人口基本上也是一個具集體意涵、且必須予以表像化的概念。於是,假若人口是用來建構所謂之“社會結構”一概念的一個重要元素的話,那麼,顯然的,如何以“變項”的形式來操作化(operationalize)整個“社會”的概念,是實證社會學的重要課題。於此,統計學上的平均值(average)(特別是均數[mean])一概念——或以奎德烈(Adolphe Quetelet)與塗爾幹的辭彙來説,即所謂的平均類型(average type),乃在社會學的論述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若以統計學上更恰確的技術性説詞來説,這樣的平均類型通常即是以諸如均數±1.96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的信任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來表示。轉換成爲社會學的語言,這也就是説,落在均數±1.96標準差的信任區間的任何數值,理論上都可以看成是沒有差異的,而其實際數值所以有著差異乃因爲種種誤差使然。
.png)
奎德烈Adolphe Quetelet。圖片來源:Bing
很明顯的,這樣運用統計學上的概念(加誤差與信任區間等等)來確立平均類型(尤其,內涵的常態性)之正當性的做法乃意味著,在特定“人口”中,一個特定屬性(如年收入)表現在個體元素之間的差異,在一定的適當範圍內,是可以視爲“無差異”的。而且,經由這樣之“差異予以無差異化”的“均質而平等化”操作所賦予的“平均類型”,即是常態的表徵,更順理成章地成爲社會一概念的具體化身。如此一來,就對人口(也是對人民)一概念賦予以平等主義的“均質而平等”的歷史屬性而言,透過統計的數量化操作來表現與證成,其實只不過是一個比較極端的做法而已。
事實上,以這樣的概率方式來認知與證成實在,也一樣地存在於非量化的概念裏,甚至可以説,這正是長期以來之西方人的典型認知模式。譬如,社會學家就一直假設著“集體意識”是存在著,而更重要的是,他們隱約假定著,這股力量對人們似乎是具有著相等而相同的作用(因爲人是均質且平等)。説來,以統計學上之均數概念來表達,只不過是透過誤差的概率理論來強化“均質而平等”的基本預設(或更貼切地説,理念期待),並經由此一步驟證成了社會所具有那獨立於個體、且對個體具普遍(且相等)有效性之制約作用的特殊屬性。
尤有進之的是,社會學家這樣供奉“社會”之結構的方式,體現在實然的世界裏,乃意味著爲一般人們所看重(而選擇)、且具“部分”事實性的屬性(亦即,理論上,可以並不是所有人皆看重的),往往會被膨脹成爲具全稱意義的社會事實。這樣的展現,一方面,透過統計母體(population)的概念,證成了一個假想的“社會”整體,另一面,也因此以爲可以“經驗”地肯確了該現象是存在於“社會”之中的。換言之,統計學的理論及其諸多概念的相互呼應,強化了社會學論述的經驗實在性。於是,社會學家就以爲,其所經營出來的概念與實際的經驗事實本身之間,可以安心地劃上了等號,當然,也因此證成了社會的圖象。
更弔詭的是,表面上看來與社會集體性對立的個體性,當實際施及於人們的現實而世俗的日常生活世界裏時,它也一樣地依附在如此的認知模式之下,被人們(特別社會學家)藉著具社會意涵之屬性(平等與自由二概念之外,尚有諸如理性、智力、財富、學力等等)以同質的方式予以呈現。因此,就結果體現的面向而言,依附在概率庇蔭之下的個體性,雖説乃是用以證成人之主體性(subjectivity)的基本內涵,但卻必須被擺在具集體意涵之外顯社會屬性的分配曲線上,而以其所呈現的相對位置來塑造著。
於是,到頭來,任何個體的主體性還是在“社會的”形式的籠罩下來予以證成。無怪乎,人們對這樣的主體性的證成方式,會一直感覺到是不完全,而且充滿著緊張的氛圍,因爲總令人感覺到社會的結構力量永遠是虎視眈眈地扞格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社會的結構形式彷彿像一張天蠶絲做的網一直罩在人們的頭上一般,人們總是擺脫不掉的。也正因爲如此,社會結構才會被認爲是與人們的自主意志一直對峙著。
五 社會結構與個體意志的兩元對峙
就在這樣的歷史場域裏,整個西方社會學傳統裏所使用的諸多概念當中,最爲普遍而廣泛通用的,莫過於是“結構”這一個辭彙了。對社會學家而言,這個概念的意涵幾乎可以説是自明,並不需要多加説明的。但是,奇怪的是,這個概念的內涵爲何,卻是最令人質疑;特別是拿來與其他的相關概念(諸如“文化”的概念)一齊考慮時,疑慮就更多了。
誠如在上面提過的,就歐洲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在歐洲人的心目中,“集體連帶”作爲實然“迸生”的既存現實社會結構狀態,它乃是一股外存於個體人的自主力量。其施加於人身上的,基本上是以一種本質上具制約性質的“平凡”例行化“權威”形式呈現著。至於自由主義思想傳統所強調之“個人自由”意志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主體行動能動性,則是引發“非凡”的神才力量以創造具“驚奇”性之新理想文明樣態的原動力。準此,甚爲多數的西方社會學者持著笛卡兒(Descartes)式之二元對張的認識論,認爲個體主體行動能動性作爲一種創造的來源與社會結構作爲一種制約的形式之間,一直是處於矛盾而對立的狀態。尤有進之的是,這乃展現啓蒙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所持續存在的一種緊張對立狀態,而這也正是任何社會內涵永恆矛盾對立之局面的一種歷史性典範。更值得提醒的是,西方社會學家們認爲,如此對社會本質所做二元對立的思想模式,乃深嵌進在人們日常生活的實際社會實踐行動裏。於是,在絶大部分的情況下,原本可以只是潛在的矛盾對立,總是成爲必然顯現的明勢格局。這反映在當代社會學理論論述的思想裏,即成爲所謂“結構/行動”二元論(性)的議題,而如何化解此二元格局所內涵的緊張矛盾,乃構成爲其中最爲核心的課題。
.png)
笛卡爾René Descartes。圖片來源:Bing
依照當前居主流地位的西方社會學思考模式來説,具高度結構化的社會形式往往即構成爲一種“體系”(system)。對此,康綸絲(Anne Kontos)指出,“體系”一概念的隱喻乃確立了形式理性的基礎(the substratum of formal rationality),而意指一些東西緊聯在一起,成爲一個可辨認、已建置、且具正當性的安排(arrangement)與制度(institution)。準此,人們往往不論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著碼(encoding)與解碼(decoding),而只問符碼如何引起凝聚(如規範、義務與內化)的問題。即使我們以諸如交換關係的概念來刻劃人與人的互動,也因爲觸及人的動機、認知或概化媒體(generalized media)等等的問題,都得先把“社會秩序”當成是一種先驗的狀態,而如是地供奉著。於是,所謂“社會體系”的結構特質,總是被社會學家認爲乃反映著“社會秩序”的可能,而且,也等同地作爲“社會秩序”的基本樣態。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有關“社會體系”的課題,其中,從人的互動行動層面來審視,可以説是晚近西方社會學家最常採用的進路。在這樣的互動觀的支撐下,倘若我們把社會結構特質看做爲一種“施爲”(agency)形式的話,那麼,它可以看成是一種集體性的權力形式。但是,假如我們從人作爲行動者的角度來審視,情形則將如應第斯(Barry Hindess)所説的,“社會結構提供給每個行動者代價、誘因和機會模式,而這模式乃刻劃著行動發生的情境。”準此,若採取理性選擇論的立場來看,結構於是可以使用“機會的序列”這樣的概念來定義。
.png)
Barry Hindess:Choice, Rationality and Social Theory書影。圖片來源:Amazon
基本上,這些説法可以説是,意圖直接或間接地把人作爲行動者的主體能動性彰顯出來,而其中有一個關鍵概念是至爲重要的。這個概念是齊穆爾(Georg Simmel)最早提到的所謂“社交性”(sociality)。根據麻菲索利的意見,儘管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乃具有著多樣化與異質化的事實,但是,社交性卻是理解人類種種社會行動不可或缺、且無以化約的基礎。因此,從社交性的概念出發來刻劃、並確立人的生活世界,基本上乃意味著人們之行動中的“社會的”(the societal inaction)這樣的特點是存在著。尤有進之的是,整個的情形並不是經由社交性引申出活生生的經驗,相反的,是活生生的經驗帶出社交性來。顯然的,在麻菲索利的觀念裏,理解人的社會世界(特別是人本身)時,人們的活鮮經驗是具有著認知上的優先性。然而,問題就在於這樣的認知優先性如何被呈現出來。或者,倒轉個角度來看,當西方社會學家關心到這個議題而企圖予以處理時,他們是怎樣進行著?這是底下隨即要探究的課題。
大體上,在當今可見的西方社會學論述當中,所謂的“理性選擇論”可以説是觸及此一認識立場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居優勢的論述形式。在此,讓我引述巴尼斯(Barry Barnes)的一些説法來加以説明。首先,巴尼斯認爲,只要根據幾個很簡單的假設,理性選擇論者即意圖確認一項命題,即:我們立刻可以預測出表現在一大堆個體之行爲中的基本模式。姑且暫時不論這樣的預測是否可能,也不論它是否確切而有效,至少,理性選擇論所企圖而衍生觸及的,乃運用到所謂的宏觀層次,同時也顯現出吉登斯之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的特質。這意思是説,它把行動模式、結構和體系看成是個體決定的産品(the products of individual decisions),而決定則又與個體對生産與再生産出來之模式、結構和體系的知識有著關係。於是,模式同時有助於處理個體決定,並以個體決定之産物的姿態繼續存在著。如此一來,理性選擇論看起來似乎既可處理人類互動的微觀面向,又可處理宏觀面向。其最具震撼力的特徵即是認爲,行動正可以依其所以被選擇的而被預測。因此,只要知道情境與在其中可能具有的行動,以及諸個體的諸多需要(wants)和其中的優先次序,個體所選擇的行動將即可預測。
.png)
Barry Barnes:Understanding Agency: Social Theory and Responsible Action書影。圖片來源:Amazon
很明顯的,這樣對個體決定給予以均質之情境結構化的論述立場,使得在理性選擇論的脈絡中自由選擇的意涵,既與外在限制,也與內在限制的意涵,都變得可以相容(compatible)。這麼一來,當認爲一個個體的意志是以理性的行動方式展現著時,它其實即意味著,一切既是可以預測,也可以推論。因此,所有的個體人被均質化,而情形變成爲:人人都具備著相同的理性成分與能力。這種來自古典自由主義假定“人生而自由且平等”的均質性預設,於是乎使得“理性選擇論所有不同的版本都招致一種想法,認爲人類的行動的底下有著某種的訊息處理裝置,而先置於它的認知過程,乃有如安置著推論程式和記憶儲藏體之推理機器的操作一般”。顯然的,這樣的立場乃與完全決定論的立場相互通融著。
依我個人的意見,整個問題的關鍵其實並不在於對人做了理性的假設,而是落在“均質化”了人之特質的預設上面。倘若對此一議題加以衍生,這同時涉及到例行化的問題。西蒙(Herbert Simon)即指出,例行是一個嚴格之理性選擇論的最基本問題,意即:例行乃展現定型、可預測之行爲模式的基本特徵。事實上,這也恰恰正是證成“結構”所以可能存在、且發揮作用的基本要件。換句話説,例行化了某些特質而使其作用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乃構成“結構”一概念的基本內涵。然而,對這樣定型之結構特質所可能産生的作用,我們應以如何的方式來看待呢?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底下所要討論的,即以此爲焦點。
.png)
西蒙Herbert Simon。圖片來源:Bing
當一個社會學家告訴我們某一個社會的自殺率是多少的時候,嚴格來説,他並無法回答我們,爲何譬如同樣得到憂鬱症、也具有著同樣的社會經濟背景等等條件的某甲會自殺,而某乙卻不會。於是,很明顯的,當塗爾幹以“社會連帶”的強弱來解釋自殺率的多寡時,他所做的只是企圖以具選擇性的親近方式來接近因果關係的可能性而已。尤其,當這是訴諸機率數據之統計模式性質的“肯證”形式時,它的肯證,並無法充分保證個別的個體人作爲一種有意識之行動者,其實際的行止表現會是甚麼一個樣子的。
集體性的東西所以被認爲是“存在”著,只是展示一種特定的認知模式而已。其對於個體若有所作用的話,基本上乃是透過“互動”所帶來的種種力道爲條件。但是,這卻還得以在人們的心靈上實際産生了作用作爲依據,才可以相對有效地被證成,也才得以形成爲所謂的“結構理路”。是故,結構理路本質上是透過集體共認之社會化過程而形塑的一種認知模式,因而,也是在假定人具均質性的前提下的一種規範模式。但是,它畢竟總是留有一定的空隙,給予人們一些自由選擇的空間。因此,任何結構理路往往只是一個具可塑性的模子,可以被人搓揉的;譬如,中國人常説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是最好的説明。
準此立場,從人的存在狀態出發,客觀的社會結構只有經過個人主觀的理解與透過互動溝通的相互主觀的檢證,才顯現出意義來的。情形是如此的話,回到人的身體體現面向來審視,乃是表現人之存在的一種方式,而且是極具世俗現實性的經驗呈現方式。於此,身體體現最爲具體的經驗形式就是“實作”(practice),而此時,社會結構則只是一種條件而已,它本身並不足以被視爲是具對立性的自主體的。情形若是如此的話,問題的重點就在於這樣的觀點是否爲西方社會學家所分享?若有,如何分享?若無,那又何以故?爲了闡明這些問題,底下,讓我們先來看看西方社會學者如何建構“施爲”這個當下極爲時髦的概念。
六 “施爲”概念的內涵與其不足之處
吉登斯與巴斯卡(Roy Bhaskar)均認爲,施爲乃意指一個個體人所具有的獨立力量,而此力量基本上是絶然不關涉到規則、或文化、或任何特殊的東西,只關係到任何被視爲可能限制到它的東西或事務。準此,在巴斯卡的眼中,施爲乃意涵人具有“另行作爲的能耐(the capacity to do otherwise)或“可以是另外的樣子”(could have been otherwise)的機會。巴尼斯認爲,這樣地定義施爲的概念,乃無異於對行爲施予因果或決定論的概念界定,所差的頂多只是接受“因果論斷的不完全”這樣的立場而已。因此,對施爲此一概念應當有更爲積極的界定,而對規範和規則有著積極而主動的取向,才是施爲一概念的基本內涵。準此,巴尼斯主張,施爲必須進一步地意涵著人具有著理性推理的能力,也有著對自己之行爲負責的特質。
.png)
Roy Bhaskar: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書影。圖片來源:豆瓣
然而,倘若我們僅就此一立基於個人主義立場的簡單命題來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具責任的“施爲者”(agent)的話,那麼,這則與理性選擇論者之人觀的基本立場並沒有甚麼根本的差異。事實上,體現在人際互動場域中的,並不是某種超乎個體之實體(不管是規則或慣域的集叢體)作用在個別特殊人身上的産品,而是互動之社會施爲者們恆定地會調整與排列那些未能一致與不和諧之個別實際行爲結果的“另類方式”。根據巴尼斯的意見,施爲者所以具有擔負起此一“另類方式”的“責任”能力,乃因他同時具有著應對力(accountability)與質疑力(susceptibility),而此等能力則反映在“地位”(status)上面。
在此,姑且不論同時以應對力與質疑力來架設“責任”一概念是否恰當的問題,很明顯的,巴尼斯這樣的處理乃是有意把討論的焦點移到“人”的自身上面,並藉此證成人行動時的主體能動性。但是,他把整個論述的重心安頓在具社會關係網絡意義、也是“社會”所賦予的“地位”概念上面,無疑地使得人的主體能動性到頭來還是被“社會化”了。因此,到底是以人本身,還是人與(特別是社會的)環境間的調適作爲整個思考的中心,實際上還是有待澄清的。在此情況之下,有關人作爲一個獨立而自主之主體的古典問題,依我個人的意見,依然存在著。
其次,讓我再引述另一個重要社會學家的説法來闡述西方社會學者對施爲一概念所持有的共同立場。這個社會學家是曾擔任過世界社會學會會長的英國女學者亞瑟兒(Margaret Archer)。以簡扼的語言來説,爲了回應後現代主義者宣稱“人文性已死亡”(the death of humanity)以及特別強調“論述”(discourse)的重要,亞瑟兒視“人文性”與“社會”乃互相獨立而有其各自的自性特質與施展能力,不能把人文性化約爲社會的。於是,雖然人的行動和社會結構有所接筍,也可以相互影響,但是,二者基本上有其各自的領域。同時,這也意涵著人所互動的世界(world)是大於、也多過於社會的。
.png)
Margaret Archer。圖片來源:Bing
亞瑟兒做此所謂“社會實在論”(social realism)的基本宣稱,顯然地是希望藉著“恢復”人本位的地位,並特別肯定“實作”(相對“論述”而言)在理解人的社會世界與行動時的優先性,以來重新考察社會的形成與運作。準此立場,亞瑟兒特別看重“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這樣一個概念在理解人之社會實作行動中的地位。藉此,她強調一個“位格人”(people)所具有的內在交談(internal conversation)能力,以作爲理解施爲此一概念的起點。這個能力涉及的是,在人思考世界與自己的處境時,對有關種種主客條件是否契合的問題,提供一些具參考反思性的事宜(a matter of referential reflexivity)。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人能否尋找到適當的辨識(discernment)、飾化(elaboration)與獻身(dedication)的方式,以便進行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s)與情緒評論(emotional commentary)的工夫。
爲了深厚位格人此一概念的內涵,亞瑟兒進而指出,除了個人認同之外,尚有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的面向。基本上,前者的指涉範疇是比後者更爲寬廣,因爲前者不但賦予後者生氣,而且,在相對著其他的考量下界定其序位。準此,社會認同乃在社會的前提下被拖引設計出來,但是,個人認同則是規約著主體對象與實在作爲整體之間的關係。於是,亞瑟兒認爲,所謂的位格人與自我(self)作爲兩個攸關“人”的迸生特質(emergent human property),後者乃代表著社會生活本身的起點,而前者則是終點。這也就是説,自我一概念是架接一個人的世界與社會的橋樑,而位格人是證成一個人作爲“人類”的終極理想樣態。只是,這個終極理想性必須落實在現實的實作社會情境裏,以具體行動來予以實踐。因而,人又必須是以行動者(actor)的姿態呈現自己。
至於所謂行動者,乃以社會角色的在位(role incumbents)的立場來界定。這是因爲角色本身有不可化爲居位者本身之特徵的迸生特質,而這些迸生特質又是外來自社會本身所賦予,並不是人自己原本內涵的。然而,問題在於這個代表著客觀“社會”、且具第二人稱之“你”(you)意涵的行動者如何實際地附著在一個“人”的自我上面被證成呢?對此,亞瑟兒又加上一個概念,她使用米德(George H. Mead)所謂之客我(Me)意涵的施爲一概念來架接代表“你”之行動者與反映著本我(I)的自我。
在此,作爲施爲的具體人物即所謂施爲者,它所指涉的基本上是分享共同生活機會的集體(或群體)(collectives sharing the same life-chances)(如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黑人女性)。這也就是説,在人的世界裏,由於種種的原因,致使有一些社會屬性對人們具有産生認同(或乃至凝聚)的作用。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面對著問題發生時,利益的歸依往往即以這樣塑造出來的集體性來予以界定著。譬如,所以得不到工作,是因爲自己是黑人女性的緣故。因此,當一個人作爲以角色來界定的行動者時,現實地來看,他是不可能不以施爲者的立場來考量的。此時,行動者乃把其所佔據的角色予以人格化(personify)。於是,亞瑟兒説道:“施爲者乃猶如是行動者的父母”。只是,行動者並非以單純的獲取角色(role-taking)方式來形塑生命形式(form of life),而是以製造角色(role-making)的姿態來加厚客體性與主體性間之因果力的交結作用。
總地來説,亞瑟兒所使用的概念相當繁複,既是多種、多元,且又是多重地疊架著。在這樣糾結而複雜的抽象論述中,要能夠既簡扼、又精準、且忠實地道出她的想法,著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容或前面對她的理論所做的描繪是掛一而漏萬,其中或許亦有著不少的誤解,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是:在極力希望以主動的能動性賦予“人”作爲具位格性的主體的期待下,她事實上又偷偷地把社會此一巨靈搬了回來。只是,她以巧妙的手法把社會的法力分別散發在諸如自我、位格人、施爲者或行動者等等看似落實在“人”身上的概念裏面而已。譬如,在討論到施爲一概念時,亞瑟兒區分了初基施爲(primary agency)與法人施爲(corporate agency)。相對於法人施爲是處於“成形”的狀態,初基施爲乃是一種“初始”的狀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認爲,初基施爲只有透過法人施爲,才能發揮力量。這樣的説法無形中乃以法人施爲這樣的集體形式,把社會這個巨靈迂迴、悄悄地又引了進來。無疑的,亞瑟兒把此二狀態當成具有著時間先後之必然性、且可以過渡的概念來使用。別的不説,這過度誇大了特定之社會的形式(在此,即爲具有相當正式意涵的法人概念)産生作用的必要性。這樣的説法基本上還是缺欠考量人所內涵更深層、且個人化之能動性(如策略運用與修養工夫)的理論意涵。其實,這樣的認知“缺欠”是普遍存在於那些企圖透過施爲概念把“人”本身的理論地位提升的西方社會學論述裏。
.png)
Margaret Archer:Being Human: The Problem of Agency書影。圖片來源:Cambridge Core
七 “身軀”、“實作”與另外之處
當近代西方社會學家使用實作一詞時,基本上,他們乃意圖用此作為表現人行動時之主體能動性的具體指標。因此,在意義內涵上,它是用來對應著社會結構的外在制約性,以證成人在行動時所可能彰顯的自主主導能力。然而,回顧整個當代西方社會學的論述,對這個概念所賦予的這様子期待,與前面所討論的諸多概念一般,實際上卻顯得是事與願違的。我們還是看到社會這個巨靈一直以迂迴而婉約的姿態在其中顯靈著。底下讓我選擇性地舉出一些晚近在文獻上看得到的説法來加以聞明。
實作一詞,除了具有實際操作的意思之外,還有練習的意思。既然實作必然是一種練習的過程,其意是形成具習慣(habits)意義的行為模式,因此,實作的基本內涵即是慣性(habituation)。在這様的基礎之下,特納(Stephen' Turner)認為,在西方社會理論的傅統裏,實作乃與諸如規範(norm)、民德(mores)、典範(paradigm)、傳統(tradition)、默然知識(tacit knowledge)、宇宙人生觀(Weltanschuug)、意識形態(ideology)、架構(framework)或預設(presupposition)等等概念成為一串的概念親族(conceptual kin)。
擺回西方社會理論論述的傅統來看,這就是説,實作的本質是社會的,乃為社會所塑造著。但是,它作為一種個人的習慣,在西方哲學史中,這卻又被視為是一種原因(cause)來看待,只是其判定常是暧昧而模糊不清。在這様的前提之下,特納站在社會學主義的立場指出,假如實作只不過是個人習慣,且具有個人習慣之獲取的特質的話,那麽,社會理論就無法與之共處,因為,此時,實作並不是一種具備足夠決定性的客體,足以用來作為嚴肅的解釋體。
同時,如此一來,任何的實作其實都立基於不同的預設基礎,它並不內涵超越時空的普遍集體性,而只是個人的習慣形塑,並且作為形構生命中種種作為(performations)輿競賽(emulations)的條件而已。於是,預設不同,實作的內涵也就不一様。同時,沒有任何人會被這些習慣所禁閉,而這些習慣毋寜地只是踏腳石,我們用來作為由掌控此轉至掌控彼之用。
從動機的角度來審視實作,吉登斯也指出,社會實作的絕大多數元素並不是直接被觸動(motivated)著。毋寜的,最典型的動機契入(motivational commitment)常常是涉及習慣性實作的概化整合(generalized integration),而這正是人格中最基本的安全體系。在此,暫且不管其所強調的概化整合一概念是否有著被過度社會化的嫌疑,對實作,吉登斯所關心的,是在於其所具有的規範特質上面。基本上,他視習慣性的實作(尤其,其所帶出的例行化行為)乃是理解社會結構的基礎,而這無疑地正是他指陳著實作所具習慣特質最為關鍵的意義之所在。於是,倘若實作作為一個人展現其主體能動性的具體指標的話,吉登斯與其他的社會學家一般,他所看重的是體現在行動之表像層面、且與社會(特別是規範)接筍的地方。
顯而易見的,配合著前面所提到以均質的假設作為對“人”之認知的前提,社會學家所著重之“人”的特質,於是乎乃是諸如能知度(knowledgeability)、意識(如階級意識)、或對社會資源的掌握(如權力)等等。以此等具外顯之社會關係性的概念來彰顯人的主體能動性,並用以輿結構的概念對立看待,其目標往往被設定在於“改變”既有的某種特定結構形態,以形塑另一種的結構形態。
因此,對行動(施為)的討論,基本上是衝對著結構此一概念而來,而且,更是朝著轉化成為另一個結構特質的方向來討論。這麽一來,行動作為結構的對立概念看待,它是被“社會的”此一概念所“異化”、也被它綁架了,最後得勝的還是“社會的”。因此,即使以“關係的”(the relational)一概念取代了實體化的社會一概念來作為確立社會學的最基本單元,事實上還是把“人”從神壇上撤換下來的。關於這様的論點,讓我們再借助有關身軀(body)的討論來做進一步的説明。
誠如在上文中所提示的,在啓蒙理性的導引下,人的身體充塞著無限的感覺話語,但是,只有可以言説的感覺才算數。這様經驗實證化人們的感知,乃代表著西方人的主體意識的證成,也同時賦予了個體性這様的名號。賀亞斯(Hans Joas)即指出,在西方漫長的社會思想發展史中,對人類行動的解説,最為明顯而特別的莫過於是,以“手段-目的”圖構的論説形式來對行動的意向從事所謂目的論的詮釋(a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ntionality of action)。
簡單地説,當我們把“手段-目的”圖構的論説形式架接到“人”身上(或人的行動本身)時,採取諸如動機、意向或計劃(plan)等等概念來串聯手段與目的,成為彰顯“人”之主體能動性的最佳説項。而且,圓成人的動機、意向或計劃等等,也因此自動地成為行動所以衍生之目的論的關鍵。前面所提到那具有悠久歷史、強調人具有理性特質的理性選擇説,就是展現如此具目的論意涵之詮釋的最佳明例。在此,理性乃對人之動機、意向或計劃等等特質的綜合性描給,可以一言以蔽之,而且完全獨立於行動來定義的。
賀亞斯認為,這様以“手段-目的”圖構形式來論述人的行動是不夠貼切,因為決定人之行動的並不只是人所具有的內在心理特徵(使用動機、意向、計劃或乃至理性的概念來説),尚取決於情境(situation)。他指出,經驗告訴我們,人在實際作為時,目的與期望並不一定是預設,也不一定是完全清澈。事實上,在實際行動的過程中,目的與期望是可以被修改、孕生、或乃至被揚棄,也可以是一開始就是暖昧地呈現著。因此,人們經常只是以“全局”的方式知覺事物(perceived globally)。
為此,賀亞斯提出行動的身軀性(corporeality)的概念。他認馬,透過人的身軀,行動與情境産生“準對話”式(quasi-dialogical)的關係。這也就是説,人的行動乃産生於前反思(pre-reflective)的情境脈絡當中;我們並非得一定要假設有著“計劃”(plan)(當然,也可以包含動機或意向)不可。縱然把計劃的概念拉了出來,行動實際發生的具體軌跡也是因情境之不同而有差異的,更是不時、且繼續予以修改著。
很明顯的,賀亞斯把身軀的概念抬了出來,與支持前面提及之所謂“結構/施為”二元説的論述,有著異曲同工的親近性。基本上,他們都是一様地反映著一個西方知識界所共同供奉的歷史使命;那是:長期來,以持具個人主義為旗幟的自由主義,一直就被西方思想家奉為具倫理應然性的基本理念,而貫徹這様的理念正是整個西方社會所追求的目標。然而,無疑的,諸多社會集體性之介體(如政府、政黨、法院、學校、工廠或傅播媒體等等)的實際存在,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性“實在”。
於是,在這様以個人為本的理想與以社會為體的現實相互衝撃之下,回歸到人的身軀,並給於社會“情境”適當的尊重,無疑地是一個在概念上可以謀求的妥協點。只是,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看待身軀?也就是説,如何以身軀的概念來證成“人”這個“東西”的主體能動性,以與社會結構相對應。
回到處理身軀一概念的問題上面來,賀亞斯首先反對把它局限在工具性的角色上,即如依利亞斯(Norbert Elias)輿傅柯(Michel Foucault)之論身軀的規訓一般,以為身軀只是反應外在社會的規範性要求而已。相反的,他認為,行動者對其身軀進行工具化乃是發展的結果,因此,我們必須對此一發展做出假設。如果我們假設此一發展並非自我進行去主體化的工具化,而是來自於自我有能力行動的話,那麽,身軀基本上乃主觀地呈現給予行動者,將是一項事實,而此一事實即為有關身軀圖構(body schema)或身軀圖象(body image)的問題。這麽一來,行動論所必須關懷的,不只是對身軀予以控制的産生,同時也是去除此控制之能力的發展;亦即,對身軀工具化之有意向的化解(intentional reductions)。
.png)
米歇爾·福柯作品《規訓與懲罰》書影,圖源:豆瓣
簡單來説,藉著身軀圖構或身軀圖象的概念,賀亞斯認為,人類對身軀的知覺乃具整體性的(holistic),而且,除了具認知性外,尚具情感性。更重要的是,一個行動者對其身軀的關係,基本上又深受人與人互動的結構所塑造著。這様之互動性的塑構即是身軀圖構或身軀圖象的特點,賀亞斯稱之為初始社交性(primary sociality)。很明顯的,此一初始社交性並不是衍生自具意識的意向性,而是先於此一意向性;易言之,它乃來自一個原先就只是包含著與其他身軀互動的共同行動的結構。
於是,賀亞斯廣泛援引米德有關意義象徵之溝通的學説,指出所有個人行止背後均具有著不可化約的社會性。他進一步説道:“倘若一個行動理論不具備有描述個體自主能力得以産生之前行條件的概念工具,此理論就不配説是為社會科學提供一個相容並蓄的綱領”。
無疑的,初始社交性之概念的提出所回應的,正是這個概念工具。如此一來,即使賀亞斯把行動的身軀作用歸因於尼采(Nietzsche)所説之具酒神戴奧西斯性格的創造力的提引,但是,終究又引導到塗爾幹式的“社會的”概念上面來,當然,也予以行為表像化。在此,賀亞斯特別強調此一“社交的”所以重要,並不在於其所引申之義務規約的規訓作用,而是在於用來構塑我們的世界、也是觸發人們之動機時,它所展現的原則性的性質上面。
其中,特別重要而有意義的是,在集體亢奮中引發自我喪失(loss of self)的“驚奇”經驗與對集體意識之具先於反思性質的認同上面。説來,這就是賀亞斯之心目中的初始社交性的雛形,也是行動之身軀性被安置在情境中的基本處境。而且,這正是證成前面所提到維科以“驚奇”作為文明發展的源起前提,也是提引塗爾幹以集體亢奮作為證成社會之原始形式的最佳寫照。
繼而,回顧西方社會學的論述史,賀亞斯發現,不論以表現(expression)、生産(production)或革命(revolution)的概念來彰顯人的主體能動性(特指創造力),都不免有以特定之實作行動形式來證成的嫌疑。對這様的作為,他指出:
隨它而來的因此是,人們若不能以詩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話,他們就是愚笨、心靈狹隘的庸俗之輩,他們所表現的形式不值得給予以進一步的注意;人們若不在掌控與運作事物之中發現自我實現,他們就是被異化;人們若不積極地在為革命鋪路當中有所貢獻,他們則只不過是被壓迫之同質群域中的一部分而已。
然而,賀亞斯以為,以這様方式來界定創造力,未免是太狹隘了。倘若創造力乃所有的人類行動的一個分析性面向的話,那麽,所有的行動都應當是具有著潛在的創造力的。對此,他進一步指出,來自歐洲的生命哲學(Lebensphilosophie)與來自美國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即具備了這様的論述特色。大體上,前者強調的是人的生命(life)與意志(will),而後者重視的則是知識(intelligence)與再構(reconstruction)。於是,在這様的雙重特質的交錯作用下,人的創造力得以發揮。
雖然賀亞斯提出創造力一概念來彰顯“人”作為行動者的主體能動性這様的説法,與過去的諸多論述相比較,看起來,對於彰顯人的主體位格,確實具有著更為深刻的意義,但是,以身軀性與社交性兩個概念來架接,無疑地還是把創造力可能撐張之內涵的深度和厚度一併給弄淺弄薄,也變得表面化。
所以這麽説,有兩面的原因。一方面,雖然身軀性是緊貼著“人”自身的初基物質特質,但是,正因為這様的初基物質性是最為根本,所以使得人所具有的另一個面向——心靈的細膩作用(如修養工夫)被懸擱了起來。另一方面,社交性的提出,固然指陳出人所賴以存在的事實狀態,但是,若缺乏另外適當之概念予以搭配(一様的,如修養工夫),則容易不自主地向著具外在制約性的社會結構力量傾斜。因此,以這様方式經管出來的創造力作為證成、發揮人之主體能動性的基本指標,到頭來,還是不夠徹底的。
八 走出普羅米修斯之迷思的陰影——一代結語
源自西方特殊歷史背景之有關“人”與社會的概念,正如文明人認為所謂的初民社會一般,無論在存有論、認識論、或乃至方法論的層次上,其實都存有著特定的哲學人類學預設作為後盾的。它反映的是一套塗染著極其濃郁之意識形態色彩的特定宇宙人生觀。
只是,現實上,長期以來,在高度體系化、且據優勢地位之西方知識系統的支配下,我們實在太習慣他們所經營出來的思考與感知模式了。尤其,加上人類的文明主調基本上也正朝著它所界定的方向行走著,於是,我們更加不自主地把它供奉成為至高無上的“真理”命題。無形之中,這使得原本甚至具有著應然期待性質之“認識可能性”的命題,被偷渡成為具普遍真理意涵之“實在可能性”的命題。遺憾的是,我們非但常常是不自知,而且,更是死不肯承認。社會學作為大學學院建制內一門獨立學科,自然也不例外地具有著這様的“偏見”性格。
.png)
普羅米修斯盜火,圖源:經濟觀察網《普羅米修斯“天庭盜火者”形象的嬗變——超越神話語境的希臘神話人物(1)》
精神分析家斯坦因(Murray Stein)透過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把火給了人類的故事來闡述西方現代文明所展現的特色。他指出,普羅米修斯給人類的禮物不只是火,而是一大堆東西,包括發明醫藥、占卜技巧、夢和徵兆的結識、冶金技術……等等文明所需的絶大多數技術和手兿。他接著説道:
但是這個長長的清單開始於一件表現了整個人類文化的先驗條件的禮物,即自我意識本身。普羅米修斯培育人類擺脫他們慌張迷惑和夢一般的混亂,擺脫他們的輕率愚笨和靈魂著魔狀態,使他們成為他們心智的主人。可是問題也恰好在於此:讓人類精神落腳,與此同時普羅米修斯卻破壊了人類輿諸神之間一個首要的關係。這埃次助長了人是他們的命運的最終主宰的妄念,造成了希臘文化的基本罪過——狂妄自大。……普羅米修斯的另外一件禮物也加強了他對妄念的主張和支持:他使人類不再預料著他們的死亡,並用盲目的希望代替了對必死的命運的直覺。
於是,人類(當然,指的是西方人)活在自我欺騙和自負之中,胸懷強烈而無端的妄念和盲目希望。作為一個西方人,斯坦因以為,以如此一般的方式予以適度的肯定,是需要的,只是分寸必須得當。然而,甚麽才是合適的分寸感,正是普羅米修斯的意識所缺乏的;為此,普羅米修斯以陷落反抗的心境來作為結局,而讓精神失態在憤怒之中猖獗地蔓延。然而,相當吊詭而諷刺的,這卻是西方近幾世紀以來之人文主義和反宗教思潮發展的主要內容。對這様一個思潮的孕生與流轉,斯坦因繼而評論道,或許,對宗教權威本身與教會之絕對權威所産生的教條主義進行反抗,是可以理解,也是值得稱道的,但是,這在西方社會卻造成了一種狂妄自大的態度,對心靈的原型力量一再地予以蔑視。
其結果是,在現代社會裹,良知被棄置,而成為只是具工具性質的理性考慮。“這也是大多數現代心理治療的真情狀況。在大多數心理治療中,內疚和羞恥被當作應予消除的問題對待,而沒有去診斷它們存在的原因。它們被作為自我發展不夠的症狀表現而被一筆勾消了。根據現代信條,真正成熟的人不受良心的煎熬”。
斯坦因所説的心靈的原型力量,到底是甚麽呢?當然,這可以有很多的説法,但是,至少絕不是時下人們所稱道、也是韋伯所一再提到的工具理性精神。依照容格(Carl G. Jung)的説法,這個原型力量乃體現在與過去(包含死亡)存有著綿密聯繫的神話裏面。容格指出,在今天所謂精神官能症的患者個案中,很多人在別的時代是不會染患的。這些人之所以成為精神官能症的患者,乃是因為人格分裂的緣故。要是他們生活的世界是一個人可藉由神話與祖先的世界聯繫起來,並且又可以真正體驗到的世界裏頭的話,他們就不會只是從外部來看了。他們所看到的,毋寜地會是一種本質的聯繫,而這種本質的聯繫基本上是一種神話的營造,它可以消除自身的人格分裂。
.png)
卡爾·容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瑞士心理學家,圖源:中讀,《3.2 榮格|人類心靈的探索者》
在容格的眼中,西方具批判性的理性主義和許多的神話概念,顯然都抹殺了死後的觀念。所以會是如此,乃因為許多人幾乎都把自己和自己的意識之間劃上等號,想像他們怎麽理解自己,自己就是怎麽的人。容格即認為,這是理性主義者的通病,妄想能夠提供所有的答案。他説道:理性向我們提出的界限過於狹窄,限制也過多,只允許我們接受已知物,生活在已知的框架之中,正如我們知道生命能延續多久。事實上,日復一日,我們都遠遠地生活在我們的意識範圍之外,儘管不知,潛意識的生活依然在我們的內心發展著。批判理性的支配利慾強大,生活變得愈貧乏;我們能意識到的潛意識愈多,神話愈多,我們就能使生活變得更完整。評價過高的理性輿政治的絕對權力有共同之處,在它的統治下,個人更形貧乏。
容格更引用老子的一句話:“衆人皆明,唯我獨懵”,説明他在老耄之年的感覺。他以為,老子看到、並體驗到價值與無價值,在生命將結束之際,希望復歸本來的存在,復歸到永恆、不可知的意義裹,這是生命的原型。老耄作為原型,它是一種限制因素,然而,“我心裹還是滿載著植物、動物、雲彩、晝與夜、人的永恆……愈是覺得拿不準自己,我與萬物有著密切關係的感覺愈是強烈。實際上,在我看來,長久使我覺得與世隔絶的疏離感,彷佛已經移轉進入我的內心世界,並向我揭示出乎自己意料的陌生。”
在此,讓我以最具有潛力把“人之主體能動性”此一概念可能內涵的理論論述意涵推到另一個更高境界的賀亞斯作為例子,以便進行著一項簡單的聞述。在論及創造力時,賀亞斯曾引述哲學家皮爾斯(Charles S. Peirce)所提到在創造行動中新假設生成的“外展”(abduction)概念,以來説明兿術創造活動的特質。同時,他更是援引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説法,認為人具創造力,並以之來經驗世界。同時,人對生命之基本感覺,更是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而這帶出了宗教經驗。
這様的思考,原有接近容格所提及之創造“神話”,尤其開啓了與東方人所謂“開悟”之説法做更細緻、且更具另類創意的契機,但是,與其他的西方社會學理論家一般,賀亞斯還是逃脫不了笛卡兒二元對張式之“結構/行動”二元並呈的思考模式,而再次地失之交臂了。
誠如在上文中一再企圖指出的,在西方社會學理論家的眼中,固然,依照個人意志而形塑的行動,是一股源自歷史期待而具備著“社會事實”性質的思想性力道,但是,結構更是一份在經驗上不可否認的集體事實。於是,結構和行動,不但是兩類具迸生性質的既有存在形式,而且一直是在企圖再創文明“驚奇”的歷史期待之下緊張地對張著。更重要的是,它們不但必須同時予以承認,並且更是需要等重地加以考量著。換句話説,西方社會學家接受著結構和行動相互衝突對立的“命運”特質,並且忠實而虔誠地把它奉為進行思考“人與社會”之問題的無上律令。説來,這是西方社會學傳統帶來的一種深具自我組織、自我指涉、繼而一再自我再製的思維陷阱,我們原本可以不必以這様的方式來思考的。
總之,基本上,上面一切的話語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既有的社會學思想模式裏,對具外在制約性質的結構而言,容或其源起是一種“驚奇”的狀態(如革命就是),而且也常被認為是如此,然而,它所進行、且實際産生作用的,卻是來自於予以例行化後取得了正當地位的時刻。就歷史進程的角度來看,在理解人之世界的形形色色的過程當中,這様的例行化是以人民之普世名義進行著。尤其,獲得了統計學上之均值人一概念具常態性的鼎力支持,這個概念巨靈於焉取得了絕對的詮釋權。
至於人的行動動能所可能帶動的作用(若非對外部社會,至少是對自我而言),在西方社會學的思考傅統裹,基本上則是被認為,純屬一種意外而例外的“溢出”。雖然這溢出的成分正是製造“驚奇”經驗的根本,但是,無疑的,它能否發揮實際的作用,是必須先接受結構“巨靈”的考驗。因此,在這様的認知架構下,整個文明所呈現的問題,轉個角度來看,即在於人的行動能否突破既有的結構模式,有著再造類似維科所説之“驚奇”的歷史局面。這遂成為我們不能不關心的重要課題,然而,對此一重要、但複雜的課題,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只好暫時擱置而不論。在此,讓我們回到一個根本的歷史情境,即:當面對著結構此一概念時,到底我們可能提供怎様的另類思考方式,而能夠更貼切地“反映”著整個人類文明之歷史場景的主調呢?
對我來説,誠如在其他地方説過的,所謂的結構性其實並無法完全征服人的個體性的。儘管,表面上看來,結構的高度體系化似乎使得人的社會世界的諸多面向(或人與人之間)互相扣攝得更為緊密,但是,事實上,它並未完全侵蝕、甚至根本就沒有動撼到人之所以作為個體人的根本特質——在地性(locality)的。當啓蒙時期以來西方人以製造(making)的方式來展現(事實上是“生産”)行動時,特定的歷史哲學乃被當作為模式來“製造歷史”,而其實這也僅只是在做實驗而已。誠如阿蘭德(Hannah Arendt)所指出的,實驗指向的基礎研究,基本上乃“在做我不知正在做甚麽”的工作,其間充滿無數的未知、未定與未可預期。
容或社會結構是“客觀”地存在著的話,這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種條件的鋪陳而已。特別是,人的稟賦其實是不同,修為不一様,而且,際遇更是有所差異著。這一切表示人的世界裏所充滿的未知、未定與未可預期,是不容忽視的。因此,我們實無任何非不可的理由,需要對“人”做“均質而一様地受制於結構”的假設。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不正面而嚴肅地思考著斯坦因對西方理性之歷史性格以及容格所特別強調的“集體神話”的特殊意義。這些都是推動著我們有必要為社會學理論論述尋找另類之哲學人類學預設的基礎。尤其重要的是,人類的文明或許也已經發展到必須重新尋找一條另類路徑來思考人的問題的時候了。或許,在貝克(Ulrich Beck)所説之“個體化”(individualized)的社會結構形式已逐漸明朗化之中,這様的歷史格局正浮現出來,而這將是下一個階段應當處理的課題。
文字编辑:郭雅文、洪嘉颖、杨茜茜
推送编辑:王天行、罗影
审核:孙飞宇、许方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