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3日9:00,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教育与文明发展”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项目主办的讲座在北京大学理科5号楼201室举行,主题为“Attitudes and Actions: Reflections on Qualitive Methodology”,由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和美国研究教授Shamus R. Khan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主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向明、副教授王利平出席并参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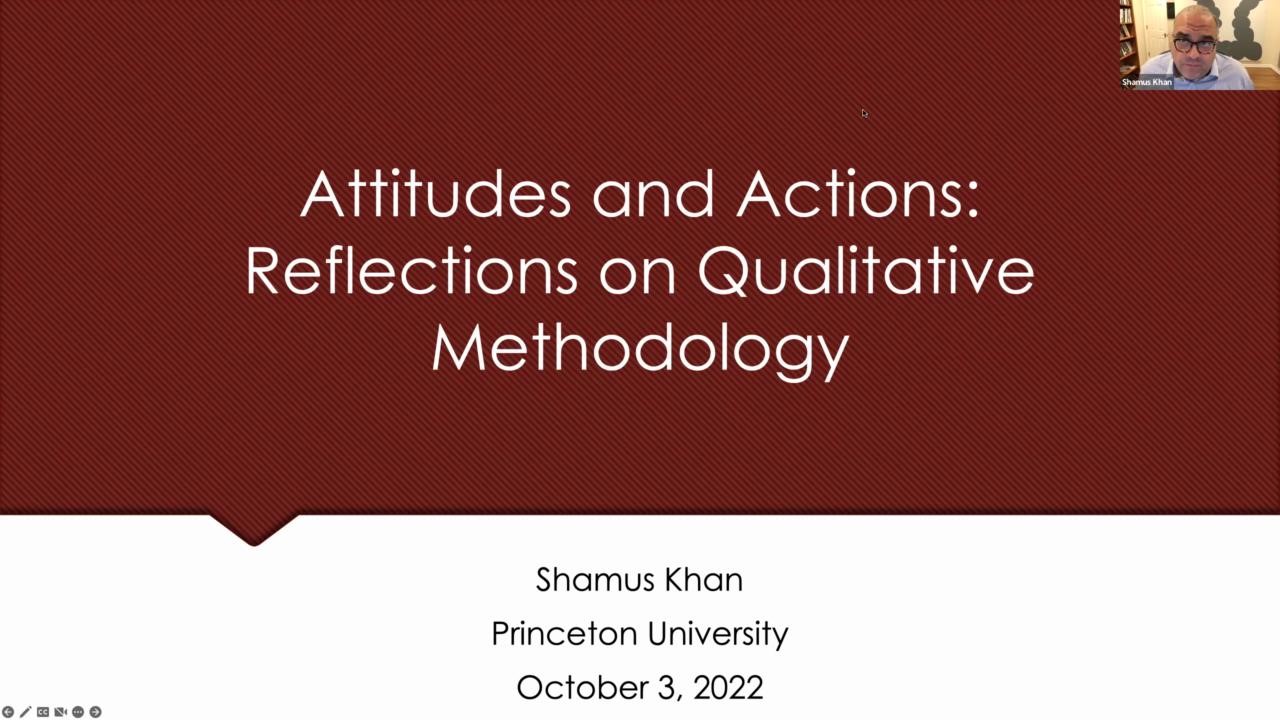
讲座伊始,Khan教授首先介绍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Sexual Citizens: A Landmark Study of Sex, Power, and Assault on Campus。这是一项多层次的研究,着眼于个人、关系、组织、政策和物理空间,讨论为什么人们会遭遇性侵犯,以及为什么一些人的性健康程度更高的问题。因此,研究者采取了一种基于团队展开、体量庞大且包含量化内容的新型民族志方法。研究团队包括四个小组,分别负责数据(statistic)、民族志(ethnography)、量化研究(quantities)和组织管理(administration)。Khan教授负责的民族志小组具体采用了深度访谈、关键信息访谈、焦点小组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并且通过基于社群的参与式研究(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视角也纳入到整体的设计之中。
Khan教授指出,该研究和自己此前有关精英教育与特权(privilege)的研究存在一个重要差异——学校中的不平等与等级制度的运转能够在田野工作中直观呈现,但关于性侵犯的行为却无法被研究者直接观察到,几乎只能依赖研究对象的叙述。然而,人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言辞往往并不一致,如果一概将人们的态度(attitude)与其行为(action)画等号,便会出现“态度谬误”(Attitudinal Fallacy)。
例如,Devah Pager在其2003年的研究中发现,虽然雇主都宣称自己没有种族歧视,但现实中却更不倾向于雇佣黑人求职者,尤其是有犯罪记录的黑人求职者。又如,20世纪30年代,Richard LaPiere带着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在美国各地旅行。在251次对酒店、饭点和露营地的实地访问中,他们只有一次被拒绝。然而6个月后,当LaPiere打电话给这些老板,询问他们是否允许中国客人入住时,只有一家回答说可以。这两项间隔60年左右的研究都表明,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并不总是一致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了解人们的态度是没有任何用处的。Khan教授认为,能够看到“不一致”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因为研究者可以进一步追问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由此,Khan教授分析了定性研究所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不准确的观察(Inaccurate Observations)、无法直接观察的行为(Unobservable Actions)和范畴回避(Categorical Avoidance)。前两个挑战往往相伴而生,不过,改进方法往往能够提高观察的效度和信度,解决观察不准确的问题。更难应对的是无法直接观察的行为,对此有两种常用的解决方案。一种是通过观察行为的结果(consequences)来推断行为。但是,当结果可能由多种因素导致时,这一方法并不理想。另一个替代方案是通过主体的叙述(subject narratives)来了解行为。但在这种方法中,研究者很容易遭遇范畴回避的挑战。
范畴回避的含义是,研究对象往往有合理的原因拒绝将自己的经历纳入研究者所关心的话题或范畴。比如,在访谈中很多学生会回避“遭遇性侵犯”的标签,也不会将这一经历告诉他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想避免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从而减轻相关的负面心理影响;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是被熟人侵犯,下意识地不想将“朋友”当作坏人。针对范畴回避的挑战,研究者通常会绕个弯解决问题(work around),也即建构一个能够被观察到的具体行为,并将具体行为匹配到具备操作性的范畴之中。比如,在关于性侵犯的访谈中,避免直接使用这一概念,而是换一种措辞方式,询问“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人在你未同意的情况下与你进行了性接触?”。又如,在一个社区中如果问人们“你是否因家庭出身被歧视过”,大多数人会回答“没有”;但如果问“你是否认为他人曾因你的口音而对你区别对待”,有很多人便会打开话匣子。不过,这种方法也因此而内含主观经验缺失的问题。

针对上述的三个挑战,Khan教授总结了四项环环相扣的对策:(1)区分描述性和叙述性事实(Descriptive and Narrative Truth);(2)转换抽样的逻辑(Shifting our logic of Sampling);(3)思考研究的层次,建立多层次定性模型(Qualitative Multilevel Modeling);(4)更注重分析的清晰性而非一致性(Analytic clarity over analytic consistency)。
首先,Khan教授指出,世上存在着各种类型的事实/真相(different kinds of truths),描述性事实(实际发生了什么)是客观的,叙述性事实则是主观的、具有主体性。如果想找到叙述性事实,需要根据情境(context)取样,了解人们的主体经验。对于描述性事实,则需要遵循定性研究的取样逻辑,从不同人的视角看问题,并且进行多层次的分析。不过,在现实中,研究者却通常会使用定量研究的抽样逻辑进行定性研究。这虽然能使得研究对某一人群的代表性较高,但并不能体现定性研究的优势,也即针对整体情况(representativeness of situations)的代表性。因此,研究者应当关心的是在特定情境中某一分析单位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 of unit of analysis within a context)。
举例而言,如果研究者观察A在家中、在课堂、与朋友一起玩时的行为,他可能会看到许多不同版本的A,这当然并不意味着A是“双面人”或者在某一场景中的行为是虚伪的,而只是说明情境(contexts)的特性会影响人的行为。采用这一视角,“模糊的对象”就会变得清晰起来,因为我们能够意识到,对象行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只是情境的差异造成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在研究中不能过于追求分析的一致性以至于掩盖了分析的清晰性。因为人们的观点与其行为时常并不一致,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中、同一情境中不同的人都是不同的。在研究中,恰恰应该描述而非掩盖这些不一致,来提高分析的清晰性。
此外,也要尝试超越个体层面的分析,采取多层次的民族志研究模型,来抵达描述性事实的分析。比如关于公共健康研究通常都从个体、关系、组织、文化的多个层次上展开。在Khan教授的最新研究中,他着重强调了空间层次的分析——某个空间到底是由谁控制的、人们是在什么样的空间中进行互动的。空间层次的分析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很多课堂都是教师一人讲授、学生只扮演聆听者的角色,这可能是因为阶梯教室的设计根本就不适合对话。
最后,Khan教授强调,在研究中建立多层次模型能够使研究者靠近更加客观的描述性事实,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叙述性事实。实际上,一项研究如果只有客观描述而没有主观经验,那就只是在绕着研究话题走(work around),而没有真正深入(work within)。因此,当研究者利用多层次模型解释某个现象时,可以在其中嵌入主观叙述。尽管,我们不能将叙述性和描述性事实混为一谈,将叙述性的主张当作描述性的真理,但是很显然二者在研究中皆是有价值的。

在提问和讨论环节,参与讲座的师生结合自身经历和讲座内容,就民族志研究过程、精英教育研究的方法等和主讲人进行深入提问和讨论。谈到对于非精英阶层的研究时,Khan教授指出,美国社会整体更加同情、理解少数族裔群体,也更倾向于不认同贫穷白人。因此,对于某些研究主体,发掘主观的叙述性事实是非常重要的。Khan教授也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研究对象行为与态度之间差异的认识,他认为,自己在研究中做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思考如何既尊重研究对象说的话,又不做一个单纯的速记员、能进一步认识到人们说的话与行动并不总是一致的。同时,如果发现了二者的脱节,研究者就有了解释的空间。最后,Khan教授提到了Matthew Desmond提出的主张:以关系民族志(Relational Ethnography)替代传统的民族志方法,不再将有边界的地点(如社区、工作地点)或群体(如单身母亲)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关注不同行动者或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建构过程。
供稿 | 马乐妍、王思凝、赵启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