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王利平,江苏常熟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1997年至2001年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学习,在李猛教授指导下完成本科论文,2001年至2004年继续在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在杨善华教授指导下从事西方社会理论研究。2013年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之后在Haverford College社会学系、芝加哥大学Harper-Schmidt青年研究院、香港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自2019年10月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历史研究,社会理论,教育社会学。代表成果: 专著The Imperial Creation of Ethnicity: Chinese Policies and the Ethnic Turn in Inner Mongolian Politics, 1900–1930 (Brill,2022);论文 “Clients, Double Clients or Brokers? The Changing Agency of Intermediary Tribal Groups in Ming Empire, 1368-1644” (first author, with Geng Tian, Theory and Society, 2021), “From Masterly Brokers to Compliant Protégées: The Frontier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Rise of Ethnic Confrontation in China-Inner Mongolia, 1900-1930”(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15),“如何培养行动力:杜威论现代教育的双重危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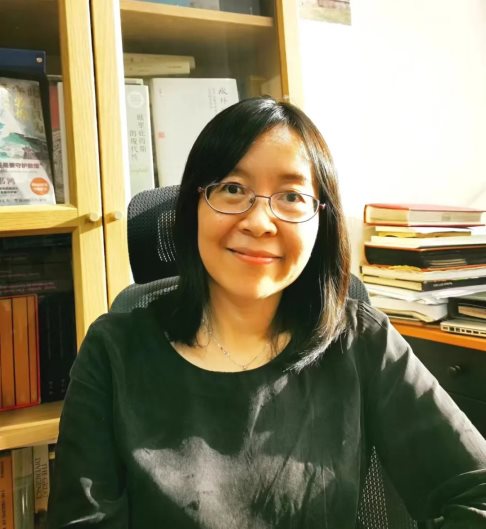
王利平老师近照。敦敦/摄
蓬勃的生趣:我在北大社会学的学生岁月
王利平
97年夏天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我接到了北大社会学的录取通知书。社会学是我的第一志愿,虽然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我跟家人说经济、法律我不喜欢,家人觉得它应该比文学、哲学要好点,我因此误打误撞地来到了这个学科。我是昌平园的孩子之一,大学的第一年是在昌平园度过的,那里静谧悠远,校门口耀眼婆娑的白杨林道,方方正正的主楼教室,是我对北方的第一印象。昌平园单调、乏味而安静,我对它印象还可以。系里老师需要搭班车来昌平园上课,很辛苦,而对每日需要占座、自习、上高数的我们来说,专业课和宿舍生活可能是最接近大学生活的那部分。在那里的课堂,我听了王思斌老师的《社会学概论》课和杨善华老师的《国外社会学学说》。很惭愧,第一次接触社会结构、变迁、乡土社会这些概念时,半知半解,我属于课上那部分对社会学缺乏朴素经验感的学生,但是因缘际会,我却在北大社会学找到了通向社会学之路。前不久,在系里重逢王思斌老师做系庆的节目,王老师低调朴实亲切的态度,情不自禁流露出的对师友、对系、对社会学的深厚情感,唤起了我二十多年前课堂里的感觉。每次走入系楼,稍显黯淡的一楼回廊,也回荡着熟悉的味道。这种感觉,就像游子眷恋的家一样,你或许游历、流连过很多地方,但心底总有一处,它温暖、亲切、自然,它存留了很多鲜活的情感和记忆,但面对它又让人近乡情怯,因为总怕在外面的自己辜负了许多期许。
在北大社会学系,我度过了七年光阴,在我工作学习过的地方,它不长不短,但回味悠远。我常和学生说,人的性格差不多在25岁时养成,此后你会经历知识的积累、阅历的增长、经验的丰富,但是你最在意什么、享受什么,为人处世的方式,25岁时差不多就定型了。而在你的学习时代,遇到过什么样的老师,交往过什么样的朋友,沉浸在什么样的氛围,大抵决定了你为人的志向。我的硕士导师是杨善华老师,本科论文导师是李猛老师。李老师当时硕士毕业留校任教,而杨老师最经常说的话是,李老师在社会理论上造诣匪浅,你有问题多找李老师请教。这些话当时只道寻常,很多年后想起常常令我感佩。杨老师代表了我所交往的社会学系诸多老师的一个缩影,在他们身上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谦逊、对学问的敬畏,和对年轻人的爱护,与今天浮躁的时代有点格格不入,实实在在滋养了好几代学生。杨老师是一个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兴味盎然的人,在我们多年的师生交往中,他总是给予我们细水长流的温暖。我跟随老师做田野的机会没有那么多,只去过宁夏和我老家常熟,记得在田野里工作一天之余,杨老师带我们享受美食,而长长的夜晚总是在小组讨论中度过。杨老师精力过人,细心过人,对每一位学生都有所留意,我学到了很多。我硕士论文做了一个理论题目,后去芝加哥读博士期间做了一个历史社会学题目,好像都没有用到田野的方法,但是当我需要做田野访谈的时候,我发现好像自己都会,这种熟稔的感觉我想是跟着杨老师长期熏染出来的。归根结底,田野研究源于对人的兴趣和对他人境况的深层的理解,这种能力也同样适用于读书和做事。印象之中,杨老师总是和风细雨,他会十分婉转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问题,包括我工作以后,向他倾诉烦恼,他总是云淡风轻地说一句,利平你太大条,然后条分缕析地帮我分析情况,让我顿觉豁然开朗。
我读书时兴趣常变,理论兴趣第一,也和师门去做田野,还在读硕士期间去河北做了个独立研究,无论我做什么,杨老师都支持我。这个敢尝试、敢放弃的习惯,一直延续到芝大,离开北大去芝大读博后,我开题是一个题目,开始做档案以后又换了个题目。今天想来,很感激我遇到的这些老师,我在北大的求学经历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走弯路,没人跟我说捷径是什么,这个习惯也许让我的学术兴趣显得边缘,但却让我安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芝大漫长的学习岁月中不自觉抵挡了很多诱惑和焦虑。北大在这一点上和芝大是一样的,那就是给予学生尝试、摸索的自由,这不仅对学生而且对老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要求为师与为学一样要有长远的眼光。而从北大社会学的求学时代起,我就觉得做学问有趣有滋味,它辛苦却不是一件苦役,是因为每一个研究都始于想要抓住一个令人兴奋的模糊的感觉。而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则是师生之间的信任,这种感觉就仿佛父母看着自己孩子的涂鸦,总是满心欢喜地能从中看出一幅大作的雏形来。
北大社会学有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除了理论和田野调查之外,孙立平、王汉生、张静等各位老师的课都磅礴大气,让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好的学问是深入现实而又有独立精神的。上一辈学人的学术与生命际遇之间有天然的亲和,虽然这一层关联很多时候是突来的难以把握的命运,但学术也恰恰如此显得更有勇气和生命力。所以,上课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受教育的过程。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王汉生老师,王老师身上总有一种威严,让我又敬又怕。她的课吸引了很多学生,一下课就被大家团团围住,但我总是悄悄离开教室,一学期课下来,我从未和王老师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在课上发过一句言,我相信她不认得我,但是期末作业我得到了特别好的成绩。很遗憾,没有机会和王老师提起这一段经历。它让我这么多年一直相信,做什么事情认真投入最重要,因为总有一双眼睛会看见。我也记得低调朴素的程为敏老师,上课总是娓娓道来的谢立中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和蔼可亲的佟新老师,还有乡音无比亲切的卢淑华老师等。系里的课让我了解了中国社会的轮廓,对中国问题复杂性的感受渗透到了血液之中。在芝加哥留学十年的岁月里,北大教给我的这些朴素的直觉虽然让我多了很多困惑,常常在异域和本土的多重视角下彷徨,但或许在他乡,才能体会到什么是故土的纯正的经验感。学问不在于理论框架有多完美,方法有多精深,根本在于是否能够真诚地探索真实的问题。这些都是我在北大读书期间无形之中积累下来的财富。
与同学相比,我的社会学兴趣不太主流。九十年代末的北大校园与今天不太一样,养了一批闲散又执着的读书人。读书人不是研究者,泛指那些读杂书且想从书里寻找人生意义的人。现在说来可能有点矫情,但有点矫情不就是人的青春状态吗?当时没有那么多课要上,也没有今天那么紧迫的绩点压力,很多同学和我一样选了五花八门的课。在没有跨学科项目的年代里,好像我们都已经历过博雅教育。我宿舍同学郭婷婷是一位诗人,受她影响我读了张承志和各种现代诗,当时中文系的诗人也经常来宿舍找她,我们也搭伴耳濡目染了一阵。好朋友李妍对宏观经济问题有兴趣,修了经双,我俩经常抵足而眠,虽然我对经济毫无感觉,但架不住她热情的感染。还有一位从化学系转来的朋友徐晓宏,经常神神叨叨,没头没尾地交流一段法国思想。我也经常去历史系同乡王锦屏宿舍闲聊,常常一待一下午。还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南配殿的小录像厅,可以点电影看,我时常和朋友去看一些特别晦涩难懂的艺术电影。内容已经全不记得了,但那个年龄会总想要咀嚼一些不能马上消化的食物。我在那里消磨了很多时光。本科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不急迫,我们同学中有目标特别明确的,也有像我这样不善经营、比较晚熟的,最重要的是当时系里氛围宽容,无论选择哪种生活好像也都过得不坏。工作以后我很怀念这段本科生活,不需追赶,或许迷惘过,但不焦虑。

作者大一暑假的军训留影。左起依次为郭婷婷、李莹、王利平、李妍。
我自己从读刘小枫的《社会理论绪论》开始,杂七杂八读了很多理论书,迷恋过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这些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思想和俄罗斯文学,还有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纪之交动荡变幻的大时代里人心思绪离合特别受触动。这些书大都优美而艰深,令人似懂非懂,当你心中有一团迷糊而强烈的探究的冲动,但又找不到一个明确的问题去落地,就去图书馆随便翻书。很多年后在芝大,导师Abbott组织了一个random reading读书会,就是去书架上随便浏览,抽一本感兴趣的来讨论,这个感觉很熟悉。这和我们今天主要依靠精准检索和推送来获取知识的途径很不一样。在一种模糊感觉的驱动下,我选了齐美尔做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犹记得在系里二楼一间凌乱的办公室里,和李猛老师第一次见面谈论文。李老师对学术的热心和投入是罕见的,只要你问一个问题,他会至少有十本书推荐,所以每次见面或是邮件请教论文,都像打开了一个百宝箱,让人既眼花缭乱又兴奋莫名。当时论文还是写在纸上的,我记得把凌乱的论文初稿交给他,估计文章不怎么通顺,李老师给了很多鼓励的话。文章终稿交上去以后,收到了李老师的一个电话,给了不少肯定,那当真是绝大的信心的鼓舞。写完本科论文,我想以后做学术,原因无它,就是单纯觉得有一种职业,它有创造力,有自己的节奏,不必朝九晚五,这份工作看起来可能有点闲散,但适合那些打心眼里爱较真的人。事实证明,这份工作一点也不闲散,这是后话。我很感激北大的读书氛围,本科四年,除了课程要求之外,我对社会学专业的阅读非常有限,也没有在意过方法论和规范,没有很细心地规划过自己的未来,但在这个环境里,我学会了认真的思考和阅读,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伴,不觉得孤独。这是一个宽松而有活力的大学,它是由那些钟情于教育事业的老师和富有热情朝气的学生共同搭建的。
跟随杨老师读研究生以后,我才算正式安定下来。杨老师支持姚映然师姐、孙飞宇、田耕和我一起组织一个理论的读书会。我记得读的第一本书是Giddens的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ety。读书会经常是在当时几个老师合用的理论教研办公室里。读的具体情形不太记得了,印象最深的是每次读完书去吃饭。当时佟园和网球场附近有一家药膳,冬夜菊花鸡的香味至今应该还能分辨出来。做论文的时候一度想做一个深入的田野研究,当时吴飞还在哈佛读博,通过他引荐去了河北的一个农村,那是我第一次体验人类学式的田野。住在村民的家里,与他们同一张炕上睡,同一张小桌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后来,因为非典,我被困在县城一家小旅馆里,正好整录音写笔记。杨老师资助了我这段研究,可是等到写论文的时候,觉得自己仍然难以割舍的真正热情还是这三年来读的黑格尔、卢卡奇和本雅明,决定放弃田野研究。杨老师依然表示支持。当老师后,每当想起这段经历,我会觉得如果有个学生这样,我该内心崩溃了。

左起依次为王竞、梁玉梅、张婧、彭铟妮、孙飞宇、黄霞、喻东、杨老师、涂骏、王利平、田耕、蒋勤。
读研期间我最经常去叨扰的是渠敬东老师。渠老师当时仍在社科院工作,在清华上社会理论课,我与清华的同学常姝、朱宇晶经常一起玩,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经常找渠老师讨论学术和聊人生。那时渠老师住在社科院的宿舍里,在东边,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穿越半个城到他家享受美食、电影和谈话。渠老师和小史姐的小家布置得温馨有特色,我们通常席地而坐,因为没有那么多椅子。大家海阔天空聊了一通以后,渠老师照例会下厨,展示他中西兼通的手艺,从切菜到下锅一气呵成,虽然厨房会狼藉遍地。我记得最深的是罗宋汤暖而厚实的滋味。晚饭后,我们一起看电影,有的时候聊到凌晨,朋友们有困得已经东倒西歪的,拉起来一起打个车回到北大。最晚的一次是早晨五点,也是冬天,清冽的风从车窗里灌进来,疲惫而朦胧的睡意袭来,我们靠在一起快睡着了,心里却很明净。另一件让我难以忘怀的事是硕士毕业申请出国读博。李猛老师那时候已经在芝大读博,而渠老师正好在芝大访学。我记得与渠老师在电话里聊了出国的打算和困难,他毫不犹豫地和李老师一起推荐我去了芝大。我去芝大求学以后,两位老师一直在生活和学业上关照我。敦敦出生后,我和田耕回北京探望师友,没有落脚地,就住在渠老师家。我与这些老师相差十来岁,我是学生的时候,他们也正青春年少,与他们的交往让我对学术萌发了憧憬。这种憧憬并不是对成为伟大学者的向往,而是对读书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生活得更加丰富更有质感的向往,还有师生之间坦诚热情的友谊,无私的帮助,都是我对为学的最初的美好感受。

作者一家在芝加哥大学,2015年。
严格来说,离开北大后,我才开始从职业意义上认识和接受社会学的训练。芝大教给了我社会学的手艺,北大则给了我求知之爱。北大七年仿佛是我找到一条通向社会学之旅的漫长小径,它蜿蜒曲折,有过很多分叉,它也像一个杂草丛生的花园,不精致不典雅,但充满了蓬勃的生趣,它将我带向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这段旅途,就好比歌德在迈斯特的学习生涯中所描绘的那样,它始于一些模糊的莫名的热情,靠着我们的护身神才得以历经一些洄漩与冲击之后稳定地行驶在它自己的航线上。我们的护身神,无他,就是我们的际遇。感谢北大社会学,给了这一方土壤,让我们能够慢慢地培育自己的理想。莫斯在《礼物》一书中说领受馈赠是人存在的根本,而有所亏欠的感觉恐怕是最甜蜜的负担。希望在未来教书育人的过程中,能像教导我的老师们那样,信任和鼓励学生,能够慢慢地偿还母系对我的培养之恩。
文字编辑:宋丹丹
推送编辑:王年廉、王朗宁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