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韋伯一生的研究裏,與倫理問題關係密切。由法學、史學、經濟學,到最後選擇社會學為職志的他,強調嚴格區分研究“實然”的經驗科學(社會學是其中之一)與研究“應然”的規範科學(倫理學是其中之一)的重要性。社會學家韋伯研究倫理問題時,主要的立場便是把“應然”的問題當成“實然”的經驗現象來研究,在他的比較宗教社會學裏,對世界諸宗教倫理與社會經濟倫理作了很詳盡的描述與分析,這樣的倫理研究,有人稱之為“描述的倫理學”。但是,韋伯關注自已所處的現實政治與時代命運問題,在學者、知識份子與政治家多重角色交織下,提出了“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二元對立的命題之時,似乎也成為一位倫理學家,建構了他自己的“規範的倫理學”。本文認為:受到康德哲學以來二元對立思潮的影響,韋伯所偏好的二元對立式的理念型的建構,實際上貫穿了他的整體社會學研究的各個領域,是我們今天探討他的作品必須加以正視的面向;倫理領域也不例外,無論是韋伯的“描述的倫理學”或“規範的倫理學”,都具有這樣的特色,但有所差異的是,在後者的領域中,韋伯似乎還存在著整合“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企圖,這是與韋伯其他二元對立的理念型概念建構是不同的。
.png)
韋伯(Max Weber,1864-1920)與倫理學(Ethik)的關係爲何?一直令人感到好奇,人們常常要問:韋伯這位百科全書型的學者,在跨過諸多人文、社會科學(法學、史學與經濟學等)領域後,最後選擇擔任一位社會學家,並且在宗教社會學研究裏,傾全力研究世界諸宗教倫理與社會經濟倫理之間的相關性問題,他究竟是以怎樣的立場來面對倫理學的?
.png)
馬克斯·韋伯(1864-1920),圖源:Bing。
近年來重新處理他的倫理學研究,並且把它與康德(Immanuel Kant)以及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倫理學相互比較的,首推韋伯全集主編之一的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筆者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古代中國儒家倫理與支配的正當化——韋伯比較社會學的批判》一書中,基本上也是循著他的研究路徑,從規則面向(Regelaspekt)、動機面向(Motivationsaspekt)與制裁面向(Sanktionsaspekt)來建構筆者對儒家倫理的詮釋,並對韋伯比較宗教社會學對儒家倫理的誤解提出批判。
由於施路赫特的論證相當繁複,而且相當程度以規範倫理學(normative Ethik)的方式,討論韋伯對“心志倫理”(Gesinnungsethik)與“責任倫理” (Verantwortungsethik)的研究,我們希望他日另文專門討論他的詮釋,在本篇短文中,主要希望從韋伯作爲一位經驗科學的社會學家出發,探討他的倫理研究的不同立場(社會學家/倫理學家,描述的倫理學/規範的倫理學),以及他的二元對立的理念型(Idealtypus)研究方法。
我們並不企圖對韋伯的倫理研究,作全面性的爬梳與整理。相反地,我們希望從韋伯不同立場來研究倫理問題出發,先討論了他從經驗科學的社會學家的立場,把應然的倫理規範問題當成實然的社會現象來研究,建構了他的“描述的倫理學”。進一步我們發現當韋伯涉及實際政治問題時,考慮倫理與政治問題時,似乎也建構了自己的、具有某種意義的“規範的倫理學”。我們無意過度深入去重建他賦予“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規範的倫理學”的實質内涵;相反地,我們找到的切入焦點,是他二元對立式的理念型研究方法,我們希望指出他這樣的研究方法的特點,還有具體應用在他的“規範的倫理學”分析裏,與他應用在其他實質社會學分析裏,究竟有何異同。我們發現,在他的“規範的倫理學”的領域中,韋伯似乎還存在著整合“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企圖,這是與韋伯理解社會學裏所廣泛運用的其他二元對立的理念型概念範疇是不同的。如果這樣的研究發現,在短短的篇幅中,有些許完成的話,也許會對社會學與哲學之間的科際整合有些裨益。
.png)
作爲社會學(Soziologie)創始人之一的韋伯,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裏,一再強調社會學作爲一門經驗科學,研究的是“實然”(Sein)的社會現象,與研究“應然”(Sollen)的各種“教義學”(Dogmatik)或“規範科學”(normative Wissenschaften)應該嚴格區分開來。他在《經濟與社會》的第一章<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裏討論到“意義” (Sinn)的問題開宗明義說:
“……這裏所謂的意義,並不會涉及客觀上‘正確的’(richtig),或在形而上而言‘真正的’(wahr)意義。在此,作爲行動的經驗科學(empirische Wissenschaften vom Handeln)的社會學與歷史學,與所有‘教義學的科學’(dogmatische Wissenschaften)區分開來,如法學、邏輯學、倫理學、美學等,它們想要掌握其研究對象的‘正確的’與‘有效的’(gültig)意義”。
換句話說,韋伯嚴格區分研究“實然”的“經驗科學”之一的社會學與研究“應然”的“規範科學”之一的倫理學。
在這種意義下,作爲一門經驗科學的社會學,並不是不能研究與應然命題相關的倫理問題與規範問題,只是經驗科學的研究方法,是把應然的問題當成實然的問題來研究。一位倫理學家稱它是描述的-分析的(deskriptiv-analytisch),而不是規範的-批判的(normativ-kritisch)研究方法。以這樣研究方法來研究倫理學問題,如果也被稱爲倫理學的話,可以稱之爲“描述的倫理學”(deskriptive Ethik)與“經驗的倫理學” (empirische Ethik),以與“規範的倫理學” (normative Ethik)與“後設的倫理學” (Metaethik)作區別。
的的確確,社會學家並不會迴避對倫理問題的探討,因爲倫理道德跟法律(Recht)、常規(Konvention) 與風俗(Sitte)一樣,它起源於社會文化之中,是社會規範(soziale Normen)的一種,會影響行動者進行社會行動(soziales Handeln)的主觀意義與行動取向,就好像法律、常規和風俗也會影響我們的社會行動一樣。同樣受康德倫理學影響的另一位社會學創始人,法國的塗爾幹(Emile Durkheim,1858-1917)也是把倫理學(道德哲學)的問題社會學化(經驗科學化),康德的道德哲學在他手中轉變成道德社會學,從社會文化的經驗背景來看社會道德的源起與轉變。
當韋伯把倫理道德看成社會規範之一的時候,他進一步指出:法律、常規與“倫理”之間的關係並不會構成社會學上的問題。他強調說: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一個‘倫理的’標準(‘ethischer’ Maßstab),是指一種特殊的標準,透過一個人價值理性的信仰(wertratuionales Glauben),他將它視爲對他的行動有效的規範,就像依據美學的標準可以說甚麼行動是‘美’的,依據倫理的標準也可以說甚麼是‘倫理上善的’行動”。
在這種意義下,倫理的規範觀念(ethische Normenvorstellungen),即使欠缺任何外在的保證,也會對行動産生巨大的影響。這種情形一方面往往在違反它時很少影響他人利益的情形出現,另一方面常常是透過宗教動機來加以保證的。在這裏韋伯繼承了康德以來的主張,法律與常規主要是透過外在的強制力量加以保證的,而倫理則是主要透過内在的強制力量加以保證的。但是,作爲研究經驗事實的社會學家,常常會發現各種實際有效的倫理,總是有可能透過外在的常規或法律來加以保證的。韋伯進一步強調說:
“究竟在人群中流傳的有效性的觀念(Geltungsvorstellung)是否能稱爲‘倫理’,對於經驗的社會學來說,只能看這群人實際應用的‘倫理’概念内涵到底爲何來加以判斷,無法一概而論”。
由此來看,韋伯的理解社會學(verstehende Soziologie)看待倫理問題,主要是把倫理看成實際發生的、與行動者内在主觀意義與内在強制力量息息相關的,而且間或與外在強制力量有關的實然的(實際有效的)社會規範,用描述的研究方法來加以刻劃與分析,至於倫理命題所蘊含的規範性質本身究竟爲何?何謂善?何謂惡?這些應然命題的實質内涵的善惡與真僞,並不是社會學家進行倫理研究所要關心的問題。事實上,也就是在這樣的經驗科學的意義下,韋伯進行了龐大的比較宗教社會學的研究。
首先,他研究了“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西方社會所具有的選擇性親近(Wahlverwandtschaft)的關係(宗教倫理←→社會經濟倫理)進行研究,身爲宗教社會學家,他強調自己的研究與具有規範科學意義的神學(Theologie)的差異,在神學認爲是殘餘類屬的、不重要的地方,如宗教倫理的社會經濟意義,正是韋伯宗教社會學的主要旨趣開展之處:當宗教倫理轉變成社會倫理與經濟倫理時,它不再只是規範信徒與神職人員的關係或信徒與信徒的關係,變成一般人與一般人交往的普遍準則之時,宗教倫理的社會學意義也日漸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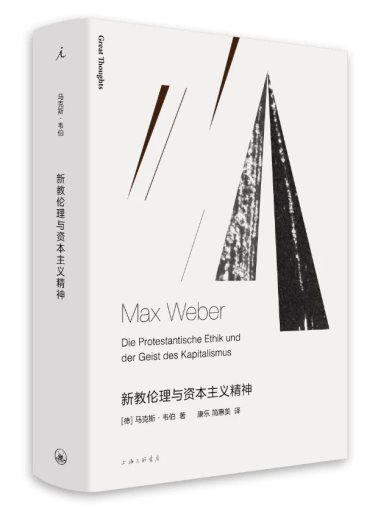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圖源:Bing。
然後,他進一步利用了理念型的建構(idealtypische Konstruktion),鋪陳了一個西方宗教倫理的發展史,把新教倫理與西方原有的巫術倫理(magische Ethik,一個有疑問的名詞,因爲按韋伯本意,巫術應無倫理可言)、猶太教倫理、天主教倫理等作對比(文化内的比較),在結合類型學(Typologie)與發展史(Entwicklungsgeschichte)的情形下,西方宗教倫理的發展便是從巫術倫理的階段,經由主要靠外在的法則加以保證的法則倫理與儀式倫理(Ethik der rituellen Religiosität und der Gesetzesreligiosität)的階段(猶太教與天主教的倫理屬之),最後到救贖宗教的心志倫理(Gesinnungsethik der Erlösungsreligiosität)的階段(新教倫理屬之),這是一個西方宗教發展的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的過程,根據兩個重要指標來加以劃分:宗教擺脫巫術的程度以及其“世界圖象”(Weltbild)系統的統一性的程度。
然後跨出文化内的比較,進入文化間的比較的領域,他進一步對比了西方新教倫理與其他世界主要宗教的倫理,建構了宗教倫理的類型學的比較研究。相對於西方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經濟倫理之間的選擇性親近關係,其他世界主要宗教的宗教倫理與經濟倫理也存在選擇性的親近關係,韋伯舉出中國、印度、回教國家爲例,探討了儒教、道教、佛教、印度教、回教、猶太教等重要宗教的倫理對於其所處社會的經濟倫理與社會倫理産生巨大的影響。以儒家倫理爲例,他認爲其發展階段主要是停留在法則倫理與儀式倫理的階段,與傳統式的經濟倫理有密切關連。
這樣龐大的理念型建構的比較宗教社會學,三大冊數千頁的著作,所進行的分析,不管是針對宗教倫理或社會經濟倫理,其研究方法主要就是描述式與分析式的。其主要目的是:探討倫理因素對歷史文化時空中,行動者發起行動所能産生的實際影響,不管是宗教行動或社會經濟行動,倫理作爲信仰的基礎與主觀意義的根源,的確會促使行動者朝向某一特定方向去行動,進一步由微視層次的社會行動,到巨視層次的社會秩序,即使其中會産生所謂“非預期性的結果”,無心插柳柳成蔭,但這卻無礙於倫理因素所發揮之實際影響與作用。社會學家的任務,就是要把這種倫理因素所實際産生的影響與作用,加以描述、分析出來。在此意義下,韋伯終生對宗教倫理與社會經濟倫理的研究,如果要稱呼它爲倫理學的話,主要是一種“描述的倫理學”。
.png)
但是,前述的“描述的倫理學”取向,其實並無法完全窮盡韋伯整體的倫理研究。如果我們把分析焦點,從韋伯的比較宗教社會學,轉到他對實際的政治問題與時代命運的探討,如他晚年兩篇重要的演講:<學術作爲一種志業> (Wissenschaft als Beruf)、<政治作爲一種志業> (Politik als Beruf),從實際的科學領域與政治領域,或者科學家與政治家的倫理問題來看,顯然韋伯在此所扮演的角色,已經不再堅守“描述的倫理學家”的崗位,或多或少他已經從“描述的倫理學”跨入“規範的倫理學”的領域。
.png)
韋伯發表“以學術為志業”演講的慕尼克施泰尼克書店的報告廳,圖源:澎湃新聞。
不少學者都指出,韋伯提出“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對比,其討論重點主要是一種政治的倫理學,而並不是想要建立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規範的倫理學”。這在韋伯的作品裏也可以看到,雖然他一再強調社會學家應該維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但他在自己所積極參加的“社會政策聯盟”多場演說裏,卻一再強調社會政策研究者主要是針對社會政策(政治)的倫理問題而發,亦即針對實際的-政治的評價(praktisch-politische Wertungen)問題來加以研究。
由此看來,他並不會迴避實際的“規範的倫理學”的研究,只是主要把它的範圍限定在“政治的倫理學”領域。或者我們也可稍微把範圍擴大些,擴及“科學[學術]的倫理學”的領域。當他主張社會科學家應該維持價值中立的立場,又在〈學術作爲一種志業〉強調說,在除魅後的諸神鬥爭的世界裏,科學頂多可以幫助我們保持清明的理智,而無法告訴我們該如何實際作抉擇,這其實也是一種“科學的倫理學”。
如此一來,介於社會學家韋伯與倫理學家韋伯之間,似乎就像經驗科學的社會學與規範科學的倫理學之間,存在著既緊張又犬牙交錯的微妙關係。韋伯這兩篇演講,選擇“科學[學術]”及“政治”作爲一種志業來作題目,並不是偶然的。因爲他實際體認到介於學術與政治之間、學者與政治家之間,經驗研究與社會政治之間,既具體相關又難以彼此調和的問題。
一次大戰前後,德國面臨戰敗的命運,國内局勢動盪不安。韋伯一方面由長期精神病狀態下逐步複元,由在家研究的學者重新登上大學的講堂來公開授課;另一方面,作爲關心德國國家命運的知識份子,他也積極針對德國政治局勢,提出自己獻身參與的實際貢獻:他參與德國自由黨(DDP)的創立,到處作政治演講,在報上寫政治專欄,還差一點成爲自由黨國會議員的候選人(其父即是俾斯麥時代的國會議員),並以學者身分參與凡爾賽和約的簽訂。在他本人身上,介於學者身分與政治人物身分之間、學術領域與政治領域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具體可見的。韋伯生前最後幾年,他同時扮演了學者、報紙專欄作家、自由黨政治演講者等多重角色,一般社會大衆與學生們對他有相當深切的期待,盼望他能面對德國戰敗的國家命運能提出獨特的立場與看法。
.png)
韋伯,1917年,圖源:澎湃新聞。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韋伯提出他的另一種倫理理論,二元對立式的對比,就像人的行動有價值理性的行動(wertrationales Handeln)和目的理性的行動(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對比,倫理信仰也有“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對比。透過這兩種倫理的對比,韋伯討論到以政治爲志業的人,究竟在人格上、倫理上應該具有怎樣的基本條件。他認爲,把政治作爲一種志業的人,他可以從中獲得權力感,但伴隨權力而來,應該負怎麼樣的責任,這是政治家的責任問題與倫理問題,關係到他有無資格爲歷史掌舵。
說明了政治責任是倫理問題之後,他認爲政治志業家必須有三種重要的特質:熱情、責任感、判斷力。三種要件缺一不可。所謂熱情是客觀而實事求是的熱情,對踏實的理想獻身,對掌管理想的神祇熱情皈依,熱情必須是實事求是的熱情,政治家重要的不在熱情本身,而在於用熱情追求踏實的理想的同時,把對目標的責任作爲自己行爲的最終指標。因此,在熱情與責任感外,政治家還需要判斷力,判斷力是心平氣和面對現實的能力,就是對人對事保持一定的距離,保持距離才能培養冷靜的判斷力。韋伯進一步指出,如何把熱情和判斷力在同一人身上加以調和,這是問題所在,雖然對政治的獻身來自於熱情,但政治靠的是頭腦,熱情的政治家的特色正是在精神上的自製能力,養成習慣地對人對事保持一定距離,這是政治人格的要件。
韋伯指出,政治行動的結果常和原先的意圖處於吊詭而難以理解的狀況,也就是因爲如此,政治行動更要有内在追求理想的意圖來支撐自己,爲了理想,政治家追求並使用權力,但這樣的理想究竟以甚麼形式出現,是由信仰決定的問題,韋伯認爲可以是有關民族或全人類的、社會的和倫理性的、文化性的、此岸的或宗教性的。總而言之,政治家要擁有某些心志與信念,否則即使外觀上看來最偉大的政治成就,最後也往往難逃空虛的命運。韋伯在此便討論到政治家的精神風格(Ethos)與道德安排的問題,在道德世界的甚麼地方才是政治的居身之所?在不同世界觀與價值觀的諸神鬥爭世界裏,最終只剩下選擇的問題。
韋伯進一步問,倫理和政治之間是怎樣的關係?韋伯提到《聖經》中登山寶訓的倫理,福音的絶對倫理真正的意義是:不是全有,就是全無,全有全無的倫理要求絶對的心智,如果要成爲聖人,一定要在每一件事上都是聖人,至少要有這樣的心智,要生活得像耶穌的使徒一樣,唯其如此這種倫理才能表現出當事人的尊嚴,如果不這樣做,就沒有意義,也沒有尊嚴可言。韋伯也提到和平主義者,他們拒絶武器,甚至丟掉武器,因爲這是倫理義務,目的在終止戰爭,終止一切戰爭。在絶對倫理下,和平主義是無條件的義務,至於放下武器的後果,和平主義的絶對倫理不過問。
在這關鍵的地方,韋伯建構了二元對立式的倫理學,他強調:一切具有倫理意義的行動都可以歸屬到兩種準則之中的一個之下,這兩種準則他稱爲“心志倫理”(Gesinnungsethik)與“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他認爲它們在根本上相互差異,同時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並不是心志倫理就是不負責任(Verantwortungslosigkeit),也不是責任倫理無視於心志(Gesinnungslosigkeit),但是他強調如果按照心志倫理行動(宗教上的說法是:基督徒的行爲是正當的,後果則委諸上帝)或按照責任倫理行動(當事人對自己的行動可預見的後果負有責任),兩種行動之間有著深刻的對立。
有學者透過一個簡明的圖表來對比這兩種倫理的實質差異,值得在此加以列出(儘管我們未必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png)
原文附表,“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對比。
透過這樣的對比,韋伯強調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永遠不可能並存,即使向目的使手段聖潔化這個原則作任何讓步,我們也永遠無法從道德上來判定,哪一個目的該聖潔化哪一個手段。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樣的宗教命題,在現實生活裏絶對不是實情,實際情況往往正好相反。韋伯說,不了解這一點的人在政治上是個孩童,所以如果要以政治爲志業,一定要保持前面提到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對一切保持距離,培養堅忍的個性。因爲,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價值多元、倫理多元的時代,處在許多不同的生命秩序中,這些秩序各自有其“固有法則性”(Eigengesetzlichkeit),沒有人能告訴另一個人,他應該採取心志倫理還是責任倫理,或在甚麼時候採取哪種倫理。
最後,韋伯談到他認爲最應該感動的狀況,這樣的人是真誠而誠心的對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做事,在某個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韋伯認爲這是令人動容的、人性的表現,在這種狀況下,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應該不再是絶對對立(absolute Gegensätze)的,而是互補(Ergäzungen)的:兩種倫理合起來構成道地的人,一個能夠從事政治志業的人。這種想要整合理念型對立的兩端的努力,是倫理學家韋伯規範性的主觀期待,與社會學家韋伯經常視理念型的兩端絶對對立的立場,具有明顯的差異。
.png)
跨入“規範的倫理學”的領域後,韋伯這種有關倫理問題的理念型建構,將“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既二元又對立,最後又希望它們相互補充的作法,對於熟悉韋伯的理解社會學常常使用理念型(Idealtypus)研究方法的人來說,也許會有些意外。因爲韋伯的理解社會學使用的理念型建構,是一種純粹類型的建構,是研究者將蕪雜的經驗事實加以精確化的思想整理:如果我們把經驗事實當成一個連續體(Kontinuum)來看待,會發現突顯這連續體的兩端各自建立一個純粹類型,當以一個爲主類型(Typus)的時候,另一個則成爲對比類型(Gegentypus),彼此相互對立,也相互彰顯,但卻是無法相互補充或相互融合的。
透過對比的概念建構,的確有助於理解社會學家對經驗世界蕪雜現象的整理,有關倫理的問題也不例外,底下分幾點來討論韋伯有關“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理念型建構問題:
首先,這種倫理的對比指涉一種相互對立的方法,這種對立使要作區別的兩種倫理縱深加大,最後到因爲兩極對立而在分析層次上使雙方“相互精確說明”(gegenseitigePräzisierung),因此它們之間的關係既不可分開也不可混合(untrennbar und unvermischbar),換句話說,相互對立(Gegeneinander)與湊在一起(Zueinander)同時發生,在一起,所以相互對立,因爲相互對立,也在一起, “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是韋伯有關倫理問題一組分析的概念範疇。
其次,正因爲它們彼此可以相互定義,也相互彰顯,所以可以確保彼此的基本關係和理念型的特性,亦即它們是概念建構下的産物。
第三,韋伯“心志倫理”強調意識上的類型,也會變成行動的類型, “心志倫理”不只是内在的確信,也會付諸行動。反之, “責任倫理”不是強調心志本身的價值,而強調與行動的結果在經驗世界裏的相關性,但這並不是說“責任倫理”只考慮外在的結果,而忽視内在道德上的確信。這兩個倫理的對立不是一個内在確信的倫理和外在結果倫理之間的對立,而是雙方都有考慮到内在與外在的層面。
這樣來看,我們在社會學基本概念裏看到韋伯對於行動類型的區分,在有關理性行動方面,他區分價值理性的行動與目的理性的行動,前者的行動以價值爲依歸,後者則考量完成目的的各種不同手段,這樣的區分與韋伯對於兩種倫理的區分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但是價值理性的行動與目的理性的行動之間,是否既二元對立又能夠相互補充,殆成疑問,必須作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
第四,“責任倫理”也必須承擔對它最深沉的信仰,加以負責,它堅信必須爲考量行動的後果而負責, “心志倫理”所根據的最後心志與信仰,是可以根據心志與信仰本身來做決定。我們可以說,在諸神鬥爭的時代, “心志倫理”是把特定信仰與心志擺在選擇之前,“責任倫理”則是把選擇擺在信仰和心志之前,在上帝死亡的時代,責任倫理家必須在平等地位的神祗與惡魔中作出選擇,他無法一開始就堅持特定的信仰作爲行動的準則,在這最後的時刻,這樣的選擇可能超越了所有的倫理(超越所有有關善惡的價值命題),這種情形下,責任倫理家作出選擇和決定。
第五,雖然“心志倫理”所隸屬的王國不是此岸的王國的倫理, “責任倫理”則是隸屬於此岸王國的倫理,但韋伯最終還是希望在一個特定的、有責任的、真正的領導者身上,兩種倫理可以相互補充整合,在此人的責任決定上融爲一體。他也強調“心志倫理”並不是没有責任的狀況, “責任倫理”也不是缺乏心志, “責任倫理”與“心志倫理”的對比不是理想主義的倫理與現實主義倫理之間的對比,或是精神界與經驗界的對比、内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對比,這兩種倫理終究包含這兩個層面。
另一位學者也強調“心志倫理”主要是宗教倫理,或類似宗教的倫理,“責任倫理”主要是政治的倫理;前者是回顧式的,針對除魅後之世界作抗議的倫理,後者是涉及未來的,爲理性化的文明而負責的倫理。強權政治(Machtpolitik)只是爲權力而權力,並沒有内在的信仰,不能被看爲倫理,它既無心志且無責任,不能和其他倫理等同看待。他也強調“責任倫理”與目的理性行動的相關性,因爲責任倫理的行動,是針對目的理性的行動,所産生的可預見的效果與副作用加以考量而行的。尤其在政治領域裏,因爲政治家所做的行動,原本的初衷與目的和最後的結果之間,常常會産生相當大的落差,在這樣的情形下,更應該強調“責任倫理”,以避免政治家作出過度獨斷的判斷。由此看來,韋伯這組有關倫理的討論,和他的其他二元對立式的理念型概念建構有相當密切的關聯。
施路赫特強調,在康德的哲學傳統背景影響之下,可以稱韋伯的理解社會學是康德式的社會學(kantianisierendeSoziologie)。韋伯區分“實然”(Sein)與“應然”(Sollen),“目的式的準則” (Zweck-Maxime)和“規範式的準則”(Norm-Maxime), “技術性的規則” (technische Regel)與“道德性的規則” (moralische Regel),還有區分“目的理性的行動”和“價值理性的行動”,早期則區分“結合性行動” (Gesellschaftshandeln)與“合意性行動”(Einverständnishandeln)等等,令人想起康德哲學裏對“假言令式” (hypothetischer Imperativ)與“定言令式” (kategorischerImperativ)之間所作的區分。此外,韋伯也用“法律性的準則”與“倫理性的準則”來區分宗教倫理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這種由外在而内在的發展過程,顯然也受到康德對“法律”的外在性與“道德”内在性的劃分的影響。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究竟韋伯二元對立的理念型概念建構,對他的整體社會學的研究,具有怎樣的意義?畢竟對韋伯這樣的理念型建構作方法論上的討論,也會有助於我們有關韋伯倫理研究的深入探討。舉例來說,韋伯二元對立的倫理區分,不只出現對“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區分之上,也出現在對儒家倫理與清教徒之間的宗教倫理區分之上。我曾經試著建構一個圖表來幫助韋伯作的區分:
.png)
原文附表,儒家倫理與清教徒倫理的對比。
透過這樣的理念型對比,韋伯認爲儒家倫理與清教徒倫理之間的對比,不只是適應現世的理性主義與宰製現世的理性主義之間的對比,也是他律倫理(Ethik der Heteronomie)與自律倫理(Ethik der Autonomie)之間的對比,這樣的做法,我曾在上述作品裹提出嚴厲的批判,有意者可參閲。
在這裹要強調的是,二元對立式的理念型建構不僅限於他的倫理研究的領域,在其他實質社會學的分析裏,如法律社會學、支配社會學、經濟社會學,以及<社會學基本概念〉裏,都有理念型二元對立的影子,綜合來看,他的對比概念範疇大概有下列各種組合:形式的←→實質的、理性的←→不理性的、形式的-理性的←→實質的-不理性的、形式理性→→實質理性、目的理性←→價值理性、理論理性←→實踐理性、理性主義←→傳統主義、理性主義←→不理性主義、實然←→應然、可預計性的←→不可預計性、非個人關係化的←→個人關係化、普遍主義←→特殊主義、國法←→人情、法律←→倫理道德、形式的法律←→實質的公道、官方←→民間、審判←→調解、專業法律人←→業餘(兼業)法律人、現代←→傳統、西方←→中國、現代西方←→傳統中國、抽象的←→具體的、法律内的←→法律外的,法律自律的←→法律他律的等等,不勝枚舉。
二元對立的概念建構形成“類型”與“對比類型”之間的極端對立,刻意強調出雙方兩極式的差異性,的確有助於對類型與對比類型差異的掌握。因此,立基在韋伯選定的區別範疇之上,所有東西被二分開來,要不就是正值的,就是負值的,不是形式的,就是實質的,不是理性的,就是不理性的,不是現代的,就是傳統的,不是心志倫理的,就是責價偷理的,二元對立的劃分後來被派深思(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模式變項(pattern variables)發揚光大,它排除其他的可能性,甚至包括正反雙方統一的可能性,如果用盧曼(Niklas Luhmann)的說法來看,這是在一階觀察的層次上,事件表現是單一脈絡的,其世界始終是二值的,一切所呈現的要不是正值就是負值,第三種可能性包括此二值的統一,都被排除在外,但其實第三種可能性無限多地存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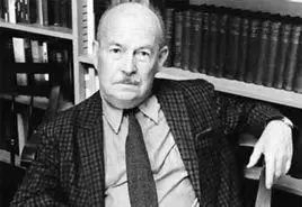
塔爾科特·帕森斯(1902-1979),圖源:B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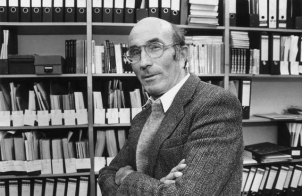
尼克拉斯·盧曼(1927-1998),圖源:Bing。
因此,韋伯強調的都是“非此即彼”(entweder oder)的對比關係,忽略了“既此且彼”(sowohl als auch)的可能性,他對“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在最終階段的整合的期待,也許是因爲走入“規範的倫理學”的領域,所以他似乎還努力做這樣的期待,而在其他理解社會學所運用的二元對立的理念型概念範疇裏,我們很難看到二元對立的兩極概念,相互補充、相互融合的可能性。爲甚麼有這樣的情形出現呢?是一個相當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值得他文再作努力。
.png)
韋伯一生的研究裏,與倫理問題關係密切。由法學、史學、經濟學,到最後選擇社會學爲職志的他,強調嚴格區分研究“實然”的經驗科學(社會學是其中之一)與研究“應然”的規範科學(倫理學是其中之一)的重要性。社會學家韋伯研究倫理問題時,主要的立場便是把“應然”的問題當成“實然”的經驗現象來研究,在他的比較宗教社會學裏,對世界諸宗教倫理與社會經濟倫理做了很詳盡的描述與分析,這樣的倫理研究,有人稱之爲“描述的倫理學”。
但是,韋伯也非常關注自己所處的現實政治與時代命運間題,在學者、知識份子與政治家多重角色交織下,在他提出了“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二元對立的命題之時,似乎也成爲一位倫理學家,建構了他自己的“規範的倫理學”。
本文認爲:受到康德哲學以來二元對立思潮的影響,韋伯所偏好的二元對立式的理念型的概念建構,實際上貫穿了他的整體社會學研究的各個領域,這是我們今天探討他的作品必須加以正視的面向;倫理領域也不例外,無論是韋伯的“描述的倫理學”或“規範的倫理學”,都具有這樣的特色;但有所差異的是,在後者的領域中,韋伯似乎還存在著整合“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企圖,這是與韋伯理解社會學裏所運用的其他二元對立的理念型概念範疇是不同的。
在這篇短文裏,我們並不企圖對韋伯的倫理研究,做全面性的爬梳與整理。相反地,我們希望從韋伯不同立場來研究倫理問題出發,先討論了他從經驗科學的社會學家的立場,把應然的倫理規範問題當成實然的社會現象來研究,建構了他的“描述的倫理學”。
進一步我們發現當韋伯涉及實際政治問題時,考慮倫理與政治問題時,似乎也建構了自己的、具有某種意義的“規範的倫理學”。我們無意過度深入地重建他賦予“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規範的倫理學”的實質内涵;相反地,我們把它們看成實際的經驗現象,探討他這樣的研究,對後世學者具有甚麼意義與啓發?我們找到的切入焦點之一,是他二元對立式的理念型研究方法。我們希望指出他這樣的研究方法的特點,還有具體應用在他的“規範的倫理學”分析裏,與他應用在其他實質社會學分析裏,究竟有何異同。
我們發現,在他的“規範的倫理學”的領域中,韋伯似乎還存在著整合“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企圖,這是與韋伯理解社會學裏所運用的其他二元對立的理念型概念範疇是不同的。如果這樣的研究發現,在短短的篇幅中,有些許完成的話,也許會對社會學與哲學之間的科際整合有些裨益。
文字编辑:李乐水、邵钰倩、刘明桓
推送编辑:王天行、陈立采
审核:孙飞宇、许方毅
文字节选自《社会理论学报》第六卷第一期第169页至188页,2003年,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