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平 | 从悲剧到哀悼剧:本雅明思想中悲剧观的发展脉络
编者按
本期内容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友王利平(1997级本科,2001级硕士)所著硕士学位论文《从悲剧观看禁欲主义——本雅明悲剧观与韦伯科学学说的对比研究》第三章,指导教师为杨善华教授。论文曾全文发表于《思想与社会》(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2006年第6卷,上海三联书店)。文章以本雅明的《德国哀悼剧的起源》为核心文本,阐释了现代社会中科学和艺术成为两大分立领域的根源及启示,从艺术下降为美的诱惑来反观韦伯天职观与科学学说内在的意义困境。本文详解了哀悼剧(又名悲苦剧)与古典悲剧的差别与内在张力,对理解现代政治的权力基础提出了极富新意的思考。

图为作者本科宿舍同学合影(后排左三为王利平老师)。
王利平,江苏常熟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1997年至2001年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学习,在李猛教授指导下完成本科论文,2001年至2004年继续在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在杨善华教授指导下从事西方社会理论研究。2013年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之后在Haverford College社会学系、芝加哥大学Harper-Schmidt青年研究院、香港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自2019年10月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历史研究,社会理论,教育社会学。代表成果: 专著The Imperial Creation of Ethnicity: Chinese Policies and the Ethnic Turn in Inner Mongolian Politics, 1900–1930 (Brill,即出);论文 “Clients, Double Clients or Brokers? The Changing Agency of Intermediary Tribal Groups in Ming Empire, 1368-1644” (first author, with Geng Tian, Theory and Society, 2021), “From Masterly Brokers to Compliant Protégées: The Frontier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Rise of Ethnic Confrontation in China-Inner Mongolia, 1900-1930”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15),“如何培养行动力:杜威论现代教育的双重危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

图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97级本科毕业合影(前排右一为王利平老师)。
从悲剧观看禁欲主义——本雅明悲剧观与韦伯科学学说的对比研究
王利平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科学与艺术的分立:
韦伯科学学说的内在困境
第二章 诗人的勇气与怯懦:
本雅明关于荷尔德林两首诗的研究
第三章 从悲剧到哀悼剧:
本雅明思想中悲剧观的发展脉络
第四章 无情的精神:
从本雅明重新审视韦伯的科学学说
结语
第三章 从悲剧到哀悼剧:本雅明思想中悲剧观的发展脉络
本雅明的《德国哀悼剧的起源》是一本内容精深,但不易理解的著作,是本雅明为了获得教授资格而写作的论文。在这部早期著作中,本雅明勾勒了德国哀悼剧的主要特征以及哀悼剧和悲剧的传承。我们看到德国哀悼剧兴盛的时代正是现代性的早期,所以本雅明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也不言而喻。
下文对本雅明悲剧观的讨论主要依循的是《德国哀悼剧的起源》的文本。
这部分内容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本雅明和黑格尔悲剧观的对比,从而引申出微不足道的人—这一悲剧观的核心,这直接开启了本雅明悲剧观中自然和恩宠之间的关联的可能。
第二部分是本雅明对悲剧和哀悼剧的对比,从而将第一部分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为有罪的自然和恩宠之间的关联。这些讨论都是以作为韦伯科学学说支撑的禁欲主义天职观内部的自然和恩宠的分离为参照的。与韦伯更恰且的比较是本雅明继悲剧之后对哀悼剧的进一步的讨论,我们会看到这一部分和韦伯在科学学说面临的复杂处境之间的关系,这为与韦伯的科学学说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更切实的入手点。
一 最微不足道的人:本雅明悲剧观的核心
本雅明的《德国哀悼剧的起源》的第一部分“悲剧和哀悼剧”详细讨论了悲剧和哀悼剧之间的传承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别,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本雅明思想中悲剧观的发展脉络。当然我们首先需要从悲剧中开始把握。对本雅明和黑格尔的比较不仅可以确立本雅明的悲剧观的核心及其与哀悼剧之间的关联,而且可以引申出本雅明的悲剧观的核心,即在于对人之为人的肯定及其与神意之间的复杂关联,正是从这里开始架起了我们在第一章的讨论中看到的自然和恩宠之间的分离。
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中对从史诗到悲剧的发展过程做了详细的论述。黑格尔对悲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后来本雅明、卢卡奇包括罗森茨威格的思想。
所以我们首先需要从黑格尔关于史诗和悲剧的对比研究开始,从中我们会看到为什么悲剧对于现代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本雅明在悲剧观上和黑格尔的传承和分歧又在哪里,以及这种差异在推进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中的重要意义。
1、从史诗到悲剧对回乡之路的切断

图为卢卡奇《小说理论》封面。图片来源:豆瓣。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首先向我们勾勒出了史诗的面貌。在他看来史诗的时代是没有问题(problem)的时代,因为人们尚未懂得渴望(seeking)的痛苦,它们仍然对灵魂的深度一无所知,后者既不可能诱使他们堕落,也不可能诱使他们去追求一个没有路途而言的高度。史诗的世界是一个同质的世界,所以不需要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跳跃(leap),只有当差别成为可能并且差别之间没有过渡的时候,才需要跳跃,这一切在史诗时代仍然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言在史诗的世界里没有超越(transcendence),那里同样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本质(essence),只不过通向本质的是一条回家的道路,所以不会有今天意义上无路可走的绝望或者说跳跃。对于史诗来说,世界在任何一个具体时点上都是最终极的,任何超验也都是经验的,它们无法超越经验的深度和广度,无法把那些循环往复的、感觉的、丰富的自然生命像现代人那样当作是一个既定的历史现实来超越。
所以对于史诗来说,并不需要离开经验的世界去把超验的现实当作唯一的现实。而本雅明在“小说的危机”、“讲故事的人”、“经验与贫乏” 以及“手帕”等文章中都向我们展示了起源于口述传统的史诗和小说的差异。就像他在“小说的危机”里面所说的,从史诗的观点来看,再没有比大海更富有史诗特征的了,史诗的写作就像是在海滩上的休息,是劳作一天之后的休息。而小说家则是孤身一人在大海上航行,他远离人群和他们的活动。
因此史诗的世界是平面的,它不需要远离人群去冒险,不需要对于经验世界本身的超越。就像黑格尔在《美学》中分析史诗的时候指出,史诗人物固然也各有愿望和目的,但是要点不在于他们是否有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在于他们在当时场合中的一切遭遇。换句话说,史诗人物的愿望和目的并不需要以超越经验世界的方式去实现,奥德修斯并不是在冒险,他只是想回到伊特卡故乡。
《奥德赛》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奥德修斯无论如何克服险阻去实现这个既定的目标,而是关于他在迷途中全部遭遇的叙述,他所碰到的阻碍,他克服的艰险以及他的心情所受到的搅扰。所以黑格尔才说,史诗具有真正的诗的性质,因为史诗世界的完成不同于诗人凭主观意志的安排,而是从经验本身自然生长出来。
换言之,在黑格尔看来,史诗当中的每一个事件之所以是一个事迹,就是因为对史诗来说任何超验的都是经验的,或者本雅明所言史诗具有的典型(exemplary) 的品质。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从史诗到悲剧,其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
黑格尔指出,在史诗的世界里,成为唯一根源和支柱的是是非感,正义感,道德风俗,心情和性格,而这些因素还没有由知解力固定下来成为散文现实的形式,和人心或个人思想情感相对立。
一旦社会如果发展成为组织得很周密的具有宪法的国家政权,有固定的法律,有统治一切的司法机构,有管理得很好的行政部门,有部长,参议员和警察之类人物,它就不能作为真正史诗动作(情节)的基础。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客观的道德习俗情况固然是意志和实现意志的结果,但是意志和实现意志都只能靠行动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并不是由于道德习俗本已普遍生效而且本身有存在理由,它就能获得客观存在(实现)。
我们看到,正是道德习俗和以人物性格和行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道德之间的不同区分了史诗和悲剧。史诗世界里面的自由,不是主奴辩证法意义上的主奴关系。史诗而不是抒情诗或者戏剧非常适用于表现战争中的勇敢,这是因为在戏剧当中主要关心的是人物内心的精神性的刚强和软弱,从伦理观点来看有理由辩护或遭鄙弃的情致,但是史诗里的关键却是人物性格当中的自然。也就是说英勇还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性,因此也不是一种伦理品质,它是人的自然品性,它和人的精神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实践的目的。
所以,史诗里面的事迹都是自然生长的,史诗人物并非自由自为地行动,而是置身于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目的和客观存在与一种本身完整的世界,就是这种整体的目的和客观存在形成每一个别人物的不可移动的基础。
正是从黑格尔关于英勇这种品质在史诗中的独一无二的表现的论述中,我们得以体会史诗中的以道德习俗出现的道德实体的含义。也就是说,在史诗的世界里面还没有出现个人和共同体的分裂,因此也就没有个人和世界之间的对立,也就不会出现表现为精神性的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而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只有从悲剧中,也就是说当史诗的浑然一体的格局被打破时才会产生。
卢卡奇的“悲剧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Tragedy)不仅是戈德曼写作悲剧观的核心文本之一,在本雅明对悲剧的分析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通过悲剧英雄的沉默点出了悲剧和史诗的区别。在卢卡奇看来,悲剧人物的伟大时刻恰恰是摆脱了一切日常生活盘根错节的缠绕而实现的,是刹那间擦亮的火光,它使得一切日常生活黯然失色,因为那是悲剧英雄和生命中的本质面对面的一刻。也就是说,和史诗里的英雄不同,悲剧英雄的伟大需要通过摆脱经验现实来实现,需要通过和经验现实之间的抗争来实现,需要在悲剧英雄无法言说的个体孤独中来实现。
卢卡奇看到尽管悲剧和史诗都喜欢用国王来象征英雄,但是在两者那里的意义确极为不同。对于悲剧来说国王是唯一一个能够摆脱一切琐碎的生活束缚的人,这也是悲剧展开的前提,在悲剧那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多(multiplicity),它的多不过是在1后面加上的无数多个0,所以命运在悲剧英雄那里永远是他一个人的命运,或者说必须由他的孤独来承担的命运。
在史诗那里则不是如此,因为史诗中过的是共同体的生活(community life),实现的永远是共同体的命运(community destiny)。换句话说,对悲剧英雄来说灵魂的确定性无法在外部的经验世界中找到任何一条能够通达它的路径,只有在悲剧英雄肉身死亡的刹那才能摆脱层层萦绕,抵达光芒的核心,获得生活的本质意义。
在卢卡奇看来,悲剧的危险是对比史诗来说的,它来自于悲剧英雄和生活之间的张力。如果对于史诗来说超验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内在于经验之中的话,那么对于悲剧来说原先的构成(constitutive)力量完全变成了规范(regulative)的力量,变成了“应该如此”(should be),并因此而杀死了生活。悲剧英雄不可能活着获得灵魂的确定性,不可能在经验世界之中获得灵魂的确定性,回家的那条路从此被阻断了。
正是在悲剧英雄之死中,我们看到悲剧是史诗世界的分裂,即悲剧英雄从共同体中的分离,在这个意义上悲剧的和解就和史诗不同了,或者说出现了黑格尔所言不同于史诗的伦理的和解。
2、黑格尔与本雅明在悲剧观上的不同侧重点

图为俄狄浦斯Oedipus and the Sphinx 。图片来源:Wikipedia。
黑格尔认为形成悲剧动作情节的真正内容意蕴,即决定悲剧人物去追求什么目的的出发点,是在人类意志领域中具有实体性的本身就有理由的一系列的力量:首先是夫妻,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属爱;其次是国家政治生活,公民的爱国心以及统治者的意志;第三是宗教生活,不过这里指的不是不肯行动的虔诚,也不是人类胸中仿佛根据神旨的判别善恶的意识,而是对现实生活的利益和关系的积极参预和推进,真正的悲剧人物性格就要有这种优良品质。
悲剧中的人物和史诗不一样,他并不像史诗中那样具有一种分散的完整性,而是在悲剧人物的性格中体现出凝聚在一点的个性,这也是悲剧人物闪光的地方。在黑格尔看来,悲剧人物的个性代表了这个人物性格的一种力量,这股力量是实体性的力量,悲剧人物按照自己的个性把自己和真理的生活内容的某一个特殊方面紧密结合成为一体,而且负责维护它。
因此在悲剧人物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伟大和坚定,因为并没有个性的偶然因素在干扰。原始悲剧的真正题旨是神性的东西,这里指的不是单纯宗教意识中那种神性的东西,而是在尘世间个别人物行动上体现出来的那种神性的东西,我们看到悲剧中的神性或是伦理并不是后来按照智识理解的道德教条,而就是处在人世现实中的神性的因素。在黑格尔看来,悲剧中的罪就在于体现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伦理理想从单方面来看都是有根据的,但是又都是片面的,所以才有不同的冲突,在悲剧的毁灭中各方面都通过毁灭而得以成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才认为《安提戈涅》是最完美的悲剧的表现。在黑格尔看来,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因为真正实体性的因素的实现并不能靠一些片面的特殊目的之间的斗争,而是要靠和解。
在黑格尔看来,如果灾难仅仅只是灾难的话就含有贬低受灾祸者的意味,悲剧就不可能在观者身上引出凝重的怜悯之情。也就是说,真正的怜悯,就是对受灾祸者所持的伦理理由的同情,也就是对他所必然显现的那种正面的有实体性的因素的同情。所以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内容意蕴和美好品质,正如他的遭到破坏的伦理理想的力量使我们感到恐惧一样,只有真实的内容意蕴才能打动高尚心灵的深处。
我们在前一部分有关悲剧和史诗的分离中已经可以看到黑格尔所谓不同于史诗的悲剧的伦理式的和解。但是在黑格尔的悲剧观中并没有发展出弱小的个体和命运之间的对决,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悲剧中的人物应该是某一伦理力量的代表。所以对于黑格尔来说,悲剧的重心在于和解,悲剧英雄并非是远离共同体的,他是共同体的必然的一部分,只不过他只代表了一部分而已。
和黑格尔不同,在古典悲剧中,本雅明更为偏爱《俄狄浦斯》,这是因为在俄狄浦斯的命运中始终包含了放逐(exile)的主题。这也是为什么本雅明在《德国哀悼剧的起源》中讨论悲剧的部分着重放在对悲剧英雄的沉默和无视(defiance)的阐述上。本雅明对悲剧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卢卡奇的影响,我们在先前对卢卡奇有关悲剧和史诗的对比中已经可以看到,之所以要引入悲剧,实际上就是要强调悲剧英雄和共同体之间,和世界之间的分离。
本雅明在《德国哀悼剧的起源》中援引卢卡奇对悲剧的论述时指出,悲剧和哀悼剧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悲剧英雄身上表现出来的无视(defiance),这在哀悼剧中是不可能的。悲剧英雄在面对将他击倒的力量时所表现出来的沉默中毁灭了将其和世界(the world)以及神(god)联系起来的纽带,一方面这样一种沉默是高贵的,因为体现了自足的骄傲,这把他和以言语(speech)为代表的世界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在悲剧通过沉默而唤起的敬畏之中,我们又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是一种无视(defiance)。也就是说悲剧英雄的沉默并不能和以言语为代表的共同体完全割离,也许我们更应该说是以无视(defiance)的方式和共同体发生了关联,所以英雄的死在我们身上唤起的感觉是和解,而不是悲恸。
但是,本雅明的重心并不是强调悲剧的和解在观者身上唤起的肃穆之情,不是被割裂了的伦理实体重新获得同一的平静,相反在和解中,本雅明把目光投向的是陷于巨大的痛苦之中的沉默的悲剧人物本身。所以,悲剧的终结,悲剧所达致的和解,是在悲剧英雄的沉默之中来完成的,它是神话(myth),是无法理解的(inscrutable),在英雄死亡的那一刻他是完全孤独的,这就是在沉默和言说之间达成的和解。
从表面上看本雅明和卢卡奇关于悲剧的论述非常相似,但是我们仔细推究的话就会发现,两者的侧重点并不一样。卢卡奇在《悲剧的形而上学》中对悲剧的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由悲剧引发的在小说中达到高潮的本质和生活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即强调的是悲剧英雄灵魂的确定性只有在毁灭生命的时刻才能够得到实现,这是和史诗教导我们如何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但本雅明在悲剧英雄的沉默中更多看到的既不是黑格尔意义上伦理实体的载体,也不是卢卡奇那里获得灵魂确定性的死去的英雄,而是痛苦而骄傲的人,是盲眼的俄狄浦斯。本雅明在悲剧英雄的沉默中感受到的是他的肉身(physis)遭遇的巨大痛苦和骄傲。也就是说在本雅明这里,悲剧英雄首先是作为一个人,并且是不受神看护的人的形象出现,这也是本雅明的悲剧观和黑格尔最大的不同。
在黑格尔对悲剧的讨论中,不是作为伦理实体代表的单单的人本身是不具备进入悲剧的可能,因为悲剧只有发生在伦理实体之间的相互冲突和和解之中。正如同奥尔巴赫在谈到古典的文体分离时指出,能够进入古典悲剧这种崇高文体,绝非弱小无助的人,绝非熙熙攘攘的尘世生活,后者只有在古典的喜剧中才能够得到表现。
黑格尔所说的作为伦理实体的代表即是体现了古典悲剧在这一点上的严格划分。悲剧人物即便是在面向死亡的时候也是坚定的,他不会遭遇盲眼的俄狄浦斯那样的孤独、痛苦和不解。而本雅明对悲剧的讨论带出了无助的肉身的人,因此对他来说悲剧是人和神之间的和解,而不是代表不同神意的伦理实体之间的和解,这也是《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的不同。
3、作为第一和第二次牺牲的悲剧英雄之死
在前面对黑格尔和本雅明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引出了本雅明悲剧观的核心:最微不足道的人。可以看出,本雅明在悲剧讨论中的侧重点是为其后面对哀悼剧的研究做铺垫的,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悲剧英雄身上尚不具备基督教出现以后的凡俗意味。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本雅明悲剧观中的人神和解是如何实现的。
本雅明在讨论悲剧时指出,悲剧的核心观念并不是舍勒所谓悲剧英雄和环境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而是牺牲的概念(idea of sacrifice)。悲剧和古代的牺牲或者说献祭的不同在于,悲剧英雄同时是第一次与最后一次牺牲。最后一次牺牲是指面向代表着古代众神(ancient rights)的牺牲,而第一次牺牲则是指向那尚未到来的新的国度。
这和古代出于命运的职责的牺牲不同,因为它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而是英雄自身的生命。换句话说,这里体现了英雄自己的意志,所以才有第一次牺牲之说,只不过这不是英雄的个人生命能够负载的,虽然对于尚未到来的民族共同体来说是有益的。
因此悲剧性的死亡具有双重意义,它既否定了古代奥林匹斯众神的胜利,同时又将英雄身上作为人性的丰饶而高傲的一面献祭了出来。悲剧的痛苦并不是单纯地遭受惩罚,“死亡成了对死亡之危机的救赎”。本雅明在这里援引了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Oresteia)里面的一个场景,祭坛如何可能成为庇护所,愤怒的上帝如何可能成为一个仁慈的上帝,而一个罪人如何可能同时成为囚徒和上帝的侍者。
我们看到正是因为有了牺牲这个概念,使得命定(finality)变得不再可能。但是这见证了英雄之伟大的第一次牺牲面向的是遥远的国度,这意味着在英雄身边的共同体当中,他是始终得不到承认的。所以,“内在的正当性(justification)体现在悲剧表演中同时传达给观众和体现在演员身上的默然的痛苦”(同上引注)。
本雅明说这也是为什么在尼采看来悲剧最深沉的地方不在于它的语言,而是形象,是展现,不是悲剧英雄说的话,因为在第一次牺牲和第二次牺牲之间的巨大的张力只有在沉默当中才能够表达出来。或者用本雅明的话来说,悲剧英雄的成就并不在于语言,而仅仅在于它的身体(physis),在于英雄之死。在悲剧英雄的孤独和沉默之中,在他对共同体的背离中,悲剧英雄并不是获知了更高的神意或是确定性,他也不是一个已经被纯洁的神赦免、宽恕并与其和解的纯洁的人,而是说这个人在自身巨大的力量之中认识到他比他的众神要更好,这让他愕然无语。
这是本雅明对悲剧的讨论中最核心的地方,也就是说悲剧英雄首先是一个孤零零的人,在悲剧英雄之死中,在肉身遭到毁灭的同时他看到了人之为人的那一部分的高贵。这才是悲剧中正义的奥秘,也就是说正义并不是对人的简单的毁灭,而是在毁灭之中对人的保存。
本雅明在《暴力的批评》(Critique of Violence)中区分了神秘的暴力(mythic violence)和神圣的暴力(divine violence)。在他看来神秘的暴力是律法得以产生的根源。在神秘的暴力中神显示了自己的存在,但并不等于是说为了实现神的意志或者目的,它只是表明神是存在的。
本雅明用了尼俄柏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阿波罗和阿尔忒密斯的行为是在惩罚,但是他们的暴力不仅仅只是对一个僭越道德不受规矩的人的惩罚,相反是要在暴力之中通过神的显形确立律法。尼俄柏的高傲并不是她敢于触犯律法,而是她敢于挑战命运,而在这场斗争中命运必然会胜利并由此而确立律法。同样,在普罗米修斯的骄傲和勇气之中,我们会看到悲剧传达的希望,是留给后来的人的,也就是说确立新的律法的希望。命运并没有完全消灭了尼俄柏,尽管它残酷地毁灭了她的孩子,但是它留下了母亲,让带罪的母亲如同石头一样屹立在人神之间。
悲剧中的命运实际上揭示了律法的根源,或者说律法的两面性,律法不仅仅是神意或者说正义的体现,同时它是暴力,是施加在人身之上的暴力,这也是律法内部深藏的不确定的因素,或者说律法本身最成问题(problematic)的地方。从悲剧的命运中确立律法的根源,即意味着正义在这里已经采取了和古代的惩罚和报应有所不同的方式。
本雅明在另一篇小文章《命运和性格》(Fate and Character)中指出,法律的框架里面不仅是罪,相反所有的罪都是不幸。如果法律仅仅看到罪的话,那无疑就将法律完全混同于简单的正义(justice),这不过体现了久已逝去的神魔时代(demonic age)中受到严格规定的人和人以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而不幸的概念最早在悲剧当中得到体现,“不是在法律,而是在悲剧当中,天才第一次从罪的迷雾中浮起,因为在悲剧中神魔的命运(demonic fate)被打破了”。也就是说罪和赎罪不再是置于天平的两端加以衡量,相反它们不加区别的混杂在一起。悲剧的目的并不是恢复已经被打破的旧有的神意的秩序,并不是完全成全神的意志,而是神的显形。
因此,在悲剧中不仅有罪和惩罚,更有不幸和宽恕。本雅明说,命运首先呈现为遭遣(condemned)其次才是罪。歌德把这两层意思同时包含在一句话里面,“你让可怜的人变得有罪”。律法并不是惩罚,而是谴责。
我们注意到悲剧在这里开启的新的方向,即我们在前面谈到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牺牲。也就是说悲剧并非针对特定的人,命运打击的是人身上作为人的那一部分生命,即人做为有限生命的自然的罪。遭遣的有罪的状态和触犯律法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前者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正如科亨(Cohen)所言,命运的秩序里面同时包括了违反和触犯。
如果说上帝是和神秘对立的话,那么神圣的暴力也是和神秘的暴力对立的。如果说神秘的暴力是立法,那么神圣的暴力就是摧毁法律,如果说前者是要树立界限,那么后者就是要无限地摧毁界限,如果神秘的暴力同时带来了罪和复仇,那么神圣的暴力只是赎罪(expiate),如果前者让人感到威胁,那么后者让人震惊,如果前者是流血的,那么后者是不流血的致命。尼俄柏的故事可以和可拉的故事相对应。上帝的审判打击了高傲的利未人,事先没有任何警告,没有威胁,但确是毁灭。但同样在毁灭中赎了罪。
本雅明说上帝的毁灭是不用流血的,这和赎罪的特征是关联在一起的,因为血象征着纯粹生命(mere life)。神秘的暴力是施加在纯粹生命之上的血腥的权力,是为了成全律法,而神圣的暴力则是对神秘的暴力之摧毁,它的力量来自于更为自然的生命的罪,它使得活生生的不幸的生命赎回了它在律法中的罪,同样也因此而赎回了律法本身的罪。因此神圣的暴力是成全纯粹生命的力量,这也是其和神秘暴力的根本区别。或者如本雅明所言,神秘的暴力要求的是牺牲,而神圣的暴力则是承纳。
“不可杀人”(Thou shalt not kill)并不是说生命本身有多么神圣。如果因为生命本身是不可触犯的,是神圣的,因此而不可杀人,那无疑是将存在本身置于正义之前,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存在,或者说单纯的生命意味着作为“人”这样一个不可化约的事实,那么说存在在于正义之前多少还有一点道理,换言之,这就是说对于人来说不存在(none-existence)是比尚未实现的正义状态(即不正义的状态)更坏。这是和人作为有限生命的自然之罪相对应的本雅明一直所言的自然的无辜。
我们从本雅明和黑格尔关于悲剧的不同入手点开始,已经逐渐对本雅明的悲剧观有了切实的把握。在本雅明看来,悲剧英雄首先是作为血肉之躯的人,作为赤裸裸的自然生命出现在命运的框架里面的。这是和黑格尔不同的地方。换言之,本雅明在悲剧中侧重强调的人之为人的那一部分无疑将有限性和偶然等一系列人作为造物的有朽的特征带入进来了,这在黑格尔看来不应当是悲剧的基础。正是在悲剧中体现出来的人和神之间的复杂关联,人在毁灭中得以成全的人之自然,才是本雅明悲剧观的核心要义,并且一直延续到他对于哀悼剧的论述。
松迪在“谢林、荷尔德林和黑格尔中的悲剧观念”中指出,希腊悲剧通过允许悲剧英雄和命运抗争的方式承认了人的自由。他在提到荷尔德林的时候指出,要理解悲剧就必须认识到所有权力的分配都是公正而平等的,但是原初的正义并不会以原初的力量(original strength)显示出来,而更恰当的说是在软弱当中呈现出来。
悲剧英雄是那最微不足道的人,在悲剧英雄的毁灭当中,正义呈现出来。神人之间的联系必须在悲剧中表现为身体的分离(physical separation),这实际上深刻地划出了神人之间的距离,有了这个距离才有了真正属人的那一部分,不再如同原初状态那样和神混同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悲剧和史诗世界的分离。
但是,作者看到荷尔德林在解读索福克勒斯时指出,在悲剧中神和人之间的张力没有得到延迟和保存,相反却是彻底爆发了,神来临的时代过早地降临在尚未充分能够承受它的时代中,所以夜晚变成了灼热的白天。而神只有在夜晚出现的时候,才不会伤害或是毁灭人,这也是荷尔德林后期的诗与其早期的恩培多克勒之死的不同。
神在夜晚来临,这正是本雅明对哀悼剧讨论的基础,我们正是从本雅明对哀悼剧的讨论中可以看到悲剧引发的主题,即神人之间的复杂关联,如何在哀悼剧中以延迟的方式呈现出来。悲剧英雄之死中获得的和解如何在哀悼剧中被一再延迟,从而哀悼代替了和解,夜晚代替了白天。
二 哀悼剧:本雅明悲剧观的完善
戈得曼在《隐蔽的上帝》的第一篇“悲剧观”中,用帕斯卡的《耶稣的神秘》结束了这一部分的讨论。帕斯卡在《耶稣的神秘》中选择了耶稣一生中仅有的两个孤独的时刻,即客西马尼园之夜和忧伤时来解释《福音书》,并赋予《福音书》以悲剧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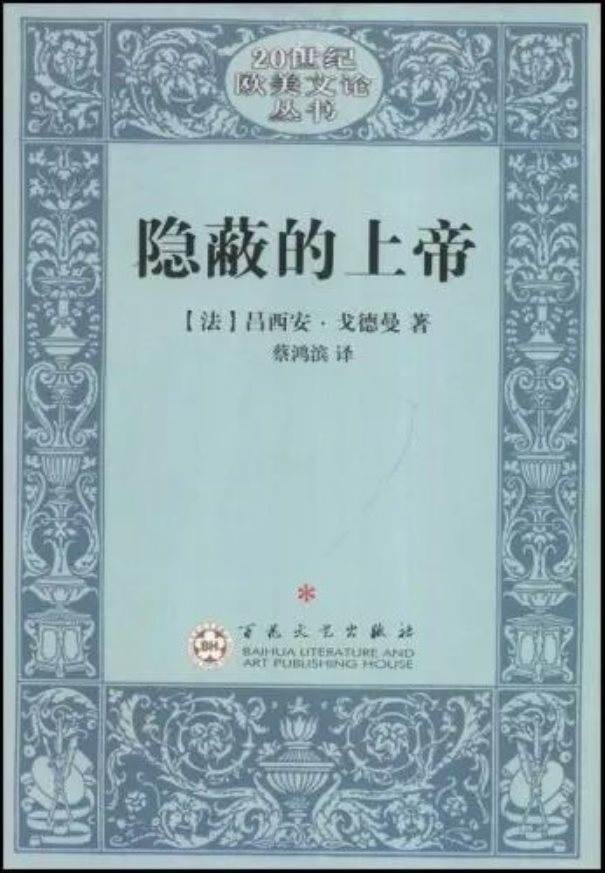
图为戈得曼《隐蔽的上帝》封面。图片来源:豆瓣。
戈德曼看到,帕斯卡的文本是按照《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写的,这是因为这两部福音书的相应段落完全适合用来做悲剧的解释。而帕斯卡之所以舍弃《路加福音》是因为,在这部福音书里有一节断言耶稣并不是一个人在山上,上帝派了一个使者来让他安心:“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而《耶稣的神秘》丝毫没有提到这种孤独的超越。同样帕斯卡也舍弃了《约翰福音》中的部分内容,因为在《约翰福音》里耶稣忧伤的这一部分,取消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的Lama sabactanie(为什么离弃我),上帝的离弃变成了上帝的“愤怒”,而橄榄山上的孤独变成了祈祷,在祈祷中不断提到耶稣的荣耀和门徒的成圣。而帕斯卡的《耶稣的神秘》严格区分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悲剧人的形象和只有圣徒才能进入的坟墓中耶稣的神圣而隐蔽的形象。
戈德曼指出,悲剧人和正直的耶稣基督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在悲剧人和为拯救人类而受难牺牲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之间才是对称的关系。《耶稣的神秘》中作为悲剧人的耶稣是不被同伴理解的耶稣,是同时被上帝离弃的耶稣,耶稣这一忧伤的时刻,才是戈德曼讨论的悲剧观的核心,这也是救赎不可跳跃的时刻。忧伤的耶稣正是理解本雅明对哀悼剧讨论的核心。
1、悲剧性向现代的转变
松迪将悲剧(tragedy)和悲剧性(tragic)区别开来,前者指的是特定的古希腊的悲剧这种形式,后者指的是在悲剧中已经得到表现并且一直延续到现代的悲剧的品质。在他的讨论中,本雅明被放在过渡阶段,虽然他对本雅明的论述不多,但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本雅明的悖论(paradox)和黑格尔的辩证(dialectic)之间的不同,“事实上,本雅明的悲剧英雄并不是和人为的律法抗争(像在黑格尔中那样),而是和历史进程中的非人的恶魔般的力量较量”。这正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上帝离弃的时刻。

图为《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图片来源:我爱画画网。
松迪看到黑格尔在其早期神学著作当中,将犹太教和基督教进行对比的时候指出,在犹太教里面是不可能发展出后来基督教意义上的命运观的。因为基督教的律法不能作为异己的惩罚,而是应当成为人的命运,人当爱自己的命运,虽然这并不会改变律法本身对人具有的绝对权威。
到了佐尔格(Solger)这里,悲剧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与人相敌对的不再是事实或是客观的必然性,而是人类存在(human existence)本身,是“从理念中转身离去,迷失且空虚的生命存在”,也就是说现在构成悲剧性的核心是失去了神的护佑的纯粹的人的存在。松迪看到,佐尔格在提到悲剧性的时候,不仅仅说人是需要牺牲(sacrifice)的,而且理念(idea)本身也需要被牺牲,被毁灭,被溶解,其要义在于神圣本身是不可能直接干预的。换句话说,悲剧性在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切断了古代悲剧的可能,因为神意不可能在世之中实现。这在赫贝尔(Hebbel)的戏剧当中得到了更深的表现。
在黑格尔的讨论中可以看到,悲剧是一种伦理生活和另一种伦理生活之间的对抗,英雄的毁灭并不会对英雄本身虽然片面但是实在的伦理生活产生质疑。但是,“在赫贝尔这里,相反,人的罪产生于一个无法借助理性完满解决的卡夫卡式的过程,它面对的是一股它无从辨识也无从理解的生命力量”。
也就是说悲剧英雄自身的生活就是不确定。这是因为,精神已经完全被世俗化了,进入了一个纯粹的历史进程中,即没有神的护佑的造物的状态。这也正是本雅明对哀悼剧讨论的起点。
2、哀悼剧中的僭主和受难者
失去神的护佑的造物状态正是人在现代性的开端面临的切身处境。一方面这意味着人摆脱神意的干预,实现自主的可能,另一方面这也正是耶稣的忧伤的时刻。这两部分在哀悼剧中作为一体两面的僭主和受难者的身上同时得到了表现。本雅明在《德国哀悼剧的起源》中引用了奥皮茨(Opitz)关于哀悼剧的定义,“悲剧和英雄诗一样壮观,只不过象国王、谋杀、绝望、杀婴、弑父、火灾、乱伦、战争、动乱、哀悼、哭泣、叹息等等诸如此类的事物对悲剧较少产生负面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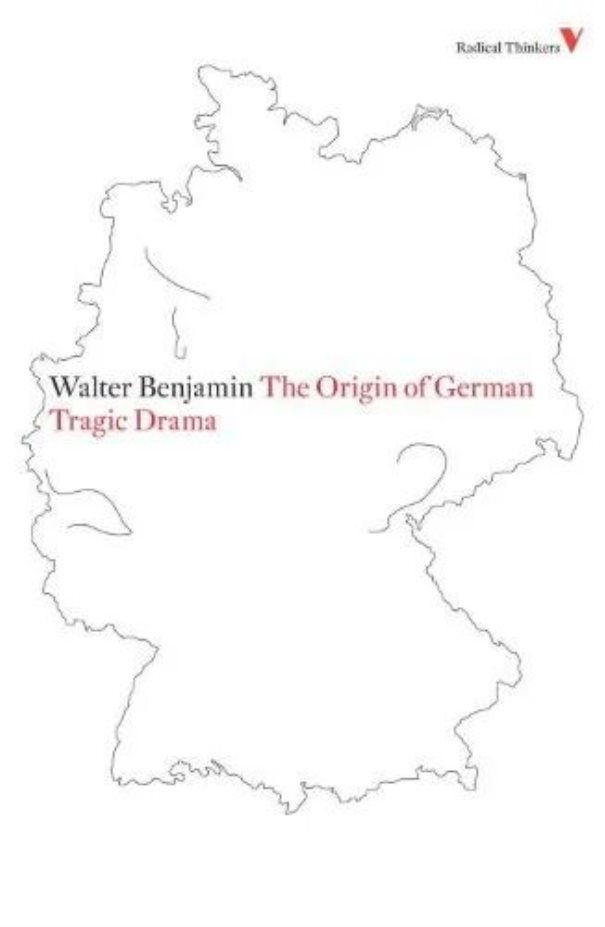
图为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封面。图片来源:豆瓣。
哀悼剧兴起于十七世纪,当时面临的背景是十七世纪兴起的绝对主权(sovereignty)以及神学意义上君权制的衰落。巴洛克时代主权观念发端于对紧急状态(emergency)的讨论。一方面这延续了文艺复兴以来的发展趋势和反宗教改革的影响,即对尘世生命的释放,但同时又保持了教会的精神,即将这种释放看作是灾难,是紧急状态。“和复兴的历史理想不同,它始终被认作是灾难。”这是哀悼剧产生并兴盛的时代背景。
在奥皮茨看来,哀悼剧和悲剧的不同在于,构成悲剧对象的并不是历史,而是神话,悲剧人物并非来自于绝对君主制国家当中的等级,而是来自于过去的英雄时代。而哀悼剧则不是要通过表现过去的英雄时代来获得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活生生的经验,相反,哀悼剧是对君主德性的肯定,它也表现君主的邪恶,表现操纵一切政治阴谋的洞见,这使得君主国家成为了哀悼剧的主要素材。
十七世纪自然法传统当中的紧急状态这一概念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消失,尤其是在康德的思想当中,这并不是因为其后的政治趋于稳定,而是因为康德的神学理性主义发展的结果。正是基于文艺复兴和教会的双重影响,巴洛克以最贴近尘世的方式倾空了这个世界,并且由此拉出了彻底的距离。
因此,巴洛克面对的是双重的格局,一方面是巴洛克的自然主义,也就是人世,另一方面它并没有抛弃救赎的框架,所以本雅明说巴洛克的自然主义必须放在神圣(deification)的层面来理解。也就是我们在前一部分讨论中谈到的,通过勾勒出完全属人的世界将神人彻底分离,但同时并不因此放弃救赎的希望,并不因此变成对人世的完全拥抱。
本雅明纠正了通常将哀悼剧视为对悲剧的拙劣模仿这一说法。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哀悼剧和悲剧一样都是力图表现庄严崇高的事物,但是在哀悼剧中往往充满了任性、迟疑和犹豫,这些都是不能进入古典悲剧的。
在本雅明看来,哀悼剧和悲剧的分离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开启了新的可能。哀悼剧经常取材东方的专制统治,尤其是拜占庭东方帝国,这是为了表现君主的无限权力。但是在哀悼剧当中,君主的无限权力却是和君主的受难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正如在希律剧中表现希律在癫狂之中挖出婴孩的脑子,或是恺撒从权力的至高之处跌落下来一样,与权力的无限荣光同时相伴的是人类的卑微和软弱,“尘世和天堂的事物混杂在一起,并且同时指向了荣光的概念。然而,这不过是异教徒式的荣光。在哀悼剧中,君主和受难者从来无法摆脱他们的内在性”。
这也突出表现在本雅明经常提到的僭主的犹豫不决,虽然他拥有无上的权力,但是他并不能完成深思熟虑的行动,他的脚步常常因为一些身体的冲动而蹒跚。所以僭主的面容之下是另一副受难者的愁苦的面容,因为僭主的专断并不是个人的任意,而是沉重的王冠和渺小的个人之间在根本意义上的不匹配,和基督一样,僭主所受的苦难同样是以人类的名义。也就是说,僭主首先是一个愁苦的人。
同样,本雅明从受难者身上也看到了僭主的影子,这突出表现在他对贞洁(chaste)这一品行的讨论中。在他看来,受难者的禁欲主义是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控制,但仅仅是控制,苦行本身并不意味着神意的眷顾,因此“完美的受难者和理想的君主一样都无法走出内在性”,他们一样是在此世的泥淖之中挣扎,这和本雅明所言的创世之处的无辜状态天壤之别。
在巴洛克时代,基督教的地位实际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各种异端邪说之所以变得不可能恰恰是因为从文艺复兴释放出来的世俗力量在他们那里反而得不到表达,而基督教在世俗化的过程反而将这部分世俗力量纳入了进来。
本雅明看到在哀悼剧和基督教的神秘剧之间有着种种相似之处,但是前者却是对后者的世俗化。反宗教改革兴起的对此世的热情并没有熄灭宗教的渴望,只不过到了巴洛克这里,宗教的渴望已经无法获得宗教意义上的满足,相反能够提供给它的只是一个世俗的解决方案。这样一来在基督教的神秘剧中尚可企及的彼世在哀悼剧里面就完全没有办法通过直接的表达触及到了。换句话说,彻底的内在性即意味着神恩(grace)的缺失。这也表现在对中世纪救赎方案的放弃, “导致末世论彻底消失的其中一股力量就是试图在赤裸裸的造物状态中,找到足以抵偿弃绝神恩的安慰”。
我们正是从僭主和受难者的身上,发现了哀悼剧和悲剧的根本不同。哀悼剧否定了任何救赎计划的可能,因为人首先不是作为一个有道德的生命,而是动物。这也是为什么悲剧的和解在哀悼剧里无法实现的原因,或者在一般人看来哀悼剧是对悲剧的拙劣模仿的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君王的荣辱成败,他们岿然不动的道德品行,并不是道德的体现,而不过是历史进程的自然一面”,是耶稣身处人世这苦难园的时刻。正是这一时刻将看起来毫无任何恩宠可言的人世,历史进程的自然一面,经由哀悼重新和恩宠之间架起了联系。下面要讨论的哀悼的主题正是连接自然和恩宠的至关重要的一环。
3、自然历史与哀悼
本雅明在哀悼剧中指出,命运并不是自然事件,它也不是纯粹的历史事件,不管命运佩戴的面具是异教徒的还是神话的,它只有作为秉承了反宗教改革的复辟神学(restoration-theology of counter-reformation)精神的自然历史范畴才是有意义的。它是历史事件当中呈现出来的自然因素,但它本身并不全然是自然的,因为神恩之光仍然从造物的处境之中反射出来,不可名状的因果链条本身并不是命运,所以命运不同于世界进程中自然法则的运行,即命运不同于自然律。也就是说命运的命定并非来自事实的必然性,命运的核心观念应该是罪——即造物的罪,基督教意义上的原罪,而非道德的逾越。
正是罪开启了因果律,使得因果律不过是命运显现的手段而已。换言之,正是在罪当中才可能纳入造物本身的偶然(accident)。我们遭遇的不可能的偶然,一些被构想出来的处境,以及一些不合时宜的复杂的阴谋,并不会减少命定的成份。
在罪的框架之下,我们看到命运成了永恒回归的秩序,这才是本雅明所言历史成为自然历史的要义,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看到有限的人世之物,而看不到神意在人世的显现,所以,哀悼剧的场景时常布置在夜间,而悲剧的故事总是呈现在日光底下。因为在永恒的罪之黑暗当中,在完全的内在性当中,我们是听不到预言或是神谕的,我们能看到的只是预言的梦境或是幽灵的显形。在午夜十分,时间停止了,幽灵显形了,预言不再以一种清晰可见的方式对历史进程中的时间(historical time)予以干预,它因而变得更加模糊暧昧。
这是奥尔巴赫在彼得身上看到钟摆摆向一个极端的情形,是彼得不认主时内心充满犹疑和惶恐的时刻。在韦伯试图通过禁欲主义英雄重新将有罪的人引向上帝的时候,世俗世界是清教徒披在身上的轻飘飘的斗篷。本雅明则要在诗人的怯懦中,由哀悼重新赋予这有罪的自然以重量。
自然历史的提出,带来了救赎方案的转换。那么是什么成全了自然历史的救赎呢?是本雅明所言的哀悼(lamentation)。要获得对哀悼的理解,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本雅明在《德国哀悼剧的起源》第二部分“隐喻和哀悼剧”(Allegory and Trauerspiel)中首先谈到的作为哀悼剧之重要特征的隐喻(allegory)和象征(symbol)的不同。
从表面上看,这是本雅明关于两种艺术表现风格的比较,但实际上这是和本雅明通过自然历史传达的哀悼的主题密切相关的。本雅明指出,在象征中美与神圣合一,实现了古典意义上内在的完善(harmonious inwardness)。而巴洛克完全抛弃了这个传统,在巴洛克的内在性(immanence)中隐喻为象征的光明世界的后面竖起了一个黑暗的背景。温克尔曼在谈到希腊的雕塑艺术时指出,艺术象征的特点是简洁(brevity)、清晰(clarity),优美(grace)和美丽(beauty)。隐喻则与此完全不同。
哀悼剧中巴洛克风格的夸张、繁复、暧昧甚至暴烈无一能够实现象征的完美统一。所以克罗伊策(Creuzer)说隐喻只是代表了一个一般的理念,这个理念和隐喻借以表现的方式之间是不协调的,不同一的,只有象征才是理念的完美体现。象征之中的美凝固在每一个确定的时刻,也就是说在每一个片刻它都是完满的,而在隐喻之中我们几乎无法找到完美的时刻,时间是流动的更迭的。
因此我们要理解隐喻与其传达的理念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如同象征那样是一对一的,相反隐喻之中的统一是神秘的,这正是哀悼剧的奥秘,也是他对荷尔德林的第二首诗的讨论中提到的身处世界之中的诗人与上帝同在的奥秘。正是由于隐喻之中的彻底的内在性,所以才有了时间的概念,在象征之中是没有流动的时间的,流动的时间是真正世俗的时间,它在每一点上都不是完美的,都是消逝,但时间的流逝并不是简单的消失和毁灭,“在象征里面毁灭(destruction)被理想化了,自然被改换的面容在救赎之光中突然被启示出来。
而在隐喻里面,历史呈现为一片已经化为石头的原始的景象,有关历史的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悲伤的、失败的,那是死亡的面容。尽管它缺乏所有那些象征的表达方式,缺乏古典的比例,缺乏人性,然而,在其中,人对自然的臣服一览无余,它不仅对于人类的存在持有疑问,而且同时提出了个体的自传式的真实的历史存在(biographical historicity)”。在隐喻中,“意义与死亡同时在历史中生成,正如同他们彼此紧密联系在造物的缺乏恩典的原罪之中”。
克罗伊策看到德国十六世纪的时候,在宗教改革和隐喻的兴起之间存在着并行关系,隐喻并非意味着投身于尘世或者造物的道德幸福之中去,它的全部目的在于神秘的教导。但是从巴洛克的角度来看,和教会传统不同的是,自然才是它要表达的意义所在,或者说我们在巴洛克的自然历史观当中又可以看到反宗教改革的踪迹,或者说文艺复兴的影响,只不过这是衰败的自然,是死亡的自然,是有罪的自然,这才是结合的关节点。
正是有罪的自然架起了巴洛克这里神意和人世的沟通,是支撑哀悼剧的框架。有罪的自然首先看到并承认了自然,是不受神干预和护佑的单纯的自然生命,与上帝同在的必要前提是与世界的同在,尽管对自然的承认是在罪的框架里面,但这毕竟不是对自然的弃绝或者说将人世仅仅看作救赎的工具。在巴洛克这里,历史不过是一个面向,自然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历史必须彻底地完全地被囊括进自然之中。中世纪的隐喻是基督教式的和教化的,此世和彼世相比不过是阴影,而巴洛克时期的隐喻,尤其在它神秘和自然历史的角度上来看,更接近于古代,不仅是埃及的古代,也是希腊的古代。
我们这里看到了巴洛克和古代在自然概念上的传接,只不过正如奥尔巴赫谈到基督教影响下的现实主义和荷马史诗的现实主义是有根本不同的,对巴洛克的自然概念的理解是要转道于基督教在其中产生的影响的。透过巴洛克时代那些纷繁复杂的隐喻的形象我们看到,任何人、任何事物以及任何关系都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物,尘世的任何渺小的事物都不具备本身的确定性,都是无足轻重的。这是经由基督教影响下形成的具有有限性的自然,这是和古代的差别所在。因此,在隐喻之中历史被带入了由死亡代表的自然当中,即哀悼剧中的废墟。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总是将基督诞生以及礼拜(Adoration)置于古典神庙的废墟的背景之下,而不是中世纪的马厩,这同样表明了古典精神的传承。只不过就像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这是转道了基督教之后的传承,或者说从宇宙论上的自然向创世意义上的自然的转变。基督的一生即是对此最集中的体现。
在基督的生命中,我们看到神秘的瞬间(mystical instant)变成了当前活动展开的现在(now),象征成了隐喻,永恒和救赎事件完全分离,“耶稣将会忧伤,一直到世界的终了;我们在这段时间里绝不可睡着”。
本雅明书中提到豪森斯坦因(Hausenstein)说,在巴洛克当中要表达神圣(Apotheoses)的时候,往往把前景放在一种极度夸张的现实布景之中,仿佛要把所有的尘世事物囊括进来,否则就不足以彰显神圣。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写实的态度并不是借助视觉效果上的对比来突出内在性和超验之间的张力,而是要为神圣留下足够的严肃的空间,即神圣是与众不同的,是肉眼无法识别的。当人为象征中流淌出来的神圣所吸引时,隐喻就是要从事物的深处来打断这股神圣之流,从而战胜象征。
这同样表现在巴洛克的抒情诗当中,“这些诗歌当中没有向前的运动,而是从内部象漩涡一样的翻腾起来”。但是很奇怪的是,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却使得隐喻的形象超出了其作为尘世之物的本分,从而赋予其神圣的意味,“在隐喻的框架下面,尘世的世界同时被提升和贬低”,“在忧郁的凝视之中物体成为了隐喻,如果忧郁使得生命在奔涌而出的同时已经死了,但却维持了永恒的安宁,那么这就是隐喻,是隐喻不可阻挡的力量 ”。
巴洛克并不是赋予生命以精神品质,相反它是彻底使其失掉灵魂。正如同诺瓦利斯说,“诗歌不过是音色优美和辞藻华丽,除了不多的几个可以理解的诗行之外,并没有任何意义或是连贯性,这如同最异彩纷陈的片断,真正的诗歌至多只能是在整体上具有某种隐喻的意义,而它的效果至多也是间接的,如同音乐那样”。
那么,哀悼剧基于自然历史基础上的救赎到底是什么呢?
黑格尔在区分古代悲剧和浪漫型的现代悲剧时指出,对于古代悲剧来说,如果人物抉择了一种唯一符合他们已定型的本质的伦理性的情致,他们就必然要和另一种同样有辩护理由但是相互对立的伦理力量发生冲突;浪漫型悲剧人物却一开始就置身于复杂的偶然关系和情况之中,可以这样行动也可以那样行动,所以由外在情况提供机缘的冲突基本上是由人物性格产生的。这造成了古代悲剧和近代悲剧在和解意义上的不同。
正是由于死亡等凸现为偶然事件,或者说悲剧意义上的实体性的消失,“所以落到我们头上的只是一种酸辛的和解感:一种在灾祸的不幸中超度到极乐世界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正是因为古代悲剧在现代变得不再可能才有了浪漫型悲剧的酸辛的和解感,这是古代悲剧在现代的失败。
黑格尔看到,在古代悲剧中,合唱队承担了和解的功能,因为合唱队和个别的悲剧人物之间始终保持着距离。合唱队代表的就是带有伦理性的英雄们的生活和动作中的真正实体性;和个别英雄们不同,合唱队代表人民,人民就是丰收的大地,英雄们是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花朵和树干,他们的整个的生存是要受这种土壤制约的。所以合唱队在本质上所站的立足点是这样:当时还没有确定的国家法律和固定的宗教教条来对抗伦理方面的纠纷,而伦理力量只有在直接的(自然的)生活中才显现出来,而且只有平静生活的平衡才能防止个别人物行动中不同的力量的对立所必然引起的那种可怕的冲突。
合唱队使我们意识到这种保证安全的庇护所就在目前。所以合唱队不会参与到动作的情节发展里面去,合唱队的表达方式是抒情的,但是它又保持了史诗里面的实体性。所以合唱队才有可能形成和解。就像剧场本身有它的外在场所,布景和环境一样,合唱队实际上就是人们,也就是一种精神性的布景,可以和建筑中的神庙相比。神庙原来围绕着神像,但是到了近代,雕像却在露天里站着,没有神庙作为背景了;近代悲剧也是如此,它用不着合唱队作为背景了,因为它的动作情节不是以这种实体性力量为基础,而是以主体的意志和性格以及事迹和环境的显然外在的偶然因素为基础了。
黑格尔看到一旦戏剧离开了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当中未经分裂的单纯意识,合唱队就不再适用了,比如骑士风和君主专政的题材就不适宜用合唱队,因为当时人民出于服从的地位。大体来说,只要所用题材涉及个人情欲目的和性格乃至阴谋诡计,合唱队就不适用了。换言之,当悲剧变得不再可能的时候,合唱队的角色也发生了转换,这也意味着从悲剧的和解走向现代悲剧的和解,而这两者之间有质的区别。其最关键的要义在于合唱队不再代表永恒正义,不再是神意对人世的干预,相反,合唱队变成了人世的映射(reflection)。
本雅明说悲剧是预言(prophecy)的准备阶段,在预言当中,过去的一切沉默,但是所有的痛苦都得到了救赎,“所谓的悲剧性即是指预言响起的刹那和过去变得沉默,所有的痛苦和死亡在预言中得到救赎”。
但是哀悼剧中则没有预言,只有被尘世裹挟的命运,哀悼剧是哑剧。悲剧上演的剧场是露天,演员、观众还有自然融合在一起,所以悲剧舞台具有宇宙(cosmos)的意味。但是哀悼剧则不同,哀悼剧的舞台是一个完全内在的感觉世界,观众是旁观者。悲剧中的合唱队起的是和解的作用,它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的超然,但并不是冷漠或是怜悯,合唱队试将悲剧中已经碎裂的碎片重新拼接成一幢巍然耸立的大厦,无论是伦理的社会还是宗教的共同体。
也就是说重新架起被英雄之死割裂了的宇宙,而哀悼剧中的合唱队则和剧中的故事完全分割开来,是作为故事的旁观者,所以它承担的是哀悼(lament),是对剧中不幸的反射。所以合唱队总是和梦境联系起来,和现实的行动世界形成对张。它就象一面镜子,反射出行动世界,因此它并不具备悲剧中通过预言产生的和解作用,它仅仅是对人世的哀悼。哀悼什么呢?尘世的无常,“啊,人生一世白驹过隙,就象脸上的笑容或是鸟儿在林梢的歌唱一样短暂”。
所以哀悼剧当中的合唱队充满了悲剧中没有的同情和情感,而同样它也无法承担起重构宇宙或是实现人神和解的作用。它更象是一个忧郁的旁观者,或者沉思者,它不可能实现神意的干预,它也不会带来任何清晰的神意和命令,“鬼魂如同意义深远的隐喻一样,它们是哀悼的呈现,它们和哀悼者之间有着某种亲和力,那些沉思迹象和未来的人”。
然而哀悼终究是人的声音,它不同于悲剧中的预言,是哑剧的世界里面人的哀叹。本雅明在谈到隐喻的时候曾经援引波墨谈到,“我们所说、所写或是从上帝那里聆听的教诲,如果没有那大大的印记(Signature)它们将仍然是喑哑无光的,因为它们不过是历史的产物,不过是从另一个人的嘴里面来的;但是如果精神向他开启了印记,那么他就会明白另一个人的言语,并进一步明白圣灵是如何在声音和语言当中启示和显现。因为在造物的外在形式之中,在他们的冲动、意向和欲望之中,在他们的声音、嗓音和言语之中,隐秘的圣灵已经被知晓了”。说出的语言是造物自由自发的活动,而隐喻中写下的语言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将事物收拢过来从而具有了某种神圣的意味。
换言之,在哀悼之中我们能够聆听到那大写的印记,尽管它并不会出现在活生生的语言或是声音里面。尽管哀悼是人的声音,然而在哀悼之中,在对缺失的感受之中,意义会以某种方式呈现,“事实上,精神自身是纯粹的理性,是完全忠实于自己的,是身体的影响把它拉向世界,它忍受的痛苦是一种更加直接的、剧烈的情感反映,而不是所谓的悲剧冲突。
如果说在死亡当中,精神重新以幽灵的方式获得自由,只有在那时身体才获得安宁”。在哀悼中我们经验到的是因为缺失而带来的巨大的沉默,本雅明说因为有了沉默,堕落的造物才会哀悼,但反过来一样成立,因为哀悼所以沉默,“在所有的哀悼当中都有一种沉默的倾向,这并不是其不愿或是不能去沟通,而是因为在哀悼者看来只有那未知的才能完全了解他”。
所以,虽然哀悼仍然不过是我们罪之反射而不是神圣的启示,但是在哀悼之中我们为那最终的神圣的到来留出了位置。换言之,造物本身虽然是有限的,是有罪的,但造物状态是我们唯一企及神意的开始,同样,哀悼虽然不过是属人的感伤的声音,但在哀悼中体验到的空白是我们唯一可以靠近神意的地方。这才是哀悼剧的真正要义,也是在切断了悲剧的和解之后,人神之间获得联系的方式。
在本雅明在对德国哀悼剧的研究中,引出了造物的自然历史的概念。德国哀悼剧兴起于巴洛克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社会进一步得到发展的阶段。巴洛克时代的复杂之处就在于一方面它沿袭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世俗化进程,但另一方面,世俗化又始终是在神学框架内部的。这体现在哀悼剧中绝对君主和受难者的并存,也体现在本雅明通过隐喻阐发的哀悼的主题。
我们看到,韦伯在科学学说中作为讨论科学的意义问题之前提的“致命的除魅”这一彻底的世俗化过程在本雅明关于悲剧和哀悼剧的对比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表现在哀悼剧切断了悲剧和解的可能。但是,和韦伯用来作为科学学说的新教伦理的天职观不同,本雅明希望通过对德国哀悼剧的研究能够重新在悲剧已然不可能的现代世界里面重新架起自然和恩宠之间的关联,这正是他通过哀悼阐发的救赎意味。
文字编辑:龚之璇、张可昕、杨茜茜
推送编辑:王天行、毛美琦
审核:范新光
本文节选于王利平副教授硕士论文第三章。


